人的文學(xué)(節(jié)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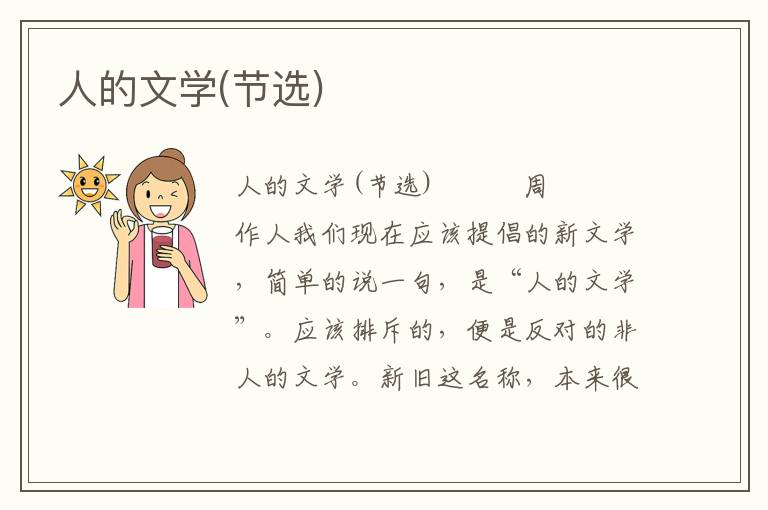
人的文學(xué)(節(jié)選)
周作人
我們現(xiàn)在應(yīng)該提倡的新文學(xué),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xué)”。應(yīng)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xué)。新舊這名稱,本來很不妥當(dāng),其實(shí)“太陽底下何嘗有新的東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無新舊。要說是新,也單是新發(fā)見的新,不是新發(fā)明的新。“新大陸”是在十五世紀(jì)中,被哥侖布發(fā)見,但這地面是古來早已存在。電是在十八世紀(jì)中,被弗蘭克林發(fā)見,但這物事也是古來早已存在。無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見哥侖布與弗蘭克林才把他看出罷了。真理的發(fā)見,也是如此。真理永遠(yuǎn)存在,并無時間的限制,只因我們自己愚昧,聞道太遲,離發(fā)見的時候尚近,所以稱他新。其實(shí)他原是極古的東西,正如新大陸同電一般,早在這宇宙之內(nèi),倘若將他當(dāng)作新鮮果子,時式衣裳一樣看待,那便大錯了。譬如現(xiàn)在說“人的文學(xué)”,這一句話,豈不也像時髦。卻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時生了人道。無奈世人無知,偏不肯體人類的意志,走這正路,卻迷入獸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來。正如人在白晝時候,閉著眼亂闖,末后睜開眼睛,才曉得世上有這樣好陽光;其實(shí)太陽照臨,早已如此,已有了許多年代了。……我們要說人的文學(xué),須得先將這個人字,略加說明。我們所說的人,不是世間所謂“天地之性最貴”,或“圓顱方趾”①的人。乃是說,“從動物進(jìn)化的人類”。其中有兩個要點(diǎn),(一)“從動物”進(jìn)化的,(二)從動物“進(jìn)化”的。我們承認(rèn)人是一種生物。他的生活現(xiàn)象,與別的動物并無不同,所以我們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yīng)得完全滿足。凡有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xí)慣制度,都應(yīng)該排斥改正。但我們又承認(rèn)人是一種從動物進(jìn)化的生物。他的內(nèi)面生活,比別的動物更為復(fù)雜高深,而且逐漸向上,有能夠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們相信人類以動物的生活為生存的基礎(chǔ),而其內(nèi)面生活,卻漸與動物相遠(yuǎn),終能達(dá)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獸性的余留,與古代禮法可以阻礙人性向上的發(fā)展者,也都應(yīng)該排斥改正。這兩個要點(diǎn),換一句話說,便是人的靈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為人性有靈肉二元,同時并存,永相沖突。肉的一面,是獸性的遺傳;靈的一面,是神性的發(fā)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發(fā)展這神性;其手段,便在滅了體質(zhì)以救靈魂。所以古來宗教,大都厲行禁欲主義,有種種苦行,抵制人類的本能。一方面卻別有不顧靈魂的快樂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實(shí)兩者都是趨于極端,不能說是人的正當(dāng)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這靈肉本是一物的兩面,并非對抗的二元。獸性與神性,合起來便只是人性。英國十八世紀(jì)詩人勃萊克(Blake)在《天國與地獄的結(jié)婚》一篇中,說得最好:(一) 人并無與靈魂分離的身體。因這所謂身體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見的一部分的靈魂。(二) 力是唯一的生命,是從身體發(fā)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三) 力是永久的悅樂。他這話雖然略含神秘的氣味,但很能說出靈肉一致的要義。我們所信的人類正當(dāng)生活,便是這靈肉一致的生活。所謂從動物進(jìn)化的人,也便是指這靈肉一致的人,無非用別一說法罷了。這樣“人”的理想生活,應(yīng)該怎樣呢·首先便是改良人類的關(guān)系。彼此都是人類,卻又各是人類的一個。所以須營一種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關(guān)于物質(zhì)的生活,應(yīng)該各盡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換一句話,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勞作,換得適當(dāng)?shù)囊率匙∨c醫(yī)藥,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關(guān)于道德的生活,應(yīng)該以愛智信勇四事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襲的禮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實(shí)的幸福生活。這種“人的”理想生活,實(shí)行起來,實(shí)于世上的人無一不利。富貴的人雖然覺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謂尊嚴(yán),但他們因此得從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為完全的人,豈不是絕大的幸福么·這真可說是二十世紀(jì)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還少,不能立地實(shí)行。所以我們要在文學(xué)上略略提倡,也稍盡我們愛人類的意思。但現(xiàn)在還須說明,我所說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jì)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類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樹木。森林盛了,各樹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卻仍非靠各樹各自茂盛不可。第二,個人愛人類,就只為人類中有了我,與我相關(guān)的緣故。墨子說,“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便是最透徹的話。上文所謂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這個意思。所以我說的人道主義,是從個人做起。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穌說,“愛鄰如己。”如不先知自愛,怎能“如己”的愛別人呢·至于無我的愛,純粹的利他,我以為是不可能的。人為了所愛的人,或所信的主義,能夠有獻(xiàn)身的行為。若是割肉飼鷹,投身給餓虎吃,那是超人間的道德,不是人所能為的了。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xué)。其中又可以分作兩項(xiàng):(一)是正面的,寫這理想生活,或人間上達(dá)的可能性;(二)是側(cè)面的,寫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這類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yàn)槲覀兛梢砸虼嗣靼兹松鷮?shí)在的情狀,與理想生活比較出差異與改善的方法。……這區(qū)別就只在著作的態(tài)度不同:一個嚴(yán)肅;一個游戲。一個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對于非人的生活,懷著悲哀或憤怒;一個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對于非人的生活,感著滿足,又多帶些玩弄與挑撥的形跡。簡明說一句,人的文學(xué)與非人的文學(xué)的區(qū)別,便在著作的態(tài)度,是以人的生活為是呢,非人的生活為是呢這一點(diǎn)上。材料方法,別無關(guān)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節(jié)——的文章,表面上豈不說是“維持風(fēng)教”;但強(qiáng)迫人自殺,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學(xué)。中國文學(xué)中,人的文學(xué)本來極少。從儒教道教出來的文章,幾乎都不合格。……人的文學(xué),當(dāng)以人的道德為本,這道德問題方面很廣,一時不能細(xì)說。現(xiàn)在只就文學(xué)關(guān)系上,略舉幾項(xiàng)。譬如兩性的愛,我們對于這事,有兩個主張:(一)是男女兩本位的平等,(二)是戀愛的結(jié)婚。世間著作,有發(fā)揮這意思的,便是絕好的人的文學(xué)。……所以真實(shí)的愛與兩性的生活,也須有靈肉二重的一致。但因?yàn)楝F(xiàn)世社會境勢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極多。這便須根據(jù)人道主義的思想,加以記錄研究。卻又不可將這樣生活,當(dāng)作幸福或神圣,贊美提倡。中國的色情狂的淫書,不必說了。舊基督教的禁欲主義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認(rèn)他為是。……一個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別擇,與人結(jié)了愛,遇著生死的別離,發(fā)生自己犧牲的行為,這原是可以稱道的事。但須全然出于自由意志,與被專制的因襲禮法逼成的動作,不能并為一談。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間都知道是一種非人道的習(xí)俗,近來已被英國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種變相。一是死刑,一是終身監(jiān)禁。照中國說,一是殉節(jié),一是守節(jié),原來撒提這字,據(jù)說在梵文,便正是節(jié)婦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幾千年,便養(yǎng)成了這一種畸形的貞順之德。講東方化的,以為是國粹,其實(shí)只是不自然的制度習(xí)慣的惡果。譬如中國人磕頭慣了,見了人便無端的要請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這能說是他的謙和美德么·我們見了這種畸形的所謂道德,正如見了塞在壇子里養(yǎng)大的、身子像蘿卜形狀的人,只感著恐怖嫌惡悲哀憤怒種種感情,決不該將他提倡,拿他賞贊。其次如親子的愛。古人說,父母子女的愛情,是“本于天性”,這話說得最好。因他本來是天性的愛,所以用不著那些人為的束縛,妨害他的生長。假如有人說,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間或要說他不道。今將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極適當(dāng)。照生物現(xiàn)象看來,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續(xù),與哺乳的努力,這是動物無不如此。到了人類,對于戀愛的融合,自我的延長,更有意識,所以親子的關(guān)系,尤為深厚。近時識者所說兒童的權(quán)利,與父母的義務(wù),便即據(jù)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時新的東西。至于世間無知的父母,將子女當(dāng)作所有品,牛馬一般養(yǎng)育,以為養(yǎng)大以后,可以隨便吃他騎他,那便是退化的謬誤思想。……至于郭巨埋兒②、丁蘭刻木③那一類殘忍迷信的行為,當(dāng)然不應(yīng)再行贊揚(yáng)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術(shù)與食人風(fēng)俗的遺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學(xué)里,更不消說了。照上文所說,我們應(yīng)該提倡與排斥的文學(xué),大致可以明白了。但關(guān)于古今中外這一件事上,還須追加一句說明,才可免了誤會。我們對于主義相反的文學(xué),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論,單依自己的成見,將古今人物排頭罵倒。我們立論,應(yīng)抱定“時代”這一個觀念,又將批評與主張,分作兩事。批評古人的著作,便認(rèn)定他們的時代,給他一個正直的評價,相應(yīng)的位置。至于宣傳我們的主張,也認(rèn)定我們的時代,不能與相反的意見通融讓步,唯有排斥的一條方法。譬如原始時代,本來只有原始思想,行魔術(shù)食人肉,原是分所當(dāng)然。所以關(guān)于這宗風(fēng)俗的歌謠故事,我們還要拿來研究,增點(diǎn)見識。但如近代社會中,竟還有想實(shí)行魔術(shù)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將他捉住,送進(jìn)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對于中外這個問題,我們也只須抱定時代這一個觀念,不必再劃出什么別的界限。地理上歷史上,原有種種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氣流通也快了,人類可望逐漸接近,同一時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單位是個我,總數(shù)是個人。不必自以為與眾不同,道德第一,劃出許多畛域。因?yàn)槿丝偱c人類相關(guān),彼此一樣,所以張三李四受苦,與彼得約翰受苦,要說與我無關(guān),便一樣無關(guān);說與我相關(guān),也一樣相關(guān)。仔細(xì)說,便只為我與張三李四或彼得約翰雖姓名不同,籍貫不同,但同是人類之一,同具感覺性情。他以為苦的,在我也必以為苦。這苦會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yàn)槿祟惖倪\(yùn)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顧慮我的運(yùn)命,便同時須顧慮人類共同的運(yùn)命。所以我們只能說時代,不能分中外。我們偶有創(chuàng)作,自然偏于見聞較確的中國一方面,其余大多數(shù)都還須紹介譯述外國的著作,擴(kuò)大讀者的精神,眼里看見了世界的人類,養(yǎng)成人的道德,實(shí)現(xiàn)人的生活。原載1918年12月《新青年》
〔注釋〕 ①圓顱方趾:方腳圓頭,指人類。出自《淮南子·精神訓(xùn)》:“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 ②郭巨埋兒:郭巨家貧,因擔(dān)心養(yǎng)孩子會影響供養(yǎng)母親,遂為母埋兒,以為孝順。東晉干寶所著《搜神記》、宋代《太平廣記》、元代郭居敬的《二十四孝》、明代嘉靖時期的《彰德府志》等書中均有記載。 ③丁蘭刻木:漢代丁蘭,幼喪父母,未得奉養(yǎng),思念劬勞之恩,刻木為像,事之如生身父母。其妻久而不敬,以針刺像指,血出。木像見蘭,眼中垂淚。蘭問得其情,遂將妻棄之。〔鑒賞〕 作者開宗明義就強(qiáng)調(diào)新文學(xué)是“人的文學(xué)”。他對“人的文學(xué)”下了個定義:“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xué)。”何謂人道主義,作者詮釋為“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這里說的是陳獨(dú)秀在新文化運(yùn)動中,大力宣揚(yáng)的“個人本位”。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人的問題尚未解決,何以廓清籠罩在文學(xué)上的迷霧。這就涉及怎么看人,人道在哪里,然后才是“人的文學(xué)”怎么做。通篇讀后,感到作者所談并不局限于文學(xué),而有著社會和文學(xué)的雙重意義。作者站在當(dāng)下審視過去,所以論點(diǎn)有歷史的穿透力,發(fā)聾振聵,顯示出尖銳、厚重的意味;因?yàn)橹塾诂F(xiàn)在和未來,故敢于呼喚,給人們帶來了一線思想啟迪的熹微。文章通篇哲理性很強(qiáng),處處有對應(yīng)的關(guān)系,體現(xiàn)了作者的識見。其一,光有對人道的認(rèn)識遠(yuǎn)不夠,還要付諸實(shí)踐。世間有人道,但知與行脫離。其二,人性是獸性和神性的統(tǒng)一,要把握好它的發(fā)展趨勢。人從動物而來,難免具有動物的一些特點(diǎn)和本能,但人內(nèi)面的東西比一般動物“更為復(fù)雜高深,而且逐漸向上,有能夠改造生活的力量”。其三,改良人類的關(guān)系,“須營一種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一方面,個人努力,求人事所需(包括衣食住行等等),另一方面以愛智信勇為基本道德,與他人友好相處,“使人人能享有自由真實(shí)的幸福生活”。他以樹木與森林的關(guān)系作喻,說明人的個體與全體密切相關(guān)。其四,以人道主義為本,使人的文學(xué)成為可能。文學(xué)是軀殼,人道主義是靈魂。人的文學(xué)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正面的,寫這理想生活,或人間上達(dá)的可能性;(二)是側(cè)面的,寫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學(xué)與非人的文學(xué)的區(qū)別,在于作者是抱什么態(tài)度,取嚴(yán)肅態(tài)度還是取游戲態(tài)度,而對作品的評判,則以作品中是人的生活還是非人的生活為前提。這樣,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堅(jiān)持人的文學(xué),就要以人的道德為本。他舉例一,兩性的愛,男女平等,靈肉一致;舉例二,親子的愛,父母“用不著那些人為的束縛,妨害他的生長”。當(dāng)然,子女也要愛敬父母,盡自己的義務(wù)。作者在九十年前,就提出從個人做起,改良人類的關(guān)系,確實(shí)讓人刮目相看,發(fā)人深省。這和恩格斯1847年起草的“共產(chǎn)主義信條草案”里的相關(guān)提法,也是相吻合的。恩格斯說:在每一個人的意識和感情中,都有一些作為顛撲不破的原則而存在的原理,這些原理是整個歷史發(fā)展的結(jié)果……每一個人都在謀求幸福,個人的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離的。現(xiàn)今,大力倡導(dǎo)社會和諧,可見人與他人怎樣相處,人與社會怎樣相處,還沒有達(dá)到盡善盡美的狀態(tài)。這取決于社會的進(jìn)步,也取決于每個人素養(yǎng)的提高。多少年來,封建社會違背了人性,以“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壓抑了人的正當(dāng)愿望。古來宗教,包括基督教,也大都厲行禁欲主義,以抵制人類的本能。“我們見了這種畸形的所謂道德,正如見了塞在壇子里養(yǎng)大的、身子像蘿卜形狀的人,只感著恐怖嫌惡悲哀憤怒種種感情……”然而,歷史的車輪已經(jīng)駛?cè)?1世紀(jì),文明程度得以很大的提高。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了,物質(zhì)產(chǎn)品開始豐富了,要警惕的是另一種傾向,即人陷于物欲之中,唯利是圖,不可自拔,阻塞了道德、情操和精神上的升華,擾亂了他人和社會,失去了人之為人應(yīng)有的靈魂。總之,兩種極端都要反對。此外,作者行文,好像與讀者促膝交談,如話家常,合情合理,不唱脫離實(shí)際的高調(diào),字里行間給人以通脫、平和的感覺。今天重讀《人的文學(xué)》,依然感到親切有味。人是文學(xué)表現(xiàn)的主體,文學(xué)反映現(xiàn)實(shí)必然要反映人性,反映人的生活,反映人的思想感情。今天講“以人為本”,文學(xué)自然也要“以人為本”,這是作家的責(zé)任感和使命感所在。盡管作者后來在人品上有污點(diǎn),他也沒有始終堅(jiān)持自己的理想,而且有的提法還有商討的地方。他更多的是講個體意識(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還沒有從整個人類的角度去闡發(fā)。把他的主張同以革命手段同黑暗反動勢力拼搏斗爭的魯迅做一番比較,就顯得有些落伍了。但不必因人廢言,社會怎樣關(guān)愛人,促進(jìn)人的個性全面發(fā)展,怎樣以文學(xué)為載體,完整而又深刻地揭示人性,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至今依然可從這篇文章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