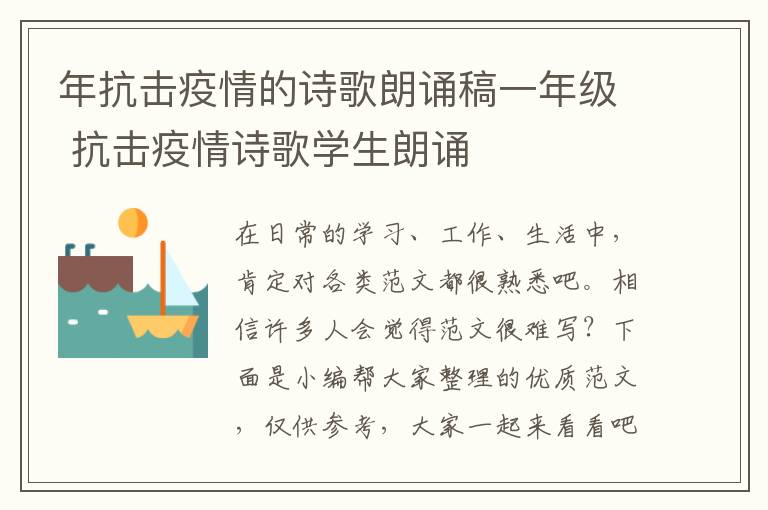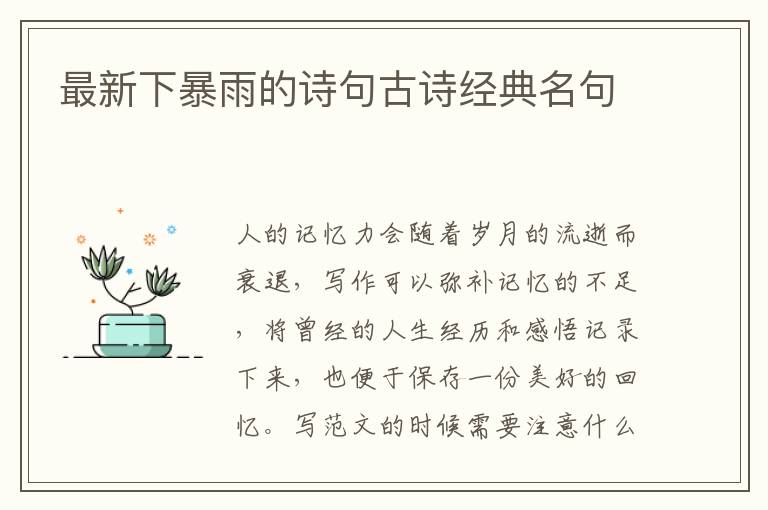許冬林·一棵野桃樹(shù)

許冬林·一棵野桃樹(shù)
許冬林
在我家和我的二伯家之間壘起了一座兩三米高的土籬笆墻,有一年的春天,土籬笆墻下生了一棵樹(shù)苗,起初沒(méi)在意,后來(lái)發(fā)現(xiàn)它的葉酷似桃葉,便也時(shí)常關(guān)注起它來(lái)。我猜想,這棵桃樹(shù)可能是我無(wú)心種下的。我喜歡到處撿一些桃核杏核回來(lái)玩,玩過(guò)之后便隨處丟撒。也許,這棵桃樹(shù)就是在我隨意丟撒間有了一次幸運(yùn)。它幸運(yùn)地在瓦礫間抓到了一捧泥土,幸運(yùn)地在兩堵墻之間抓住了幾尺陽(yáng)光,然后是空氣和濕度,接著萌芽,破土而出,有了一次脫胎換骨的超然。
我想,我也是幸運(yùn)的,在時(shí)光的河流上,屬于我的生命流程充其量不過(guò)七八十年,一棵桃樹(shù)的流程也不過(guò)十來(lái)年,而在這其間,我的生命和它的生命竟有一小截疊合,這與其說(shuō)是巧合,不如說(shuō)是幸運(yùn)。
小桃樹(shù)便在我的珍視和盼望里漸漸長(zhǎng)高長(zhǎng)大,五年之后的一個(gè)春天,它打了些紅紅小小的花苞,可是開(kāi)得卻很遲。當(dāng)別的桃樹(shù)謝盡了芳菲時(shí),它才三三兩兩地次第開(kāi)放,花朵很紅,紅艷艷的一片,紅得熱烈、張揚(yáng)、活潑,似乎想淋漓盡致地宣泄它開(kāi)放的熱情和美麗,那土籬笆墻因此而多了幾分熱鬧。奶奶來(lái)看了,然后冷冷地丟下了一句:是棵野桃樹(shù)!原來(lái)野桃樹(shù)的花開(kāi)得紅而遲,奶奶說(shuō)它成不了氣候,結(jié)不了什么好果子。可是,我還是不愿相信奶奶的話(huà),因?yàn)橐恢币詠?lái),她就沒(méi)說(shuō)過(guò)什么好聽(tīng)的話(huà)。她總愛(ài)在父母面前嘮叨,說(shuō)一個(gè)丫頭還讀什么書(shū),將來(lái)好了別人家,真是浪費(fèi),以至于我后來(lái)十幾年的讀書(shū)生涯一直懷著負(fù)罪的心理。
那棵野桃樹(shù)因?yàn)樵谕粱h笆下,沒(méi)有多占一份泥土,也沒(méi)有多占一份陽(yáng)光,因而獲得了繼續(xù)生存下來(lái)的權(quán)利。那花兒確實(shí)開(kāi)得好看,每片花瓣都染上一片紅暈,顯得更加生動(dòng)、健康,我覺(jué)得那片富有活力的緋紅似乎更能承載一份秋天的希望。三月過(guò)了,花兒落了,紅紅的花瓣隨風(fēng)飄揚(yáng),有的落在瓦礫上,歸入泥土;有的落在屋頂?shù)拇u瓦上,高高地干枯在四月的陽(yáng)光里;有的飄到小河上,隨流水而去,瘦弱的樹(shù)枝顯得頗為憂(yōu)傷和冷清。美麗總是就那么一剎那,總是太短太短,就像鄉(xiāng)下的新娘——童年的鄉(xiāng)下最熱鬧的事就是看新娘,我那時(shí)以為女人做了新娘就永遠(yuǎn)是新娘,就會(huì)永遠(yuǎn)那么干凈而美麗,天天坐在房間里,只是偶爾出來(lái)羞澀地笑笑,那只是對(duì)著我們這些孩子。可是只是三天,這些新娘便扛鋤拿鍬地下了地,一年后便是手里捧著飯碗懷里摟著孩子,門(mén)口晾了花花綠綠的一大片尿布,走起路來(lái)快了,說(shuō)起話(huà)來(lái)嗓門(mén)大了,臉色黃了,皮膚皺了。鄉(xiāng)下的姑娘就像桃花,出嫁的那天開(kāi)得最美最艷,然后一夜風(fēng)雨,便凋謝了。
當(dāng)別的桃兒已經(jīng)長(zhǎng)得肚大腰圓,滿(mǎn)臉漲紅時(shí),野桃樹(shù)的桃兒還是那么小小的、青青的,躲在枝葉叢里,它的生長(zhǎng)似乎比別的果實(shí)總要慢一拍子。中秋過(guò)后,田里的稻子已收割回倉(cāng),家里的人閑閑地坐在門(mén)口,我看見(jiàn)野桃樹(shù)上的桃兒都已經(jīng)泛起了紅暈,很多已經(jīng)長(zhǎng)得開(kāi)裂。我摘了一個(gè)輕輕一掰,開(kāi)了,里面是鮮紅的瓤,原來(lái)野桃是從里往外紅的,它成熟得那么謹(jǐn)慎而謙虛。我嘗了嘗,綿綿的、軟軟的、香香的、甜甜的,我又摘了幾個(gè)捧到奶奶面前,奶奶嘗了嘗,咂了咂嘴說(shuō),苦中還有點(diǎn)甜柔,就是太小了點(diǎn)。可是我已經(jīng)很高興了,我的野桃樹(shù)它終于捧出了自己的果實(shí)!
現(xiàn)在,奶奶早已去世,我的父母已經(jīng)老了,他們喜歡常常站在門(mén)口,看我回去。在鄉(xiāng)下,他們常常引我為自豪,引我為欣慰。他們覺(jué)得,在書(shū)聲朗朗的校園,在抑揚(yáng)頓挫的講課聲里,有他們女兒的一個(gè)聲音;在報(bào)刊的大大小小的豆腐塊里,偶爾有他們的女兒的一個(gè)名字;在讀書(shū)不多的祖祖輩輩里,有我這么一個(gè)子孫,用墨香巧扮自己。
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那棵野桃樹(shù)啊,艱難地抓住了一捧土壤,固執(zhí)地想結(jié)些果子。我不愿我的生命里只有三月,只有那短暫的絢爛。而我那些兒時(shí)女伴,她們也都和我一樣,早已出嫁。她們依然如從前的新娘,走路快了,嗓門(mén)大了,臉色黃了。我不知道,當(dāng)她們?cè)陂T(mén)前門(mén)后種桃插柳時(shí),是否想起,這樣的風(fēng)景已是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了。我愿她們的女兒做一棵真正的桃樹(shù),能夠理直氣壯地站在土地上,站在陽(yáng)光里,她們有三月的美麗,更有八月的果實(s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