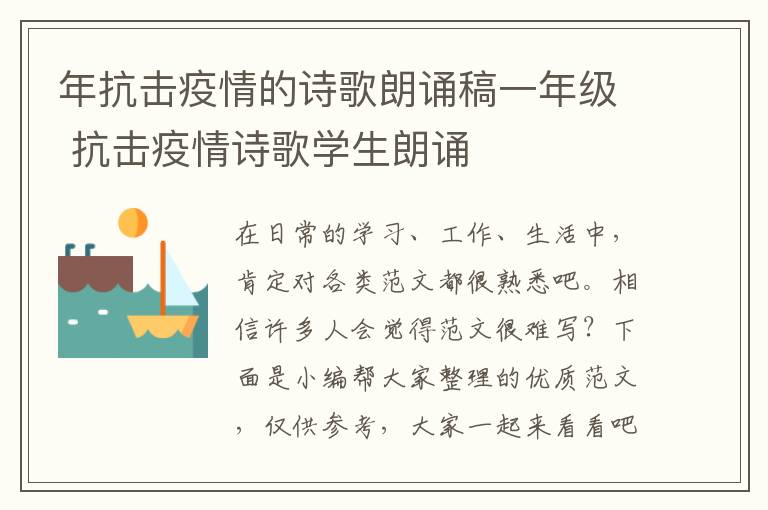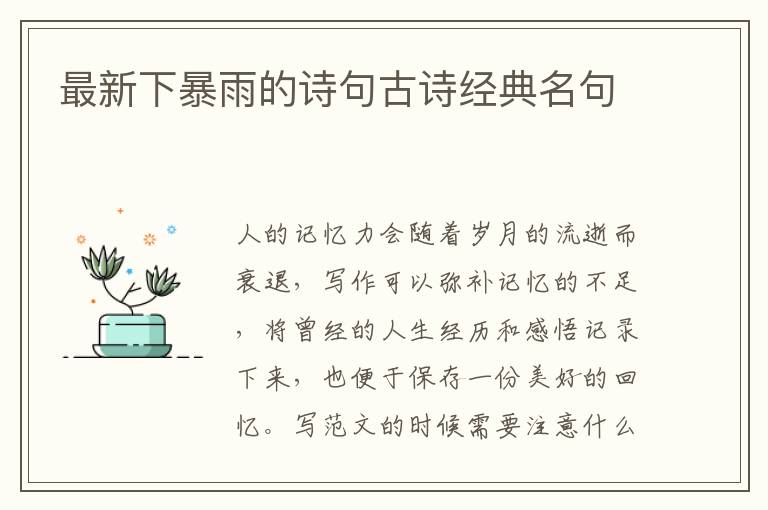謝巖津《機械》東方文學名著鑒賞

作者: 謝巖津
【作家簡介】橫光利一(1898—1947),日本小說家。生于福島縣北會津郡,父親橫光梅次郎是一個建筑工程師。他從小被寄養在寺院,養成了孤僻的性格。中學時代就酷愛文學,開始習作。1916年進入早稻田大學預科文科,繼續勤奮寫作。不久,因神經衰弱休學,后又復學。1920年再次退學。休學期間曾參加一些同人雜志的編輯工作。文學創作最先曾受到菊池寬的器重。他最早的作品是寫實主義的。1923年在《新小說》發表長篇小說《太陽》,確立了他的作家地位。1924年他與川端康成等人創辦《文藝時代》雜志、掀起“新感覺派”運動,與川端康成一起被稱為新感覺派文學的雙璧。“新感覺派”于1925—1926年發展到高峰,不久開始分化。橫光利一也轉向新心理主義,后又轉向傳統主義。他的作品頗富變化,由新感覺派的代表作《太陽》(1923),《蠅》(1923)《頭與腹》(1924)。《春天乘著馬車來了》(1926),到心理主義作品《機械》(1930),到長篇小說《上海》(1928—1931),《紋章》(1935),《旅愁》(1937—1946),以及反映戰敗后心境的《夜之鞋》等。創作形式,從長、短篇小說到戲劇、詩歌、俳句、短歌、評論以及隨筆,多種多樣,以至人們對他的評價也是各說不一。可以說橫光利一是個具有多重性格的作家。他最初的創作是富于抒情性的,“新感覺派”時期,他又以新的感受和新的藝術手法使人耳目一新。在無產階級文學興盛時期,他的文學也開始對人和社會,對人的自我和異化等問題進行思索。戰后人們對橫光的評價貶斥居多,因為在戰爭中他曾發表過“戰勝宣言”,留下了積極支持戰爭的印跡。日本戰敗后,他被指控為戰犯,受到批判,對其作品也褒貶不一。
《機械》,丁民、丹民譯,見《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第2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出版。
【內容提要】經人介紹,我來到了一家制造銅牌的作坊工作。這家的老板是個怪人。他的剛剛兩歲的孩子不喜歡他,他就發火,孩子摔了跟斗,他就去打老婆。我因此疑心他是瘋子,也許作坊中的劇毒試劑使他大腦受到了傷害吧。然而,這樣的老板又極為善良,他對錢財很不在乎,只要他手里有錢,就會毫不吝惜地散給人,然后忘得一干二凈,所以每次外出拿錢辦事,老板娘總是找人陪著老板。
我冒著被劇毒試劑奪去勞動能力的危險來到這個作坊。最初,我是想掌握制造銅牌的支術,漸漸地,我開始喜歡上了老板,暗暗地維護起老板的利益。跟我一起做工的是一個早些時間到這里的工人輕部。他怕我偷作坊里的技術,時刻在監視我的行動。然而老板卻特別信任我,他讓我跟他一起進暗室,研制新的配方。這間暗室除了老板,別人是不許進去的。如今,我有了這個特權,更使輕部對我不滿,而我又懷疑他會同老板娘一起把老板的工作秘密賣掉,于是我們開始互相監視。有一天,輕部借機打了我,我向他說明了我進暗示的原因。輕部頭一次開始向我認輸,從此不再懷疑我。
沒多久,作坊接了一大批活。為了趕活,老板從同業的作坊中借來了名叫屋敷的工人來幫忙。這屋敷一開始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他要偷竊作坊中的技術秘密,便默默地監視他。但輕部被他迷住了,對他毫不提防。為了監視他,我有意跟他接近,兩個人竟然最要好。屋敷也明白我在監視他,他不隱誨自己為偷技術的目的,這反倒讓我佩服。等到那一批活接近收尾的時候,有一天,輕部突然把屋敷按倒打了起來,屋敷被壓在強壯的輕部身下,毫無反抗的余地,我勸輕部停手,輕部反過來朝向了我,說我與屋敷是同謀,我被輕部毆打的同時,屋敷又來打我,三個人就這樣互相打做一團,直到累趴下。很可能連日的勞累和試劑的毒素使人們的理性混亂了,才造成這樣的局面吧。好不容易那一大批活趕完了,要發工資了,然而不幸的是老板又把剛領來的全部工錢丟了。在沮喪疲累之時,輕部建議三人去喝酒,大家響應。等到夜里酒醒之后,發現屋敷誤把水壺里的重鉻酸銨當成水,喝后死去。人們懷疑是輕部害了他,我也無法否定;也許害死屋敷的正是我吧,我仍無法肯定。
【作品鑒賞】短篇小說《機械》寫于1926年。當時,日本的新感覺派文學已開始走向低落時期,而從這篇小說開始,橫光利一的創作技巧和方法也發生了變化,但從中仍可清楚地看到“新感覺”的明顯印痕。小說通篇寫主人公“我”的內心獨白,雖說“意識流動”的速度比較舒緩,意識的“軌跡”也比較清晰,但仍是從直覺上再現了人物的心理動態、不間斷的意識流動貫穿小說的始終,從這一點上,把它劃為意識流文學范圍內也是不為過的。
這篇小說的最突出之處,是通過主人公內心獨白的方式,揭示了進入機器文明社會之后人性與機械的對立,反映了人類的茫然,命運的不可知。正如作品中所說:“我們之間似乎一切都明白了似的,一個看不見的機械在測量著我們,并按著這種測量的結果,在推動著我們前進。”主人公“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輕部的監視,進而又不自覺地監視起輕部和屋敷,三人之間勾心斗角,竟然不惜撕破臉皮扭打作一團,而造成這一切非理性動作的原因則是那可以使人們喪失理智的有毒試劑,這便有力揭示了機械與理智的對立。在機械主宰人類的社會中,人們時刻要受到那看不見的機械的擺布。小說圍繞著對銅牌制造技術保密或竊密這一問題,展示了人物的心理動態,主人公“我”為學技術來到了作坊,進而為老板的善良所打動,不顧輕部的干擾,為老板忠心耿耿服務。在這時,善良和忠誠這種傳統的道德觀念占了上風。然而當屋敷出現后,“我”的心理發生了突變,最初他為保密而監視屋敷,忠誠仍占主導地位。當接受了屋敷一番時代感的辯解之后,他對老板的忠心產生了動搖,他甚至想到利用老板的好意,將老板的技術秘密偷出來。到此為止,傳統的道德觀徹底崩潰,而主人公“我”也完成了他個人的異化過程。最后,三人扭打作一團,屋敷喝毒劑死去,死因不明,“我”始終搞不清自己在屋敷之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只是感到那機械的銳利的尖部對準我直逼過來”。在現代的文明社會中,主人公終于完全喪失了自我,陷入迷茫之中。這種迷茫反映了作者自身對現實社會的恐懼和不安,同時也流露出了懷疑和不滿情緒。
在圍繞試劑的勾心斗角之中,唯一一個不為所動的人便是作坊的老板——銅牌制造技術的發明者,他可以說是這場爭斗的“超人”,也是作者的理想。在金錢至上的社會中,他把錢看成身外之物,“老板娘一放松警惕,老板就如脫兔一般跑出去散錢”,然后忘得一干二凈。在他心中,根本不存在“自私”這一概念,因而“我”認為他就是古人所說的仙人,是個超凡脫俗之人。同時,老板又是極輕信,沒有利害觀念的人,當別人千方百計地為他的技術專利而保守秘密時,他卻考慮設法出賣專利,并且大意地讓與他毫不相干的“我”和他一起參與秘密研制工作。在“我”的眼中,老板似乎是一個傻子,可是老板的這種傻勁,正是他獨立于這個丑惡的社會之外,仍保持著純正的自我的有力證明。正因為如此,他的傻勁才格外具有感人的力量,既贏得了同行的信譽,也獲得了雇員的忠心,連主人公也想:“要成為老板這樣一個徹底的傻子,也是很不容易的,這位老板偉大就偉大在這一點上。因此,我由衷地表示謝意,表示愿獻出力量幫助老板搞研究。……然而,我這位老板絲毫也沒有對別人充恩人的思想,這就使我更加五體投地。我像一個受啟示的信徒一樣,被他身上發出的光芒照耀著。”這樣,在這個“傻子”老板的身上已罩上了作者理想的光圈,給作品沉悶的氛圍中增加了一抹明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