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棗》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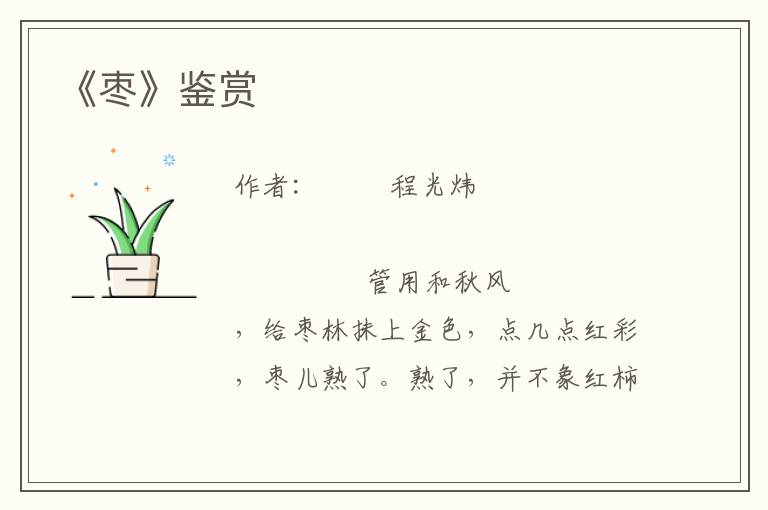
作者: 程光煒
管用和
秋風(fēng),給棗林抹上金色,點(diǎn)幾點(diǎn)紅彩,棗兒熟了。
熟了,并不象紅柿那么耀眼。
熟了,并不象金桔那么燦亮。
熟了,也不象鴨梨那么引人注目。
你不喜歡炫耀成果么?個(gè)兒是那么的小,模樣兒也不太俊俏,甚至,人們?cè)诓烧臅r(shí)候,并不那么仔細(xì),而是用竹竿敲打著你呵。
但是,我知道你結(jié)的很多很多,稠密如天上的繁星;你結(jié)的實(shí)實(shí)在在,落地“乒乒”有聲。
當(dāng)眾多的棗兒集合在一塊,堆成小山似的,誰(shuí)能低估一棵樹(shù)的分量!
也許,你真的不喜歡炫耀——我想起了你的花。
你的花不也是極小極小的么,那色彩也并不象花的色彩,同葉兒一樣,淡淡的綠色,很不顯眼,害羞似的躲躲藏藏,把自己掩蔽在綠葉之中。
你的花香味也不濃烈,清醇淡泊,似有似無(wú),溶化在空氣里,暗暗流動(dòng),被人們吸進(jìn)肺腑,沁入心脾,提神醒腦——也許,誰(shuí)也沒(méi)有覺(jué)察出來(lái)呵。
但是,蜜蜂知道你的花的美好,花的純良,它們紛紛飛來(lái)采取芬芳的汁液,釀成人們十分喜愛(ài)的“棗花蜜”……
呵!棗兒熟了,默默地熟了,悄悄地熟了,不動(dòng)聲色地熟了。
我捧著一捧鄉(xiāng)親送給我的脆棗,象捧著一捧無(wú)聲的歌。
我將這支歌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時(shí)刻默默地歌唱:該怎樣開(kāi)花,該怎樣結(jié)果……
和管用和其他詩(shī)文一樣,《棗》在寫(xiě)法上也是“由淺入深”的。先寫(xiě)棗的普通,它“并不象紅柿那么耀眼”、“并不象金桔那么燦亮”、“并不象鴨梨那么引人注目”,花朵極小,且色彩淺淡。樸質(zhì)的棗讓我們想到周?chē)T多普通的事物,一種從棗中源源流出的平民感,使我們漸漸感到了它的自然和親切,從而產(chǎn)生對(duì)“棗”的接受心理。如果說(shuō),作家寫(xiě)作是一種自我評(píng)價(jià),那么,讀者觀賞作品何嘗不是情不自禁的自我觀賞呢?由此,人們接受棗的心理其實(shí)十分簡(jiǎn)單。“棗”原來(lái)在人生世界中是一種大眾的樸素的人格,“花香味也不濃烈,浙江醇淡泊,似有似無(wú),溶化在空氣里”,人格的樸素在于它不夸耀痛苦,常常以平靜如常的態(tài)度面臨苦難。“棗”有如千萬(wàn)大眾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狀不驚人的生存,有如流動(dòng)在我們身邊的空氣、陽(yáng)光和水,它貌不驚人,然而驚人地隱喻了我們的存在本質(zhì)。蘇珊·朗格說(shuō),詩(shī)歌來(lái)自于假定。就是說(shuō),藝術(shù)源自生活中無(wú)法實(shí)現(xiàn)的因素。生活中的棗除滿足食欲之外,不可能給人帶來(lái)某種生存的驚喜,更不可能令人流連再三,但是,通過(guò)棗本身的重新“假定”,棗便移離于原本的物質(zhì)屬性,變成了一種精神,一種我們內(nèi)心早已渴求的東西。作者寫(xiě)作上的“由淺而深”,才得以完成。因此,作品最后“該怎樣開(kāi)花,該怎樣結(jié)果”的表達(dá),也超出了它生活意義和一般性的感恩戴德(這一闡釋意味著我們對(duì)作品的“二次閱讀”)。
作者系本色的鄉(xiāng)土詩(shī)人,該詩(shī)似乎更接近他一貫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樸實(shí)沉穩(wěn),遣詞用句注重鄉(xiāng)土背景及其意味。《棗》取之于鄉(xiāng)村山野,它的色彩和內(nèi)在氣質(zhì)自然無(wú)需人工的夸飾,而它的精神,則更如山澗溪水,來(lái)去并無(wú)急切的目的,一切都自然自在。要說(shuō)該作品語(yǔ)言上有何特色,我想蓋在其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