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金融城的成因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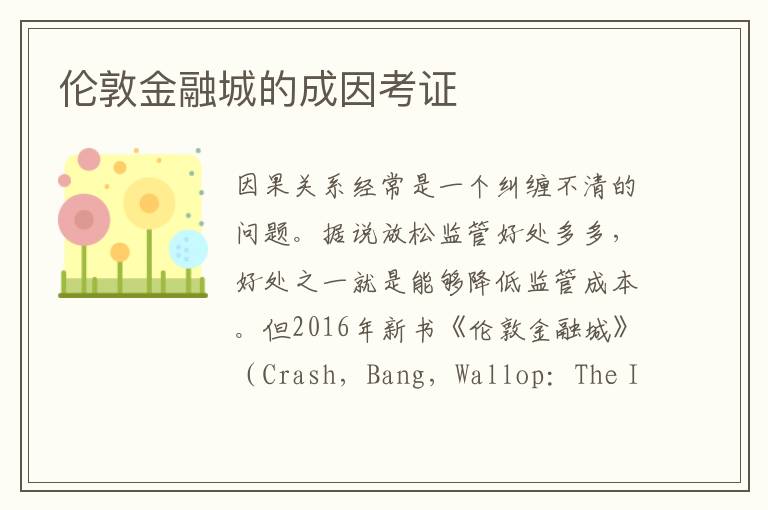
因果關(guān)系經(jīng)常是一個糾纏不清的問題。據(jù)說放松監(jiān)管好處多多,好處之一就是能夠降低監(jiān)管成本。但2016年新書《倫敦金融城》(Crash,Bang,Wallop:The Inside Story of London’s Big Bang and a Financial Revolu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似乎有不同的例證。1986年,英國全面放松金融監(jiān)管,但合規(guī)成本不降反漲:1986年倫敦金融城的合規(guī)成本是2000萬英鎊,但到1992年卻增加到9000萬英鎊。但該書作者伊恩·馬丁(Iain Martin)并沒有說明,合規(guī)成本增加是否有通貨膨脹的因素。
《倫敦金融城》英文原版封面
30年前,英國全面放寬金融監(jiān)管,動作兇猛、激烈,比作是宇宙大爆炸(Big Bang)。推出此舉之后,美國各投資銀行紛至沓來,爭相在倫敦擺攤設(shè)點。但馬丁認為,倫敦金融城并非必定勝出,歷史上就有反復。《倫敦金融城》試圖列出了倫敦金融城崛起的各種因素,包括偶然性因素和必然性因素。偶然因素包括:倫敦城的行業(yè)協(xié)會興起,有助于倫敦取代阿姆斯特丹的地位;中東產(chǎn)油國售油獲得的美元大量涌入歐洲,成為歐洲美元,為倫敦金融城增加了不少業(yè)務。
馬丁列出的必然性因素包括:倫敦位于紐約與東京之間,處于“交易的最佳時區(qū),且長于外匯交易和融資交易,還有百年機制框架”。不過,這些必然因素并非一成不變。比如,時區(qū)是有利因素,卻不是關(guān)鍵因素,甚至不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上海證券交易所與倫敦股票交易所(以下簡稱倫交所)一直在研究如何推出滬倫通,即兩家交易所的投資者可以異地進行交易。上交所與倫交所不在同一時區(qū),時區(qū)方面不僅沒有優(yōu)勢,而且有劣勢。香港股票交易所的高層領(lǐng)導曾經(jīng)得意揚揚地表示,不必擔心來自倫交所的競爭,時差過大就是倫交所解決不了的難題。2016年11月,倫敦股票交易所首次透露的初步設(shè)想如下:倫敦股票交易所精選倫交所上好的公司,在上海當?shù)亟灰讜r間內(nèi)在上海交易并結(jié)算,由倫交所指定的經(jīng)紀公司擔任做市商。上海交易所也選出上好的公司,在倫敦當?shù)亟灰讜r間內(nèi)在倫敦交易并結(jié)算。倫敦的投資者可以當?shù)氐慕灰讜r間內(nèi)買賣這些股票。這實際上是又設(shè)立了兩個交易所。
《倫敦金融城》是倫敦的金融史,故事是從頭說起。馬丁介紹了1519年出生的托馬斯·格雷沙姆(Thomas Gresham),倫敦首家交易所由其創(chuàng)設(shè)。馬丁稱格雷沙姆是“商人、探險者、金融設(shè)局者和土地開發(fā)商”。馬丁還引用了英國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問題:“格雷沙姆是竊國大盜,還是江洋大盜,是政治家,還是南海泡沫的弄潮兒。”斯威夫特揭示了金融大亨的矛盾身份,而這種矛盾的身份與其成就金融大業(yè)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并不清楚。斯威夫特看到了格雷沙姆成功的多面性,馬丁也看到了倫敦金融城成因的多面性,但兩人都不愿直面的一個因果關(guān)系是:一個國家是否會有國際金融中心,與該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密切相關(guān)。
倫敦金融城的崛起與英帝國主宰眾多亞非國家不無關(guān)系。而紐約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不無關(guān)系。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發(fā)橫財不富。倘若不是路有凍死骨,哪里來的朱門酒肉臭。勤勞可以溫飽,最多是小康水平,不可能發(fā)大財。個人如此,國家也是如此。但英、美人不愿意提及他們所獲得的不義之財,好像他們是靠勤勞致富的。
各種因素與倫敦金融城崛起的因果關(guān)系難以確定。證券市場的許多問題與其成因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也難以確定。比如,投資者索賠的訴訟中,華爾街的銀行作為被告經(jīng)常提出,即便被告做了重大虛假陳述,即便原告合理依賴了這些陳述而且蒙受了損失,原告仍然不能勝訴,因為原告所購股票是因為股市價格整體下跌所致。換言之,被告所做虛假陳述與原告損失之間并沒有因果關(guān)系。美國法院也時常接受這種觀點。但換一個問題,華爾街的銀行又一口咬定存在因果關(guān)系。華爾街推銷股票的一個理由是,上市公司會不斷成長壯大,其股票價隨之增加。但通過量化寬松不斷為證券市場輸送資金,則股票價格自然會上升,經(jīng)濟體量不斷放大,股票價格也會隨之上升。水漲船高并不說明船好。股價上升與公司是否成功之間并無必然的因果關(guān)系。股價本身上升也不足以證明上市公司的價值。當然,《倫敦金融城》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考證因果關(guān)系,馬丁只是借助因果關(guān)系的邏輯來講述故事:虛構(gòu)作品和非虛構(gòu)作品都必須有主線,而主線離不開邏輯關(guān)系,甚至邏輯關(guān)系本身就可以是主線。
不講邏輯關(guān)心,不講因果關(guān)系,實踐上也是前后矛盾。倫敦的前任市長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就是自相矛盾,前后立場不一致。鮑里斯·約翰遜大力鼓吹脫歐,并因此而爭得了外交大臣的交椅。但據(jù)好事者后來考證,鮑里斯·約翰遜先前曾經(jīng)悄悄支持過留歐。不講邏輯就是前后立場矛盾。這位市長大人——現(xiàn)在的外交大臣——并不一定是要騙人,怕是自己也不知道想要做什么。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有不同的動機,動機不同,即便是同一主體(“主體”是法律術(shù)語,泛指自然人、法人和任何實體)做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動機。2015年歐洲央行推行量化寬松,德國默克爾當局多有微詞,2016年3月歐洲央行搞經(jīng)濟刺激,德國的默克爾當局又有微詞。但彼微詞與此微詞不同。2016年歐洲銀行貶值歐元,默克爾當局是真反對。德國存款者和小銀行深受其害(利差是小銀行的重要收入來源)。但2016年德國經(jīng)濟增長已經(jīng)放緩,低息刺激對德國未必不好。但2015年一百萬難民由巴伐利亞涌入德國,巴伐利亞人深為不滿。巴伐利亞居民傳統(tǒng)上支持默克爾所在的基督教社會黨聯(lián)盟,但對歐元一向深惡痛絕。默克爾集團生怕巴伐利亞人倒戈,所以攻擊歐洲央行,試圖轉(zhuǎn)移斗爭大方向。
《倫敦金融城》的作者馬丁是記者出身,先后為《華爾街日報》和《每日電訊》等報紙工作過。《倫敦金融城》由Sceptre出版社出版,全書352頁,精裝版售價25英鎊。馬丁還著有《心想事成:引爆英國經(jīng)濟的弗雷德·古德溫、蘇格蘭王家銀行及其人們》(Making it Happen:Fred Goodwin,RBS and Men Who Blew up the British Economy)。許多有關(guān)國際金融市場的英語力著出自記者出身的著者,其中包括:介紹華爾街內(nèi)幕交易的《賊巢》(Den of Thieves),作者詹姆斯B.斯圖爾德(James B. Steward);介紹2008年金融危機內(nèi)幕的《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ll),作者安德魯·羅斯·索爾金(Andrew Ross Sorkin);介紹私募股權(quán)基金并購業(yè)務的《門口的野蠻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作者布賴恩·伯勒(Bryan Burrough)和約翰·赫利亞爾(John Helyar);介紹安然丑聞內(nèi)幕的《愚人的陰謀》(Conspiracy of Fools),作者庫爾特·埃誠瓦爾德(Kurt Echenwald);介紹美國銀行收購美林的《超大銀行的垮臺》(Crash of the Titans),作者格雷格·法雷爾(Greg Farrell);以及介紹黑石的《資本之王》(King of Capital),作者戴維·凱里(David Carey)和約翰·莫里斯(John E. Morris)。至少可以說,每次出現(xiàn)金融危機或金融丑聞(兩者經(jīng)常聯(lián)系在一起),著書評論的大多是記者出身的作者。《倫敦金融城》一書也有危機背景,英國脫歐之后倫敦金融城暫時遇到了信心問題,一些外資已經(jīng)撤出或表示要撤出倫敦。而馬丁的意思是,倫敦幾起幾落,其興衰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各路朋友大可少安毋躁。
倫敦的金融行業(yè)十分重要。2016年7月初,全球五分之一的貸款是在倫敦發(fā)放;倫敦的美元交易量是美國的兩倍;倫敦歐元的交易量是歐元區(qū)的兩倍;全球18%的對沖基金設(shè)在倫敦,13%的私募股權(quán)基金設(shè)在倫敦。了解倫敦金融城對我國金融業(yè)也很重要。倫敦證券交易所與上海交易所正在商談設(shè)立處的聯(lián)合交易。此外,香港證券交易所(簡稱港交所)收購了倫敦金屬交易所。港交所與上海證券交易所對接交易,還要與深圳證券交易所對接交易。可以說,倫敦金融城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我國的金融市場。《倫敦金融城》一書有助于了解倫敦的金融行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