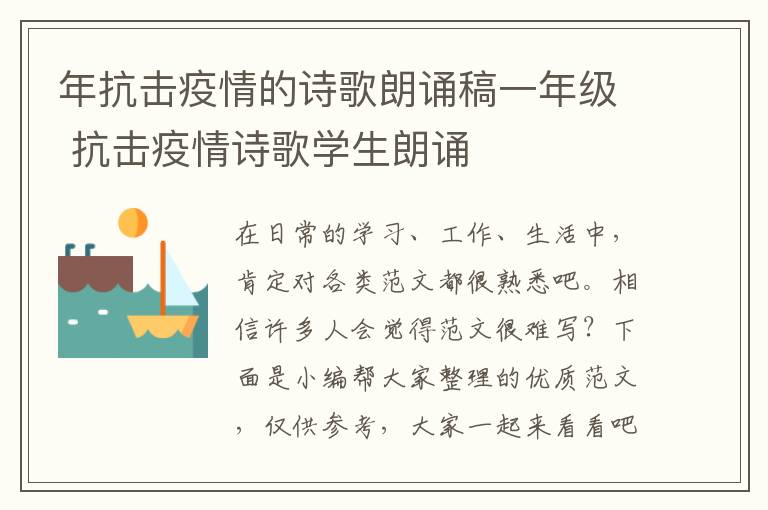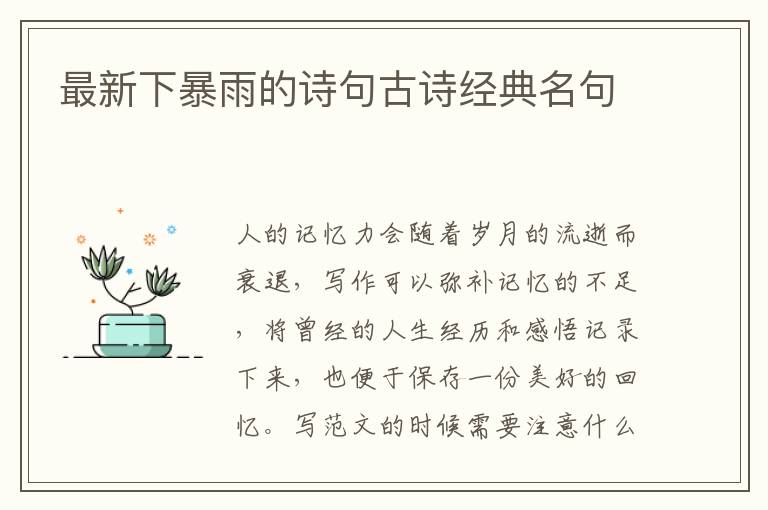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一泓被叫做青海的湖(外一篇)》文秋菊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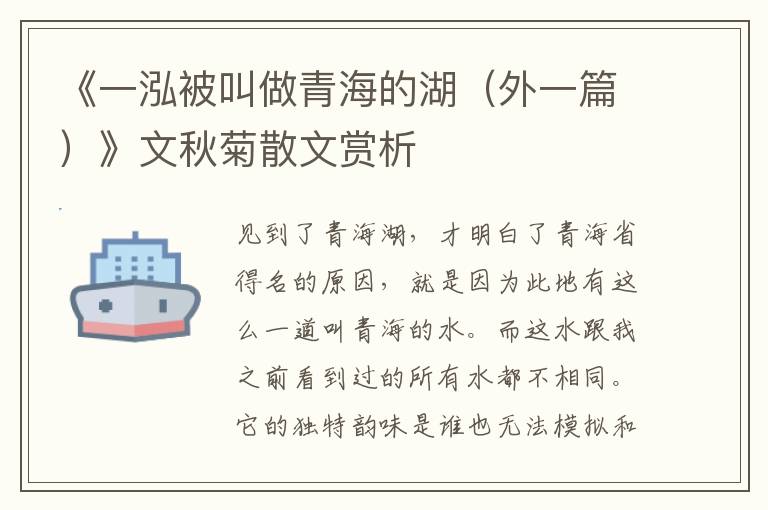
見(jiàn)到了青海湖,才明白了青海省得名的原因,就是因?yàn)榇说赜羞@么一道叫青海的水。而這水跟我之前看到過(guò)的所有水都不相同。它的獨(dú)特韻味是誰(shuí)也無(wú)法模擬和克隆的。看來(lái),青海湖首先應(yīng)該是海,其次才應(yīng)該是湖。
看到它之前,曾聽(tīng)人談?wù)撉嗪:f(shuō),那寺,那鮮花,那小舟上光著腳丫的蕩漾……于是,在我的心目中,就一直以為青海湖只是炕桌上的一面小鏡子,可以把玩,可以臨摹,可以照影,可以嬉戲。
然而,見(jiàn)到之后我才明白,青海湖根本就不是可以散發(fā)弄扁舟的小溪小水,她的宏大、她的雍容、她的清粹……讓你久久合不攏嘴。那種美,是清涼的,是幽深的,是圣潔的,是透徹骨髓的。如果要用季節(jié)來(lái)描摹她的話,我只想說(shuō),她是屬于秋或者冬的,秋則應(yīng)是清秋,冬則應(yīng)是白雪皚皚的冬。
我感受過(guò)黃河的厚重、長(zhǎng)江的奔騰、九寨的瑰麗、漓江的秀美,但青海湖卻讓我屏住了呼吸。我唯恐自己的濁氣熏染了她,我擔(dān)心自己的絮叨驚擾了她。
我無(wú)法想象,在這片疾走都會(huì)感覺(jué)困難的土地上,怎么會(huì)有這么一片碩大的柔亮清凈。她安靜悠然于這方天空下,如果不經(jīng)意,你會(huì)以為是頭上的這片高而遠(yuǎn)藍(lán)而清的天,跌落于此。遠(yuǎn)遠(yuǎn)地,汽車上如果沒(méi)有導(dǎo)游的指點(diǎn),你一定會(huì)以為這是和無(wú)垠土地相接的藍(lán)天。因?yàn)樗龑?shí)在是太透徹太宏大太安靜了,而不像別的海,幾里地就可以聽(tīng)到潮聲的喧囂。
著鮮艷藏服的老人小孩、潔白的牦牛,只是插圖。那安靜無(wú)垠的、湛湛幽幽的、醇正的青,才是主色調(diào)。那些興奮的叫賣、那些為了蠅頭小利而斤斤計(jì)較的嘈雜,仿佛被消了音一樣,變成了清風(fēng)和陽(yáng)光,在天空下散發(fā)著圣潔干凈的光。
沒(méi)有寺廟,沒(méi)有經(jīng)幡。只有無(wú)垠的天高遠(yuǎn)著,只有無(wú)垠的地平坦著。站在高原之上卻看不到高原,只有這天、這地、這水,仿佛是盤古的板斧劈開(kāi)天地之后的初始,純真原始。
在這里,你無(wú)法找到時(shí)間運(yùn)行的痕跡,似乎亙古如此。
悄悄地,不要叫喊。請(qǐng)讓我一個(gè)人,靜靜地在這叫做青海的湖邊坐一會(huì)兒。讓我慢慢地、仔細(xì)地捋一捋。讓我思一思走過(guò)的路,想一想見(jiàn)過(guò)的人、學(xué)過(guò)的知識(shí)、讀過(guò)的書、思考過(guò)的問(wèn)題,看看能有什么和這叫做青海的湖碰撞,看看能有什么能和這叫做青海的湖匹配。
青出于藍(lán)而勝于藍(lán),那么這比藍(lán)還藍(lán)的則叫青嗎?這方青凝,恰似天之眼地之目,沉靜靈動(dòng)著腳下的大地,柔和清冽著這方自然。撥開(kāi)烏云見(jiàn)青天。青天大老爺?shù)那啵瑫?huì)不會(huì)就是這么一種境界:古樸原始,悠然清靈,還人間以寧?kù)o,還心靈以澄澈,公平而且透明?
讀著佛家,一直體會(huì)不來(lái)“自在”的境界,然而,站在這里,我似乎有所悟。“自在”或許就是超然,毫不附著的超然,或許就是一種不著痕跡的融合。青海湖是獨(dú)立青澹的,似一位遺世的高人。但是它和這天這地融合得又是那么的無(wú)懈可擊。就如同一個(gè)人的身體,缺不了胳膊也缺不了腿,它不僅是眼睛,也應(yīng)該是前胸后背或者身體的任何一部分。融于人群,而不失掉自我;堅(jiān)持自我,而不孤高自賞。像滴水融于大海,像清風(fēng)融于宇宙。這樣或許就 “自在”了。
站在青海湖邊,沐著清風(fēng)和陽(yáng)光,內(nèi)心充溢的是快樂(lè)、寧?kù)o和滿足。像嬰兒的第一次啼哭,我深深地飽滿地吸上一口氣。這氣是青海湖的,也是湖邊鮮花的,更是島上鳥(niǎo)群的,還是這方藍(lán)天和大地的,更是湖邊潔白的牦牛和鮮艷淳樸的人的。
站在這里,沒(méi)有什么陰霾忘不掉,沒(méi)有什么坎坷填不平。因?yàn)檫@是一泓被叫做青海的湖。
拋開(kāi)喧囂,遠(yuǎn)離浮華和塵埃,我想要走進(jìn)青海湖的心里,然后,過(guò)濾,沉靜,冥想……
一個(gè)人,終其一生,其實(shí)都是在尋找家園。那家園應(yīng)該是柴米油鹽之上的升騰,應(yīng)該是物質(zhì)的減肥或消失,只留精神或靈魂的長(zhǎng)存。就像眼前這偶遇的青海湖,青得讓人心疼,靜得讓人心醉,清凈得讓人不忍離開(kāi)。于是我久久地盤桓在三百多公里的青海湖邊,希望化為這湖中的一尾魚(yú),將自己的三生都交與……
成都草堂,那一間茅屋
去成都是抱著補(bǔ)救的心態(tài)匆忙前往的。在漢中呆了十七年,離開(kāi)后,忽然發(fā)覺(jué)連距離最近的歷史名城都沒(méi)有去過(guò)。一時(shí)間,惶恐遺憾后悔等復(fù)雜情感不一而足。所幸老天成人之美,在離開(kāi)一年半之后,又得以回來(lái)。因?yàn)樾睦锩靼祝舜位剞D(zhuǎn)或許也只是兩三年的工夫。于是,填補(bǔ)遺憾就成了返回之后的重要事情。
對(duì)于不同的人而言,成都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在我心里,沒(méi)有草堂,沒(méi)有那一間茅草屋,成都便什么都不是。所以,成都之于我,牽心的全在于草堂,那一間住過(guò)字子美名杜甫的唐代詩(shī)人的茅屋。
其實(shí),之前的之前,對(duì)草堂的向往,本是懷著仰望拜謁的情感的。然而,當(dāng)我站在那被秋風(fēng)所破的茅屋前時(shí),那一瞬間,詩(shī)人的一生遭際、顛沛流離、艱難輾轉(zhuǎn)讓我熱淚涌動(dòng),感同身受。那個(gè)瞬間,我面前的不是名冠今古的詩(shī)圣,而是鄰家的老人,在怒號(hào)的秋風(fēng)中,老而無(wú)力,倚杖息。
那些環(huán)繞在詩(shī)人身上的一切光環(huán)全部消逝,只有悲苦,深重的悲苦留了下來(lái)。此刻,我離詩(shī)人是那么近。在唐代詩(shī)人中,不,是在我讀過(guò)的所有古人中、在我走過(guò)的所有名勝中,沒(méi)有哪一個(gè)能像此刻這樣深深地揪緊我的心。
我沒(méi)有走進(jìn)茅屋,我知道那里早已不復(fù)舊時(shí)模樣。我只是站在門前兩米多遠(yuǎn)的地方,靜靜地站著,聽(tīng)?wèi){“八月秋高風(fēng)怒號(hào),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詩(shī)句在心頭翻騰,聽(tīng)?wèi){靈魂深處的那股潮濕,那股為諸如“親朋無(wú)一字,老病有孤舟”等許多熟悉的詩(shī)句所洶涌的心,熱辣辣地酸楚著。
據(jù)說(shuō),草堂是詩(shī)人人生歷程中唯一有亮色的地方,唯一可以稱其為居所的地方。可它也被秋風(fēng)秋雨席卷浸泡,苦寒至此已極矣。然一聲“嗚呼!何時(shí)眼前突兀見(jiàn)此屋,吾廬獨(dú)破受凍死亦足”,憂患、仁慈至此亦已極矣。
這就是詩(shī)圣啊!
圣原來(lái)就該是超越自我遭際、痛及天下或人類的情懷。
只是,公元761年怒號(hào)的八月風(fēng)早已不見(jiàn),茅屋頂上的茅草早已不再隨風(fēng)狂舞,只發(fā)出風(fēng)雨不動(dòng)安如山的色澤。而浣花溪的水,也是清澈透亮,寧?kù)o安謐。那個(gè)曾經(jīng)在這里喜悅過(guò)、憂愁過(guò)的詩(shī)人,那個(gè)曾在大半個(gè)唐朝土地上流浪過(guò)、漂泊過(guò)的身影,如今只留下了石頭雕成的硬瘦。
詩(shī)人一定是硬瘦的,這是石雕師的聰明,也是世人的認(rèn)可。在唐朝的詩(shī)人中,還有誰(shuí)能比杜甫更飽受戰(zhàn)亂,更顛沛流離,更挨餓受饑?
可硬瘦的外表并不代表內(nèi)心的枯瘦。即使居無(wú)定所,即使飄飄似天地一沙鷗,但詩(shī)人的心卻是濕潤(rùn)豐盈、充實(shí)富裕的。他對(duì)家國(guó)親人,對(duì)天下所有被時(shí)代所左右的生命,對(duì)他們的愛(ài)及關(guān)切之情,豐裕著他的人生。他那瘦及骨肋的身體,在顛沛流離、食不果腹中,以仁愛(ài)的目光將唐朝以及唐朝之后的所有時(shí)空覆蓋。
離亂的朝代,動(dòng)蕩的時(shí)局,并不缺少夜夜笙歌的歡飲。唐王朝的大殿里,也曾是風(fēng)雨般密集的紅衣綠袖,在霓裳羽衣下翻飛著無(wú)盡的風(fēng)流。長(zhǎng)安啊長(zhǎng)安,到底讓誰(shuí)長(zhǎng)治久安了?倜儻的天子,滿紙生花志滿意酬的文臣武將,他們迷離恍惚的眼睛看不到那么遠(yuǎn)。他們不在乎誰(shuí)能“致君堯舜上,能使風(fēng)俗淳”,別人的理想與他們何干。他們感受不到凍死之骨的寒徹。
甘肥真的會(huì)使人眼界狹窄?! 因?yàn)樗械捏w驗(yàn)全聚于感官,無(wú)暇他顧本是情有可原。那些也畢竟只是人而已!
可硬瘦的詩(shī)圣卻不知曉,只是一味地向西向南向北奔走、突圍,然后,落腳于浩淼的水上,順流而下逆流而上地尋找著,逡巡著。可那柔軟綿長(zhǎng)的水,就像某種無(wú)法把握的命運(yùn),更像大唐的霓裳羽衣舞,飄蕩著糾纏著,遮蔽著掩藏著,更是詭異著。
我不明白生于中原的你何以對(duì)水如此鐘情。是不是前半生的經(jīng)驗(yàn)使然?或許是你覺(jué)得無(wú)論多么洪大浩蕩的水,總是有方向的,總是執(zhí)著向前的,總是會(huì)到達(dá)的。于是就有了那一葉小舟,有了那一葉小舟上的一家老小,有了那個(gè)拖著殘軀、又老又病,終究沒(méi)有靠岸的你。
黃昏開(kāi)始降臨,成都的細(xì)雨亦開(kāi)始輕輕飄落。
成都草堂,那一間茅草屋,在微雨中漸漸變得模糊。最終成為一種寫意,淡淡的,但分明是橫撇豎捺的,烙在了我的眼底,烙在了我的心里,滋潤(rùn)著我的焦躁,也滋潤(rùn)著我的傷感,讓我悵惘的腳步欲罷不能,頻頻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