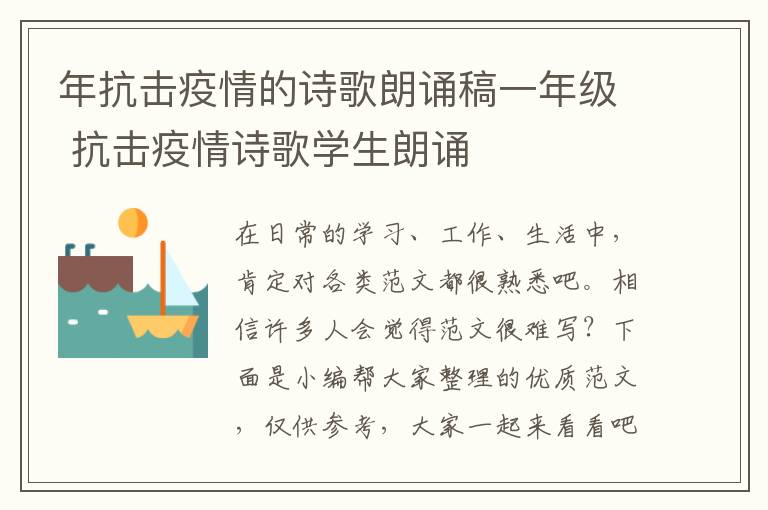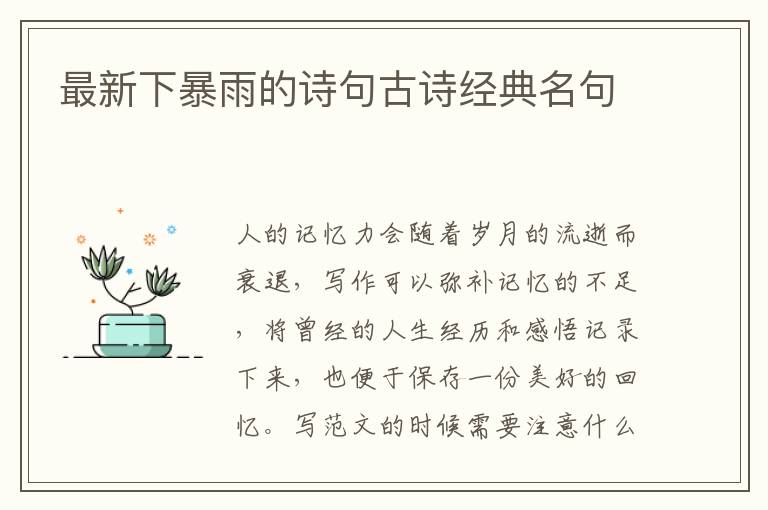徐國平《再回老家活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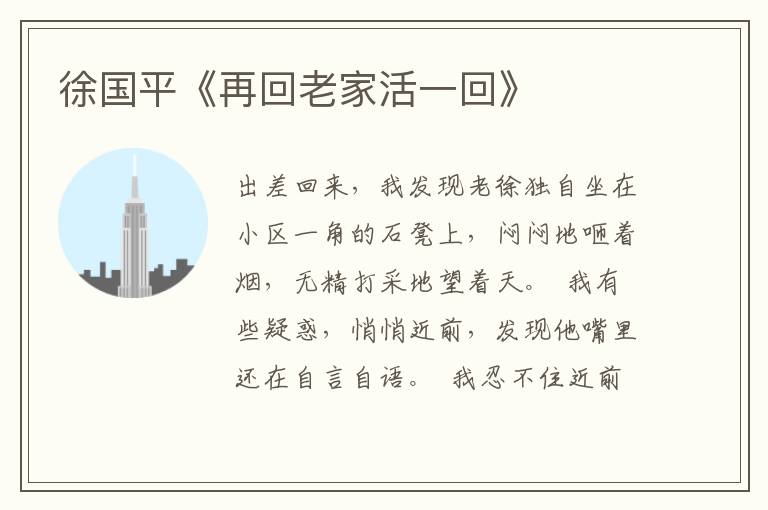
出差回來,我發現老徐獨自坐在小區一角的石凳上,悶悶地咂著煙,無精打采地望著天。
我有些疑惑,悄悄近前,發現他嘴里還在自言自語。
我忍不住近前喊了一聲,老徐,咋了?
老徐慢騰騰地將頭一歪,瞥了我一眼,有氣無力地說,快要死了!
我想,老徐最近心情不好,準是開玩笑。
老徐跟我隔著一棟樓。小區的業主,大都來自不同的地方。平日,我極少搭話。自從老徐來了,一聽口音親切,聊了幾句,既是同姓,又是同鄉,兩人就熟了,而且談得很投機。他比我大幾歲,我就喊他老徐。
老徐說他是被逼無奈進的城。老伴五年前就病死了,兒子一家都在城里工作。
他老家早就沒幾個人住了,可他一直舍不得老屋和那盤土炕。鄉下人有三寶:老婆孩子熱炕頭。老婆沒了,孩子走了,他就剩下熱炕頭了。
我笑他,城里生活多舒坦,土炕有啥貪戀的。
最初老徐還一臉幸福,不住地給我絮叨進城的所見所聞,說自己吃喝拉撒都不出屋,就跟圈里養的豬一樣,半個月就長了十多斤的膘。
只是,過了個半月,老徐就明顯有些不適應了。再見面就跟訴苦一樣,說他在鄉下一人浪蕩慣了,雖然兒子兒媳沒反感,買菜不用他,煮飯也不許他動手。可是他煙不能隨意抽,痰不能隨地吐,尿也不能隨意撒。小孫子聰明伶俐,見老徐一天到晚無所事事,也對他大呼小喝。兒子少小離家讀書,爺倆也沒啥共同語言。就是同一張桌子上,或者吃個飯,不過兩句話。媳婦干脆借口工作忙,早出晚歸。問她啥都是嗯嗯幾聲就算了。他在家就像一個多余的木頭,放在哪里都會礙人的手,就跟蹲監坐獄一樣難受。
老徐開始懷戀老家,那薄薄的炊煙,悠長的小巷,潺潺的小溪;還有一到秋天就掛滿了枝頭的金燦燦的柿子……更重要的是那些熟悉的老伙計。吃完晚飯,幾個糟老頭蹲坐街頭,絮絮叨叨地說著村里的長短。那條溫順的老狗,也親熱地搖著尾巴走來走去。每天一早,挑兩擔清涼清涼的水,到自家翠綠的菜地里潑上幾大瓢,好像干了活,才有理由去吃個早飯。
我總是勸慰老徐,要學會適應生活,再說你就這么一個兒子,人老了,不跟著他還能跟誰啊?
這時,老徐見我站在跟前,將余燼的煙頭,扔到腳底踩了一下,長嘆了一口氣,透出實情。說人老了,別的養不成,病卻好養。飯吃得好好的飽飽的,這些日子肚子卻隱隱作痛,還不停地打嗝反酸,人也像撒了氣的皮球見風就瘦。兒子催了幾次,要帶他去醫院檢查,他怎么也不肯去。最后,他痛暈了,送到醫院一檢查,竟是胃癌晚期。
我聞之一怔,仔細打量老徐,就見他突然間老得就像一截枯黃的木頭,兩只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腰也佝僂了起來。
我連忙勸老徐,不要怕,趕緊住院治療,還有希望啊。
老徐搖搖頭說,這把年紀了,死不可怕。住了幾天院,看到病房里那些渾身插滿管子的病人,我害怕了,這不是躺著活受罪嗎?我不能就這樣死在這里,我要回老家,死也死在自家的炕頭上。
我有些擔憂,試探著問,這樣能行嗎?
果然,老徐的兒子不同意。可老徐倔上勁兒不住院不治療,兒子無奈之下還是同意了。
老徐走的時候,我去送他,他一臉坦然地說,在老家要么重生,要么葬身在此。
沒想到,老徐在老家竟然學會了微信,一直跟我聯系。他說老屋一切如故,土炕還能走煙。人也沒閑著,先是砍掉了影響通風透光的榆樹、楊樹、柿子樹,種上桃樹、蘋果樹、石榴樹。勞累一天,飯也吃得香,渾身也舒坦,一個人優哉樂哉。轉眼一年就過去了,老徐雖然清瘦,面色卻紅潤了許多。
兒子帶老徐去市醫院做檢查,原來如山壓頂的癌癥指標竟然都趨近于健康值。醫生驚嘆不已,問他是不是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仙丹啊?
我也替老徐高興。老徐非要帶我去他的老家瞧一瞧。
我早就想去探探老徐的仙府圣地。我踏進院門,眼前好一個碧綠的五族大世界:攀藤一族是葫蘆、葡萄和絲瓜;地潛一族是山藥、胡蘿卜、土豆;鮮果一族是大桃、蘋果、石榴;草莽一族是野菜、黃花、金銀花。
土院里的一切都是原生態的,土坯房、柴火灶、雞窩、茅坑,窗臺晾著黃花、金銀花、苦菜根。
須臾飯熟,一桌莊稼菜勾人食欲。老徐特地烀出一鍋焦黃干脆的貼餅子,冒著熱氣的面倭瓜,一股股植物的本味勾起我許久以前的記憶。飯后,我搶著刷碗,那刷碗后的水沿著一條小溝緩緩流到果樹下。
黃昏,藤架下,兩人攀談。老徐說他這一年啥都看開了,一個人雖孤單,可天天有事做,心里充實,沒煩惱,活一天就當賺的;吃自己種出來的寬心菜,喂出來的土雞蛋,吸幾口大糞干味道的新鮮空氣,再放聲哼上幾句。
說著,老徐一仰脖,真就放聲唱了起來:“我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
一陣晚風拂來,輕柔舒爽,土院外伴來幾聲狗吠和蟲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