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諾依《西苑紅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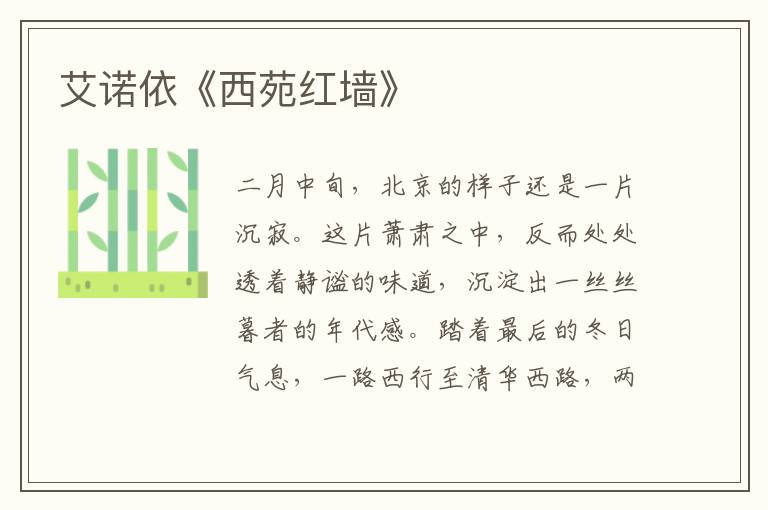
二月中旬,北京的樣子還是一片沉寂。這片蕭肅之中,反而處處透著靜謐的味道,沉淀出一絲絲暮者的年代感。
踏著最后的冬日氣息,一路西行至清華西路,兩旁青松翠柏立于門前,串串大紅燈籠掛于枝上,孩童穿梭其中斷斷續續傳來銅鈴般的嬉笑聲,靜立此地的小小門洞里面,居然有這么一座舉世聞名的園林。
上次來探訪圓明園,大致于高中時代,似乎更傾心周邊的百年名校,那時雄心壯志的少年忽略了它的存在。隨后,逃不開北海的熱鬧、景山的高處、后海的日落,尤其是頤和園的冬雪與夏荷,甚至乘龍船自北京展覽館后湖途徑紫竹院、萬壽寺終至頤和園,游經慈禧太后最喜歡的河道線路,賞長河兩岸桃紅柳綠。這座城的每一處都埋下往事,鎖住年華,余暉中的側影,無法回望的故事令人動容。
當流連于這些繁華盛景時,與慕名前往、游客如織的愛國主題教育景點擦肩而過。從印象中拼湊不齊、碎石滿地的西洋樓,到后來看過圓明園復原微縮景觀,內心驚詫于它的輝煌與魅力,但那時仍覺得已然欣賞不到的美景,何必至此一行。
雖然沒有找到任何理由來訪,沒有帶著期盼的心情前往,然而,圓明園,這座“萬園之園”自始至終帶著它百年來的浴火歷劫、寵辱不驚,把真實的一面展現在世間。人人愛美,人人躲避傷痕,落雪后一墻之隔的頤和園到處可見扛著攝影設備的記錄者,盛裝出席在鏡頭前的無數面孔。這里的沉默,就像這里花未開、樹在眠,冬日大片大片裸露的土地一望無邊,沒有樓臺亭閣、巷陌勾欄,踏在厚土之上,看著腳下殘留的地基,幾根殘留的柱子曾托起一個人間仙境,此處的長廊,彼處的高臺,逐次從腳底的廢墟里拔地而起,用大理石、漢白玉、青銅和瓷器精雕細刻,用洋漆鋪染,上了琺瑯、鍍金,飾以琉璃、脂粉,披上綢緞、綴滿寶石,一座座花園、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噴泉,將詩情畫意融化與千變萬化的景象之中,正是這里,凝聚六代帝王心血的地方,幾乎是神奇的華夏人民運用想象力創造的一切。它的神秘就在于它的不存在性和不可復制性,毀滅與存活,這顆東方明珠同曾經馳騁在白山黑水之間征服了北戎南蠻的馬背上的王朝,一起湮沒在歷史的塵埃里。
壯麗的宮殿,秀美的園林,無數的珍寶與藝術品,皆付之一炬。來此之前,我感到它的骨骼似是冷冰冰的石頭,來此之后,那些靜臥的巨石荒涼而寂寞,熊熊烈火中被刺傷、受污辱,彷佛廊柱殘破的一角還留有燃燒后的余溫。那恬淡秀美的武陵春色在哪里?那曲橋塔影的平湖秋月在哪里?那笙歌管弦的宴樂生平又在哪里?昔日的繁盛,被揉碎在眼前才更覺悲痛。
從長春園行至西洋樓的分岔口處,原本朝著海岳開襟的水邊前行,右手邊有綿延的土丘,隨著幾位游人也爬上一探究竟,竟可從高處俯瞰西洋樓的景觀群,大水法、遠瀛觀、海晏堂、水力鐘噴泉、方外觀、養雀籠直至萬花陣。殘垣斷壁之中,萬花陣已被修復的頗為完整,這是圓明園內一座中西結合的迷宮,由陣墻、中心庭院、碧花樓和后花園組成。盛時,每當中秋之夜,清帝坐在陣中心的中式涼亭里,宮女們手持黃色彩綢扎起的蓮花燈,尋徑飛跑,先到者便可領到皇帝的賞物,故又稱為黃花陣,雖然從入口到中心亭的直徑距離不過三十余米,但因為此陣宜進難出,容易走入死胡同,清帝坐在高處,四望蓮花燈東流西奔,引為樂事。我們遇到這么奇思妙想的地方,也不禁莞爾一笑。
類似于此的地方,還有園中的福海,這里相當于北海公園的水面。湖水平靜如明鏡,清綠似翡翠,映照著怪石叢林,和煦暖陽,萬點金光,燦爛奪目,湖水環繞著蓬島瑤臺,島上亭臺樓閣典雅秀麗,碧水蕩漾在群山之中,小橋若彩帶與群山相連,一片湖光山色美不勝收。每于端午佳節,清帝在此舉行傳統的龍舟競渡活動,七月十五日夜,清帝于此觀賞河燈,冬日結冰后,清帝乘坐冰床在福海賞游,一路留下歡聲笑語。也恰是有了遼闊的水域,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由于圓明園面積太大,景點分散,水面開闊,才使一些偏僻之處和水中景點幸免于難,但時至今日,園內景色依然能觸目驚心地體會到“夷為平地”四個字的深刻含義,更為重要的是,火燒圓明園的真正概念,不僅是火燒圓明園,而是火燒京西皇家的萬壽山、玉泉山、香山三山,清漪園、圓明園、暢春園、靜明園、靜宜園五園,焚毀的范圍遠遠比圓明園大得多。歷史的車輪吹散籠罩在北京城上空遮天蔽日的黑云,碾碎愚昧和野蠻,我們愿意歷史朝哪邊走,我們又在讓歷史朝哪邊走?
離開之前,我在岸邊停駐良久。
庚子初年,一場突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大地,圓明園中沒有了絡繹不絕的游客,口罩隔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原本籌備元宵燈會的諸多裝飾物散落在湖面、樹間,大片空地的掛繩上,片片燈謎紙條在風中瑟瑟抖動,它們已等不來答案。憶起去年此時,我與先生沿著老北京中軸線,從景山公園一路步行至鐘鼓樓回家,處處洋溢著熱鬧歡樂的氛圍,吃食是藏著內心深處的情感寄托,街邊裹著厚棉襖老人懷里是插滿糖葫蘆的桿子,透明的冰糖薄薄地包在那一顆顆誘人的紅果上,紅寶石般凝聚出小小的光點,望著望著,甜甜的滋味已蔓延至舌尖,也巧遇百年老字號的手工元宵,凝固著千萬個祝愿和溫暖,即使元宵的口味早已搶購的所剩無幾,也甘愿買一些嘗個鮮。在此之前,為了沾沾喜慶,我們首先前往景山公園猜燈謎,陽光明媚的晌午,人們紛紛在漂亮的花燈前合影留念,行人駐足在樹與樹之間,三三兩兩的結伴交流,也有的人拿起手機在網上查閱,猜到謎底的題目需要記住編號,駐留時間長了還會感到一絲涼意,先生說這是不能太貪心。
于是揣著想好的謎底,我們便前往了兌換處,一路思考著其余未猜出的謎語,討論著有沒有猜謎的竅門。兌換處的門口早已排起長長的隊伍,大家都摩拳擦掌的期待著,有的人手里已經領到了禮品,再次排隊來尋找新的答案。所有正確答案都在工作人員查詢的冊子上,輪到我進入屋內,每個毛孔都不自覺地緊張起來,好似回到了學生考試揭曉成績的一刻。最終還是先生答對了,獎品是紅彤彤的手提燈籠,我小心翼翼地提在手中,沿途吸引不少孩子們好奇又羨慕的目光,我們商量著,明年等寶寶大一點,也帶她來感受元宵節的氣氛。只可惜,盼著盼著,誰也沒有料到疫情蔓延,美好的計劃瞬間變成了空談。
踏雪尋梅,月色嬋娟。二月的北京城有自己專屬的記憶,元宵燈會在景山,在圓明園,在一座座紅墻之內,古往今來,人們驅逐黑暗,用燈籠祈許光明,驅魔降福。望著結冰的湖面,惡性放在歷史的鏡像前,人類與人類之間,人類與自然之間,放大的欲望掠奪著生靈,巨大災難籠罩著無數個你我,生與死隔著薄薄地一扇門,生命的脆弱是絕對的,生命如石的頑強是相對的,忽而升起“后人視今,亦如今之視昔”的無限感慨。歷史往往給人類生動而鮮活的謎面,我們必須自己作出解答。我們需要怎樣的城市,我們如何對待腳下的土地,敬畏是每個人內心設立的一道底線,這種敬畏的人格素養基礎就是尊重。
落日余暉,水波粼粼,蘆葦蕩漾,野鴨成群,黑天鵝時而優雅地旋轉身子,時而俯仰頭顱,野鴨游于水面而立于冰面,水有水的優點,冰有冰的良處。干枯的蓮蓬歪歪扭扭,隨手撿拾一支,卻有別樣的韻味。似是這座園林的寫照,荷花盛景之美留在人們心間,曾天真地在其間雀躍,曾癡迷地在其間沉吟,但更多的時候,忍受那些寒冷和潮濕,那些無奈與寂寥,并且以晨光熹微的期盼度日。鮮花凋落,歲月翻過,生命已成暗褐色的蓬頭,依然擁有獨樹一幟的古樸,依然保持著出淤泥而不染的風骨。
后來,我把它帶回,放置在書桌,閑來煮茶半曲瓊瑤,觸碰枯蓬的脈搏,常常憶起那一抹的悲涼,常常凝視那一處的滄桑。
作者簡介:艾諾依,1990年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先后創作詩集《山河映萬朵》、報告文學《追光者》、散文集《且來花里聽笙歌》,曾獲冰心散文獎,《讀者》新媒體年度最受歡迎作者獎,編劇作品獲全國政法題材優秀原創劇本獎等。魯迅文學院第36屆作家高研班學員,老舍文學院第3屆作家高研班學員,現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