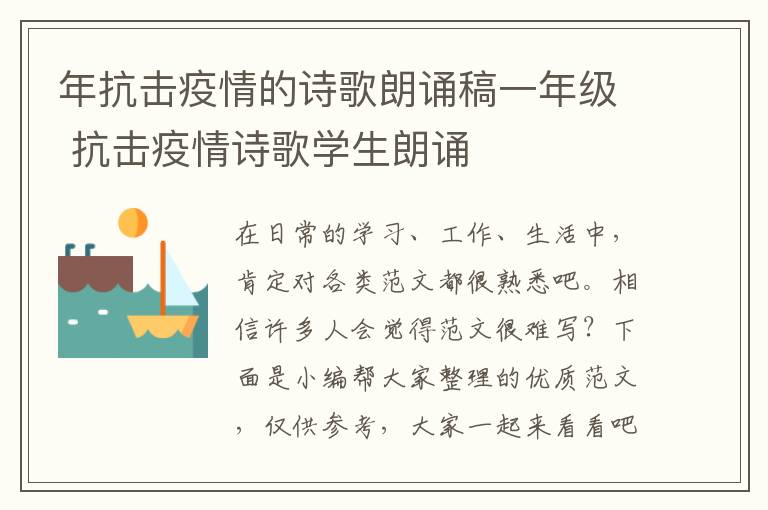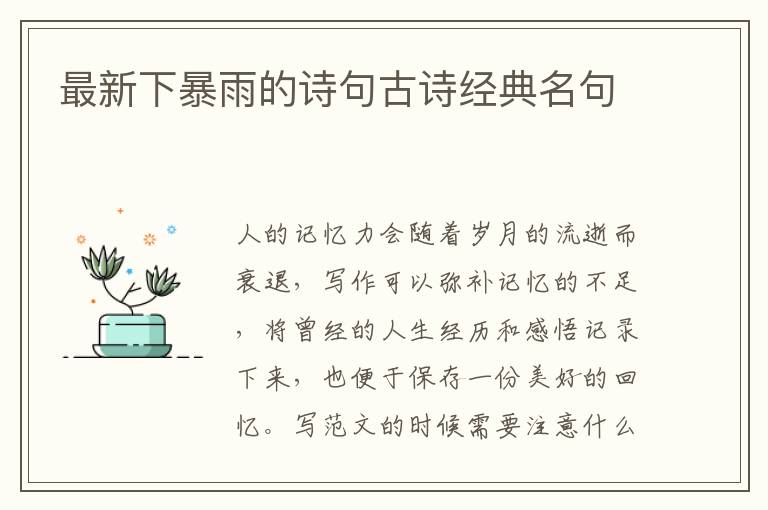康志剛《將軍還鄉》

老人回來那天,一大早,天上飄起蒙蒙小雨,空氣里彌漫著新鮮的土腥味,還有小草淡淡的清香。
上午九點,兩輛小汽車駛過濕漉漉的街道,停在了村委會大院。雨突然停歇了,露出一大片湛藍的天,陽光灑滿了大地。
第一個從車上下來的,是縣委宣傳部的王部長。他拉開后面的車門,非常小心地攙扶著老人下車。
戴一副眼鏡,有幾分斯文的劉鄉長從另一輛車上下來,他向迎候在院里的村干部們介紹客人。其實根本不用介紹,大貴早搶先一步,一把攥住了老人的手:“大伯,我是大貴呀,盼您回來好久了!”
老人比大貴想象的要年輕一些,但脊背佝僂得厲害,穿一身灰色運動衫,戴一副茶色太陽鏡。大貴心里一熱,眼窩就有點發濕。
老人抓住大貴的胳膊,笑呵呵地說:“哎呀,你就是大貴呀,我上次回來,你還跑著耍哩。”老人的聲音嗡嗡的像低音炮,不但讓大貴,也讓所有人都無比驚嘆:哎呀,哪兒像九十多歲的人,說話中氣這么足!不愧是從戰場上蹚出來的!就是不一樣。
老人仔細地瞅大貴,說,你長得像你爹,小時候我倆沒少在一起耍,還在村南葦塘里捉過“葦喳子兒”(一種鳥兒)。他還健在不?大貴說:“都去世十多年了。”老人呃一聲,問,多大上?大貴說,七十三。老人邊搖頭邊念叨:“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可惜呀,見不到我老兄弟了!”
老人又說:“我當年跟著隊伍打鬼子,家里全憑你爹你娘照應哩。”老人的嗓音就有些哽咽,用手揩一下眼角,臉色沉重起來。大貴眼里也汪出淚花,他把老人的手握得更緊。老人提了幾個名字:煥秋、瞇瞪,還有偏頭,竟然都作古了。老人的臉色比剛才又沉郁了一些。
以老人的意思,先在街上轉一轉,看一看。闊別故鄉幾十年,他恨不能走遍村子每個角落,尋覓一點兒時的痕跡。但老金和大貴執意讓老人先去村委會喝杯茶,聽聽村里的情況。無奈,老人由兒子和大貴攙扶著上了二樓會議室。上樓時大貴更感到了老人的不同尋常,老人的腿邁得堅韌有力,兩只穿深藍色運動鞋的腳踏在樓梯上,像鼓槌擊打鼓面,哪像那么大歲數的人呢?這讓大貴恍若看到了當年那個驍勇無比又一直在父親口中、也在全村人口中傳誦的極富傳奇色彩的本家大伯!
大家在收拾得干凈整潔的會議室落座后,老金代表村里,說了幾句歡迎老人回來的話,也算小小的歡迎儀式吧。然后開始匯報,主要談近幾年村里的發展情況。
作為村支書,這也是老金最津津樂道,最引以為豪的。截至目前,他們村大大小小的板材廠和家具廠已不下幾十家,可以說一抓一大把。據說,家財千萬的大老板都不少于十個了,村里光“奧迪”就有二十多輛,這在全鄉都是拔尖兒的。老金說,有錢了,人們就拆舊房蓋二層小樓。其實這些廠子和老金沒什么相干,但他是村里一把手,臉上有光啊。老金說得興致勃勃,還不時扭頭讓大貴補充或證實一下,大貴畢竟是老人的本家侄子,又是村主任,似乎比他更有說服力。
老人聽得入了迷,連茶水都忘記喝了,太陽鏡早被他放到了桌上。沒有了太陽鏡的遮掩,老人眼角的皺紋疊成魚網狀,下垂的眼袋像倆大肉瘤。大貴心里一沉,仿佛才感到大伯的確是歲數不小了。但又不明白他為什么突然要回來看看。自從接到老人的兒子從上海打來的電話,他這幾天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又想不明白。
老金剛介紹完畢,老人就迫不及待地發表感慨。他說,我們當年為什么要舍家撇業地跟著共產黨干呢,為什么要把腦袋掖到褲腰帶上和敵人拼命呢?不就是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嗎?咱村當年好幾百畝地,大多是香保和老費家的。人家大白面饅頭不斷頓兒,咱窮人哩,一天能吃上倆高粱面餅子、喝碗稀粥就不賴了。人家過年要殺一頭大肥豬,咱們只能買上幾根豬骨頭啃啃,哎呀,那個世道不公平!我這次回來,看到咱村變化這么大,打心里高興!除了個別音節,老人口音基本沒什么變化,這讓大貴想到了逝去的父親,還有家族中其他長眠于地下的長輩。一種源自血親的力量,讓他的心悸動了一下。
從會議室出來,大家簇擁著老人來到大街上。
老人的手微微顫動,他望望天,又望望腳下的地。還沒走幾步,就不再讓兒子和大貴攙扶了,他要自己走,仿佛只有自己走才覺得不是夢幻。這是他曾經走過無數次的街道呀,從童年一直走到成年,上面落滿過他大大小小的腳印。
大貴伸出胳膊,還要客氣,老人的兒子朝他擺擺手。這是老人的長子,長條臉,寬下巴,高顴骨,眉毛粗短濃黑,和老人有幾分相像,但白凈清秀,多了幾分南方人的特質。唷,這是那條主街嗎?老人一邊走,一邊問大貴。大貴點點頭說,沒錯。老人瞧瞧腳下,水泥路面讓小雨沖洗得白亮干凈,就說,好,好,這路不錯。再往兩邊看,幾乎全是清一色的兩層小樓,瓷磚貼面,潔白的塑鋼門窗,呈現一種與時俱進的態勢。老金伸手指著身邊的小樓,眼里閃出亮光,瞅著老人說:“這就是新民居,您老看好不好?”不等老人開口,又說,“早年不是有個說法嘛,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嘿嘿,咱不但實現了,再過幾年,俺們還打算蓋幾棟樓房,新農村嘛,就得和城里一個樣兒。”
老人停下來,驚嘆得直咂巴嘴:“想不到啊,咱村變化這么大!”
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老人停住,扭頭四下尋找什么。
老人伸手往地下指指,說,從前這里有一棵大槐樹,樹底下有一盤石碾。你看,這樹也沒了,石碾怎么也不見了?
老金怔一下,趕忙解釋:“是這樣的大伯,那棵樹我小時候也見過,一個人摟不住!”就張開粗短的胳膊做了個合攏狀。老人點點頭,說沒錯,我小時候也摟不住!好大一棵樹!它長得好好的,啥時候刨了?那兩只茶色鏡片就直直地盯住老金。老金被盯得心里有些發毛,右手插進濃密的頭發里,用力撓幾下,回答:“大伯,是最早修路那年刨的。”
老人又問起那個石碾。
這一問老金頓時亂了方寸,支吾了半天才說:“呃,對了,好像前些年讓人給砸了。”
哦!老人張大嘴巴,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是假牙。真牙哪兒有那么白?他怔怔地望著老金,問,為什么砸了?誰砸的?
老金眼珠子轉幾下,又啊嗯了半天才說:“時間長了,記不清了。”他其實是在搪塞老人,那石碾當年就是他領人砸的。他一接前任的班,就領一班人砸了。當時村里有種說法:不用的石碾放著不吉利。他最在意的就是這個不吉利!
于是老人唏噓不已,不停地搖頭,說那么好一個石碾,怎么說砸就砸了呢?當年那是大家湊錢買來的,光往村里運就費了老大勁兒。老金趕忙解釋,說村里老早就用上了磨面機,石碾沒用了唄。大貴也給老金解圍,說石碾放著畢竟礙事兒,就砸了。
老人嘴巴緊緊閉起,下巴上就現出一堆皺紋。大貴瞥見老人脖子上也滿是皺紋,像一塊揉皺的舊衣布。老人就這么站著,久久不愿離開。過了許久才說,當年大家喜歡坐在大碾盤上吃晚飯,一邊吃一邊扯閑話,那才叫舒服哩。小孩子們愛在大槐樹底下捉迷藏,趴在碾盤上聽大人講古,講薛仁貴征西,講李自成攻進北京城后天天吃餃子,說天天像過年,結果只做了四十二天皇帝。本來他有做四十二年皇帝的命,非說天天像過年,可不就做了四十二天唄。
“哎呀,再見不到那個石碾了!”老人像失去了一個非常要好的伙伴,一臉痛苦,接下來說了這么一句話,“咱村里唯一還認得我的,也許就是這個石碾和那棵大槐樹!可都沒了!唉呃——”
就是這句話,讓氣氛頓時壓抑起來。大家都默然不語,大貴心里更像扎進了一根刺兒。
老人的兒子趕忙解釋,說父親年歲大了,這幾年更愛懷舊了,要不非得回來看看呀,任誰也勸不住!
到底是縣里的王部長見多識廣又有文化,隨口說了一句陶淵明的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然后哈哈地笑著打圓場,說人哪兒有不戀舊的?就連鳥兒,不是還戀舊枝嗎?何況,像大伯這樣離開故鄉半個多世紀的人,不想家才怪!
他這么一說,大家紛紛附和道,大伯實在難得呀,這么大歲數了還牽掛著故鄉。這次老人回來省親的消息,是大貴告訴鄉里的,鄉里認為這是件大事兒,又告訴了縣里。因為老人是縣里唯一一位將軍,縣志上都有專門介紹,還有老人身著戎裝、胸前戴滿功勛章的照片,那是當年軍委授勛時照的。雖說老人早已離休,但畢竟是縣里在外面職位最高的,因此縣領導對老人這次回鄉非常重視,特意派王部長前去機場迎接,而且還全程陪同老人。中午的接風宴,早安排在了縣里最好的飯店,領導們都要出席的。一個縣能出個將軍實屬難得!
老人說:“你們別夸我,我就是回來看看,看看小時候耍過的地方。這些年晚上一合眼,想的就是村里人,村里事兒。”老人的聲音都幾度哽咽了。他兒子擔心老人的身體,勸老人不要太過激動。大貴也勸,大家都勸。
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時,幾個在大街上嘮嗑的老頭老太太圍上來,驚奇又親熱地和老人打招呼。他們也都六七十歲,雖說和老人不曾謀面,但久聞老人大名。老人使勁兒握著那一雙雙粗糙的手說,今天能見到你們,我也非常高興!
和他們告辭后,大家領著老人來到了他家老宅。其實只能說是老宅的位置,因為老人出生又長大的老屋,哪兒還有一點蹤影呢。那是三間土坯房,他前妻一直住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用他寄回的錢翻蓋新房。前妻去世后,老人就把那三間房無償地捐給村里,村里就拆掉蓋了大隊衛生院。現在還是衛生院,只是房子又翻新了,依然是平房,但高大寬敞,也是瓷磚貼面、鋁合金推拉門窗,完全是現代化的樣式。
老人在院子當央停住了,環視一圈兒,喃喃地說著什么。王部長和劉鄉長對視一下,擔心老人因情緒太激動發生意外,但又不好說什么。劉鄉長兩手扣在一起不安地搓動。
老人嘴里發音終于清晰起來。他說一閉眼,就看到了那棵棗樹。他走到院里的偏東位置,伸手指著有些濕漉漉的地面,說就是這個位置,沒錯!棗樹是他頭參軍那年和妻子一同栽種的。記得“文革”前那次回來,它長得都有大腿粗了。非常奇怪,他沒有吃過樹上的棗兒,但一想起它,仿佛就聞到了棗花的香味,嘴里也滿是棗香。
“就是這個位置,我不會記錯的!”老人抬腳在地上踢幾下,非常肯定地說。他的聲音很高,空氣都震蕩起來。因為踢得用力,松軟的泥土被他踢出一道淺溝兒。忽然,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問大貴:“好好的棗樹為啥也刨了?”
大貴和老金又都慌了神。如今村里的樹們大多是短命的,尤其人們住上了小樓,裝了空調,就不再依賴大樹遮陽,沒人把樹當回事,于是院里只種些花花草草。怎么回答老人呢?明說吧,怕他傷感,大貴一拍腦袋,就說:“哎呀,大伯,我想起來了,前幾年那樹不知為啥突然不結果了,你說,不結果還讓它長著干啥呀?就是不刨,也不中用了,太老嘍。”說完突然意識到不妥。老人果然嘆息一聲,說樹和人一樣,都有老。邊說,邊無奈地搖頭,也有自嘲的意思,一頭銀發,像風中的一團棉絮。這時院里的氣氛又沉悶起來。因為吃不透老人的脾性,誰也不敢再搭話。
“爸,咱該去墳上了。”經老人的兒子一提醒,老人才開口了:“走,看看你爺爺奶奶去!”
老人家的祖墳位于村西一座沙崗上。因為沒有占耕地,所以才幸運地保留下來。遠遠望去,那只是一片雜樹林。楊樹發芽兒早,醬紅色的葉片已完全舒展開,閃出一抹嫩黃。幾簇黃綠色的打碗碗花兒,像星星一般點綴在墳包之間。濕潤清新的泥土味,撲進大家的鼻子里。
祭奠儀式非常簡單。當紙灰隨著火苗升騰起來,老人把太陽鏡遞給兒子,深深地給九泉之下的二老鞠了躬。之后,又在緊挨二老的一個墳包前也鞠個躬。大家知道,下面就長眠著他的前妻,那個癡情又苦命的女人。老人嘴里叨念了幾句什么,誰也聽不清,也許是說給那個女人的私密話吧。然后蹲下來,望著墳包呆呆地出神。老人的兒子說:“讓我爸歇會兒吧。”
老人就這么蹲著,對大家說,他為什么突然回來呢?因為前些日子他夢見前妻了。前妻還是年輕時的樣子,紅彤彤、胖嘟嘟的臉,哪兒都沒變,笑瞇瞇地對他說,咱家樹上的棗兒把樹枝兒都壓彎了,又大又紅,比哪年都結得多。那年你還沒吃上棗哩,就跟著隊伍走了。她還告訴他,如今鄉下和從前大不一樣了,要他務必回來看看。老人說完嘆息一聲,說就是這個夢,才讓他趕在清明節前回來一趟的。當初,萬不該給她寫那封信……
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尤其是大貴,他見過那個本家大娘。那時他還小,時常聽大人們說她傻,說男人和你離婚了,你還不改嫁,還像從前一樣侍奉公公婆婆,又養老送終,圖個什么?人們不理解,大貴也不理解,但他覺得說話辦事干脆利落的大娘一點不傻!后來聽說,當年大伯隨部隊南下時,就做好了為國捐軀的準備,為不連累年輕的大娘,給她寫了一封解除婚姻的信,同時也委托區委會做大娘的工作;大娘也給大伯回了信,說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她要等他回來;終因戰亂,這封信沒有寄到大伯手中……大伯家沒有近親,從前大貴父親每天給大娘挑水,大貴長大后就接替父親,直到大娘離開這個世界。
此時,望著老人一臉的懊悔和凄楚,大貴眼睛發酸,心也像讓東西撞了一下。大家都沒有想到老人這次回鄉會是這么一個結局,都有些尷尬,不知道該怎么辦。是呀,如果那棵大槐樹、那盤石碾還在,那棵老棗樹還在,老人心里也許能得到一點慰藉吧。那是時光留給人的一點難得的念想。他們能感到老人心里空落落的,他們心里也空落落的。
這時,大貴兜兒里的手機突然響了。是女兒小霞打來的,說:“爸,我決定了,我要打掉!”
死妮子,你往前走沒錯,可得給人家留個后呀。大軍可是根獨苗兒!——還沒張口呢,已傳來嘟嘟的斷線聲。他想打過去,又作罷,這場合怎好說這個?
老人回去沒多久,就傳來辭世的噩耗。
老人的兒子在電話里對大貴說,父親走前留下遺囑,要把他大部分積蓄捐給村里,也就三十萬,讓用在該用的地方。哪兒是該用的地方?大貴和老金犯起了思量。
幾天后,還是老人的大兒子送老人回來的。老人已變成了一個小小的骨灰盒。按照老人的吩咐,他要在老宅院里逗留一會兒。大貴把本家晚輩都喚了來,卻沒讓女兒來。這幾天女兒正和他慪氣,無論他和親家公如何做工作,女兒就是不松口,擔心生孩子再嫁人受影響。她媽也這么認為。直到親家公提出給五萬元做補償,女兒和她媽才動心了。大軍是個好女婿,和小霞結婚還不足一年,卻不慎從城里工地的腳手架上摔了下來……他覺得那錢拿著燙手!
伴隨著二踢腳的脆響,老人的骨灰盒被大兒子抱在懷里,走出院門后,在大家的簇擁下,朝老人家的祖墳走去。
骨灰盒里沒有老人的骨灰,只放了老人一頂舊軍帽、一件舊軍裝。老人的兒子解釋,雖說他非常同情那位大娘,但弟妹們一致認為不能按照父親生前的意愿,分一半骨灰給她,那樣對母親不公平!沒辦法,他得少數服從多數。
在沉重而紛沓的腳步聲中,大貴望著骨灰盒上大伯的遺像,忽地生出個想法:用那三十萬在大伯家老宅建個村史館,里面除了陳列早已廢棄的農具和石碾、石磙、牲口槽等等,還要有本家大伯的事跡。當然,更少不得他和大娘這段塵封已久的愛情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