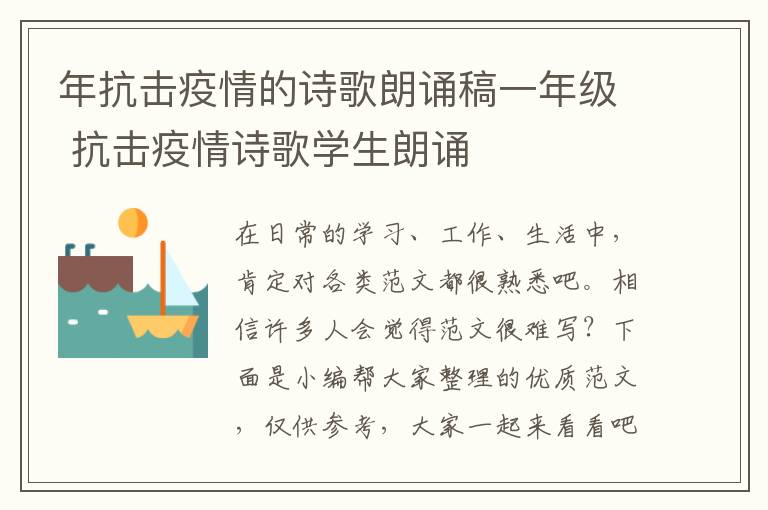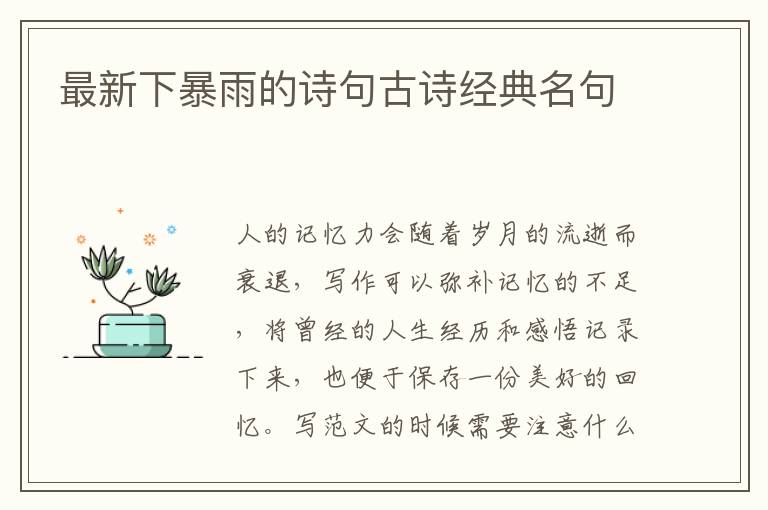某孝廉

作者: 謝澤生 【本書體例】
王同軌
王同軌,字行父,黃岡(今屬湖北)人。生卒年不詳,約生于明嘉靖中期,卒于萬歷末年或天啟初年。以貢生除江寧知縣,遷南太仆主簿。《耳談》十五卷,“亦《夷堅志》之流”,“每條皆記所說之人,以示征信”。
乙未有某孝廉,群飲于郊,見一婦哭墓歸,素笄艷妝,絕美。婦乘蹇(jiǎn簡),因棄眾驅蹇從之。及門,婦人,莫為計。
忽自內一人出,孝廉與語。其人曰:“此婦新寡,辭其夫墓歸,將適人耳。吾為某執伐來也。”孝廉曰:“幸甚,為我媒,當厚報公。”其人曰:“然。”因與為期,至邸舍,僅出廉值,盟已成。
其夜婦至,下輿,諦視之,果逢者,大喜。花燭觴散且就寢。婦曰:“君第先寢。”孝廉即先寢。逾時婦不寢。孝廉起問曰:“汝何不寢?”婦語如前。孝廉又先寢。婦見孝廉韶秀,又饒橐(túo駝)裝,屢寢皆如己言,知無他腸。因問曰:“君有密友否?”曰:“即吾同胞塞涂,何論密友!”曰:“妾從君矣!”孝廉大詫曰:“汝為予所娶,不從何往?”曰:“非也!此賺錢術耳。夫未曉必至,逞其無賴矣!妾哭母非寡。媒者,即吾夫也。不寢者,夫旨也。君但乘夜遷密友家,始為得妾。此妾自媒從君也。”孝廉即如其言遷去。
未明,夫果擁眾至。見是空室,以詢邸主人。邸主人曰:“相公夜裝歸矣。”即群崩去追之,不知所往。
婦身是賺具,反為婦賣,機中有機,亦何矯捷。屢寢皆如婦言,本是細微,而以此得婦心。此柔道之驗,彼壯于頄(qiú求),其何能以有求!吳寧伯說。
(選自《耳談》)
明嘉靖乙未(1534)年間,有一個孝廉,一次同朋友一起在郊外飲酒。看見一個少婦從墓地哭罷歸家。她頭上插著白色的簪子,身上穿著艷麗的衣裙,非常美麗。那婦人乘著毛驢,于是孝廉也離開眾人乘著毛驢跟蹤著她。到了家門前,婦人進門去了,孝廉無計可施。
忽然一個男人從屋里出來,孝廉同他交談。那人說:“這個媳婦才死了男人,辭別她的丈夫剛從墓地回來,將要嫁人。我是替別人作媒來的。”孝廉聽了,說:“好極了,請替我作媒吧,我一定用厚禮報答你!”那人說:“行!”并與他約定了相見的日子。到了孝廉住處,他僅僅出了很低的價格,事情就商量成功了。
這夜,婦人來了,下了車,孝廉仔細一看,果然是他白天遇見的女人,不由心中大喜。待酒宴過后,該就寢了,女人卻說:“你先睡。”孝廉就先睡下。過了一個時辰,女人仍不睡,,孝廉起身催問:“你為啥還不睡?”女人仍象以前一樣回答他。于是孝廉又先躺下。女人看孝廉年輕英俊,家里的財產也很富足,況且多次都按自己的意見睡下,知道他沒有其它想法。于是對他說:“你有親密的朋友沒有?”孝廉回答說:“我的同事好友都是做官的,說什么密不密的。”女人說:“這樣,我就真正跟你了。”孝廉非常吃驚:“你被我所娶,不跟從我還想往哪兒去?”女人說:“不啊,我這樣做不過是賺錢的把戲罷了。天不明我丈夫必定來這里,來了就會大耍無賴,白天我哭是哭我母親,并非是寡婦哭丈夫。所謂媒人,就是我丈夫啊,我之所以不就寢,完全是我丈夫的主意呀,只有你連夜遷到親密的朋友家,才能得到我,這是我自己作媒嫁給你。”于是,孝廉馬上就按她所的話搬走了。天不明,她的丈夫果然帶著人到了,發覺屋里空著,就盤問店老板。老板告訴他說:“先生夜間帶著行李回去了。”他們就分頭去追,然而不知該向哪里去找。
女子本是賺錢的工具,最終卻反被女子出賣;機關中還有機關,也真是考慮周全了。孝廉多次就寢都依女子所言,這本是小事,但卻因此得到女子的愛心,這就是柔能克剛的明證。那男子鬼計多端,機心太盛,又怎能得到什么呢!吳寧伯談。
孝廉與他所追求的女人之間,本是無情的,一為羨慕其“素笄艷妝,絕美。”一是充當賺錢的工具,然而終成伴侶。何也?本源一個“誠”字。
人世間大凡男女相悅,除了相貌之外,最為要緊的,應是以心換心,以情悅情。試想,孝廉若是見了“絕美”女人就如狼似虎地撲上去,那就會是另外一種結局。然而孝廉在以貌取人“大喜”之后。對“絕美”的哭墓婦,并非只懷玩弄之意,而是真心想娶,所以才會如婦之言,先寢多次。恰從這里,孝廉以其老誠換取了女人之心,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作為賺錢工具的女人,畢竟是一個血肉之體,誰不希望過真正的充滿情愛的生活呢?每天作為“賺錢術”的主角,實是一個不光彩的角色,壓抑真情,虛露假面,對一個被利用的女人,哪怕是被其丈夫利用,因為不能享受情愛,理當會萌生一種新生活的追求。因之當她發覺孝廉“屢寢皆如己言”,“知無他腸”,就傾出真心“自媒從君”,以求開始新的以誠相通、以心相許的新生活。
篇末作者評論說:“婦身是賺具,反為婦賣,機中有機,亦何矯捷。屢寢皆如婦言,本是細微,而以此得婦心。”說得有理。那個男子本是“機關算盡”,但卻忘記了把自己的妻子當作“工具”使喚,最終反會“偷雞不成蝕把米”。“柔道之驗”關鍵在一個“誠”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