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肆高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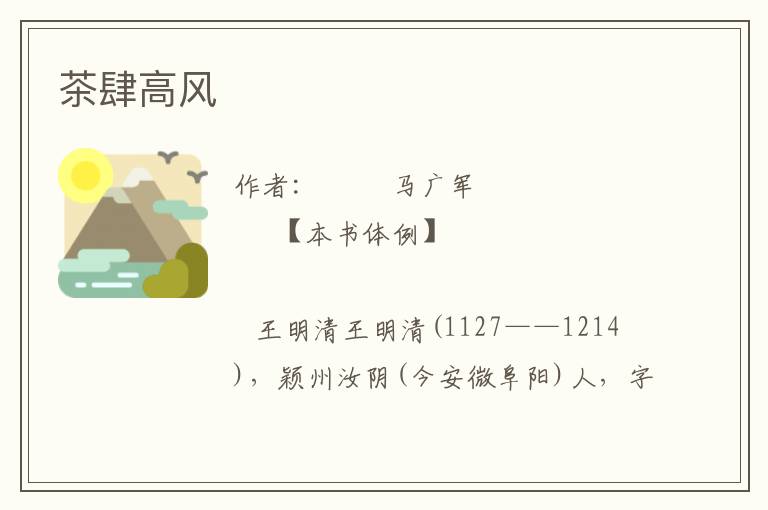
作者: 馬廣軍 【本書體例】
王明清
王明清(1127——1214),穎州汝陰(今安微阜陽)人,字仲言,著名學者王銍(zhì質)次子。嘉泰二年,任浙西參議官,他熟知本朝典故制度,尤注重搜集宋南渡后的軼事遺聞。晚年隱居,著作頗豐。有《揮麈前錄》、《后錄》、《清林詩話》、《摭青雜說》等傳世。
京師樊樓畔有一小茶肆,甚瀟灑清潔,皆一品器皿,椅桌皆齊楚,故賣茶極盛。
熙豐間有一士人,乃邵武李氏,在肆前遇一舊知,相引就茶肆,相敘闊別之懷。先有金數十兩,別為袋子,系于肘腋,以防水火、盜賊之虞。時春月乍暖,士人因解卸衣服,次置此金于茶肆桌上,未及收拾。未幾,招往樊樓會飲,遂忘遺出,既飲極歡。夜將半,滅燈火,方始省記。李以茶肆中往來者如織,必不可根究,遂不更去詢問。
后數年,李復過此肆,因與同行者曰:“某往年在此,曾失去一包金子,自謂狼狽凍餒不能得回家,今與若幸復能至此。”主人聞之,進相揖曰:“官人說什么事?”李曰:“某三四年前,曾在盛肆吃茶,遺下一包金子,是時以相知拉去,不曾拜稟。”主人徐思之曰:“官人彼時著毛衫,在里邊坐乎?”李曰:“然”。又曰:“前命坐者著皂皮襖乎?”李曰:“然。”主人曰:“‘此物是小人收得,彼時亦隨后趕來送還,而官人行速,于稠人眾中不可辨認,遂為收取,意官人明日必來取,某不曾為開,覺得甚重,想是黃白之物也。官人但說得塊數、秤兩同,即領取去。”李曰:“果收得,吾當與你中分。”主人笑而不答。
茶肆上有一小棚樓,主人棒小梯登樓,李隨至樓上,見其中收得人所遺失之物如傘、屐、衣服、器皿之族甚多,各有標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遺下者”;僧、道、婦人則曰:“僧、道、婦人。”其雜色人則曰:“某人似商賈”、“似官員”、“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則曰:“不知其人”。就樓角尋得一小袱,封記如故,上標曰:“某年月日,一官人所遺下。”遂相引下樓,集中再問李塊數秤兩。李計若干塊、若干兩。主人開之,與李所言相符,即舉以付李。李分一半與之,主人曰:“官人想亦讀書,何不知人如此!義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輕義,則匿而不告,官人將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也。”李既知其不受,但慚怍不言,加禮遜謝,請上樊樓飲酒,亦堅辭不往。時茶肆中五十余人皆以手加額,咨嗟嘆息,謂世所罕見也!
識者謂伊尹之一介不取,楊震之畏四知,亦不過是。惜乎,名不附于國史,附之亦卓行之流也。今邵武軍光澤縣烏州諸李衣冠頗盛,乃士人之宗族子孫。高殿院之子元輔,乃李氏之親,嘗與余具言其事。
(選自《摭青雜說》)
京城樊樓邊有一座小茶館,非常優雅潔凈,用的都是最精致的茶具,椅子桌子擺得整整齊齊,所以生意十分興隆。
熙豐年間,邵武一位姓李的士人,在茶館前遇到一個過去的好朋友,相互拉著來到茶館里,敘說長久分別后的思念。他隨身帶有幾十兩銀子,放在一個袋子中,系結在腋下,以防突發事件與盜賊。當時是春天,天氣突然轉暖,士人就脫下衣服,隨手把裝金的袋子也放在茶館的桌子上,沒及時收起。不一會,招呼朋友去樊樓飲酒,就忘了放下的袋子,出了茶館進了酒樓,兩個人開懷暢飲。一直到半夜,熄了燈以后才想到這件事。李氏認為茶館中顧客來來往往,一定無法追查,就不再去詢問這件事。
幾年后,李氏再次路過這個茶館,就跟同伴說:“幾年前我在這個地方曾丟了一包銀兩,饑寒狼狽幾乎不能回家,今天和你又能到這兒,真是有幸。”茶館主人聽了這話,走上前來對他施禮說:“官人說的是怎么一回事?”李氏說:“我三四年前,在貴茶館吃茶時丟了一包銀子,當時被好友拉去喝酒,沒有回來問您。”主人認真回憶一下說:“您那時穿毛衫,坐在里面嗎?”李氏回答說:“對。”又問:“走在前面請您先坐的那人,穿黑色皮襖嗎?”李氏回答說:“對。”主人說:“這袋子我撿到了。當時我隨后趕去送還給您,可惜您走得太快,在眾人中沒法找到,就替您保存,想著您第二天一定來找。我沒有打開這袋子,只是覺得很重,想著一定是黃金、白銀之類。您只要說對塊數、斤兩,馬上可領去。”李氏說:“真是您收存,我應當與您平分。”主人笑笑沒有回答。
茶館上面有一層小閣樓,主人搬來梯子上樓。李氏隨他到樓上,看到樓上存放著顧客所遺失的象傘、鞋子、衣服、器皿之類的東西很多,上面各有標記。寫著某年某月某日什么樣的人丟失的。僧侶、道士、婦人丟的東西就寫上“僧、道、婦人”。身份不明確的就標著“某人象商人”、“象政府官員”、“象秀才”、“象公吏”,不知道誰丟下的就標上“不知某人”。走近樓角找到一個小包袱,象過去一樣原封沒動,上面標明:“某年某月某日,一個官人丟的。”于是一起到了樓下,又認真問了李氏銀兩的塊數和斤兩。李氏回憶著說出多少塊、多少兩。主人打開袋子,和李氏答的相吻合。就拿起來還給李氏。李氏分一半給他,主人說:“官人您也是讀書明理的人,怎么這樣不理解人!古人尤其重視義與利的區別,如果我重利輕義,就藏起來不告訴您,您將怎么辦?又不能用國家法律懲罰我,我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怕內心有愧呀。”李氏知道他一定不要,慚愧得不能說話,更加感激涕零。請他去樊樓喝酒,主人又堅決拒絕。當時茶館中五十多人全都感慨喟嘆,說是這樣的事世上罕見啊!
有見識的人說伊尹連別人的一根小草也不肯要,揚震害怕“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重義輕利,也不過如此。可惜啊,茶館主人名不見國史。如果見于國史,應該歸于有高尚節操的那類人呀。現在,邵武軍光澤縣鳥州的那些李姓的人作官的很多,就是這個士人的同族子孫。高殿院的兒子高元輔,是李氏的親戚,曾經與我詳細說過這件事。
這是一篇贊揚平民百姓拾金不昧的“小小說”,小說的情節也較簡單,甚至簡單到連主人公的姓名也沒有。可貴的是作者能夠通過環境的描寫,人物之間的鋪墊和烘托,寫出了主人公的高尚情操,并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展示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所具有的道德風尚,讀來給人以啟發和教育。茶館的主人是小說的核心人物。作者通過環境的渲染和烘托,暗示出他拾金不昧的高尚品格。
寫李氏的出場筆墨較多,描述較細致。先寫李氏與朋友不期而遇;次寫李氏因天暖脫衣而將金袋放在桌上,沒有及時收起;再寫李氏與朋友“既飲極歡”而“遂忘遺出”。最后寫李氏為何不去“詢問”。在“往來如織”的茶館中丟了金銀,在一般情況下,“必不可究”。作者在這里賣了一個關子:李氏的金銀到底能不能找到呢?這就為下文主人公的送還埋下了伏筆。
作者把茶館主人的出場置于客人的對話之間。接著作者通過主人公的語言、行動來突出人物性格。“后數年,李復過此肆”。于是李氏大發感慨,“今與若幸復能至此”。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主人就走上前來問了事情的經過。反映了茶館主人不取遺財,時時刻刻都想著失主的美好品質。而下文的“問之”“思之”“證之”“釋之”的一系列行為。又突出了他的認真負責、謹慎小心的性格特點。失主終于找到了,作者借李氏隨主人去樓上取失物的契機,借李氏之見,把主人公的美好品德更加凸現出來。樓上堆積著各種各樣的失物,保存完好,原封不動,并且上面標著記號。可見,作者的拾金不昧,不是一時的“良心”發現或心血來潮,這就更進一步突出了主人公的高尚品質。丟的金銀找到了,李氏自然感恩不盡,提出要“意思意思”。先“我當與你中分”,遭回絕后,“請上樊樓飲酒”,又“堅辭不往”。從而使主人公的不圖名利、施恩而不圖報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
作品末段涉及到伊尹和揚震兩個不同時代的歷史人物。伊尹是商朝人,官居相位,為政清廉,別人的一根小草似的東西他都不要;揚震是東漢人,一次有人想走他的“后門”,深夜送給他一車黃金,并說沒有別人看見,請他收下,揚震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說沒人知道!”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里,作者把茶館主人的行為與伊尹、揚震這樣的人物相比較,并評論說“亦不過是”。作者的態度是何等的鮮明啊!有意識地去寫“小人物”的看似平凡而實則偉大的“小事”,就是這篇小說的思想價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