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漢史,閱紀(jì)信韓信傳·華岳》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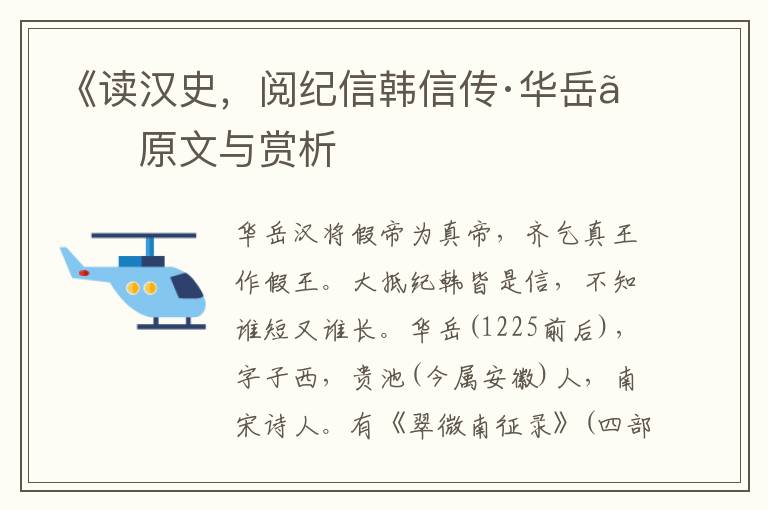
華岳
漢將假帝為真帝,齊乞真王作假王。
大抵紀(jì)韓皆是信,不知誰短又誰長。
華岳(1225前后),字子西,貴池(今屬安徽)人,南宋詩人。有《翠微南征錄》(四部叢刊本)。
全詩寫劉邦被項羽圍困于滎陽時,紀(jì)信甘愿冒充劉邦出降來解脫劉邦,結(jié)果代死而終,而同在劉邦危急之際,韓信向劉邦討封,劉邦為利用韓信兵力,不得已封其齊假王(代理王),指出紀(jì)信對劉邦的愚信堪嘆,韓信對劉邦的輕信可悲。詩人巧妙地抓住“信”這個詩眼,把紀(jì)信、韓信兩個都名“信”的人物的愚信、輕信和劉邦的無信,借議論暗示出來,有著化論為詩,情理深致且又莊諧雜作的機趣。
“漢將假帝為真帝”,是指紀(jì)信乞代劉邦去死一事。《史記·項羽本紀(jì)》與《漢書·高帝紀(jì)》均記載了其事;紀(jì)信見劉邦兵困滎陽,眼看性命難保,便獻計冒充劉邦出降,使劉邦從別處逃脫,后項羽知道受騙,就怒而燒死紀(jì)信。紀(jì)信心甘情愿地扮演假帝的角色詐降去為真帝劉邦赴死,他成了劉邦的救命恩人。
“齊乞真王作假王”,是指韓信平齊地后,要求劉邦封他為齊假王(代理王),實質(zhì)是要作真王。《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著這件事:劉邦被項羽圍困于滎陽,慮不得解脫,就向韓信求援,韓信要求封王,劉邦并不愿意答應(yīng)這種日后對自己會形成擁兵生變的威脅性的交換條件,但因事急,也只好封之。韓信乘機討封,可見他是不肯白白地為主子賣力的。
以上一、二句詩是述史,下面兩句詩是議論。
“大抵紀(jì)韓皆是信,不知誰短又誰長”,是指紀(jì)信、韓信都名“信”,又都講“信”(信用),誰優(yōu)誰劣,難以論其短長。這里語帶雙關(guān),意謂紀(jì)信對劉邦忠信,劉邦賴以脫險,韓信求封后,為劉邦滅項稱帝建立了卓越功勛,稱得上是守信的。而真正無信的是誰呢?——恰恰是利用紀(jì)韓二“信”的劉邦!
這首詩的機趣,充分表現(xiàn)了詩人的藝術(shù)匠心。它在“真”和“假”、“長”和“短”上嵌進去理性的沉思,以紀(jì)信、韓信的假作真來真作假,長是短來短是長的行為,讓人從中思索到深邃的哲理。紀(jì)韓的忠信,見其愚,而韓信的守信,見其拙。歷史事實證明了這種愚與拙是利于劉邦而害了自身。劉邦爬上帝位,并未記住紀(jì)信的救命之恩,而韓信竟被劉邦忌殺。如此看來,紀(jì)韓的忠信與守信跟劉邦的無信無義相比,這兩人之間就毋庸究其短長。如果硬要道長說短的話,應(yīng)該在紀(jì)韓與劉邦之間分辨長短。詩的結(jié)句“不知誰短又誰長”是有意將紀(jì)韓排除在議論之外,暗刺劉邦失信的卑鄙兇殘。這種透過字面看字里,越過虛處看實處的由顯探隱的筆法,是靠著紀(jì)韓皆名“信”的組合與延伸來打開意蘊的空間的,巧合得渾然天成,加之語言戲謔有味,讀之直感到痛快淋漓,為詩人能如此揮舞著奇想的魔杖別善惡、明是非、寓褒貶拍案叫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