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淮河宿闞石有感·文天祥》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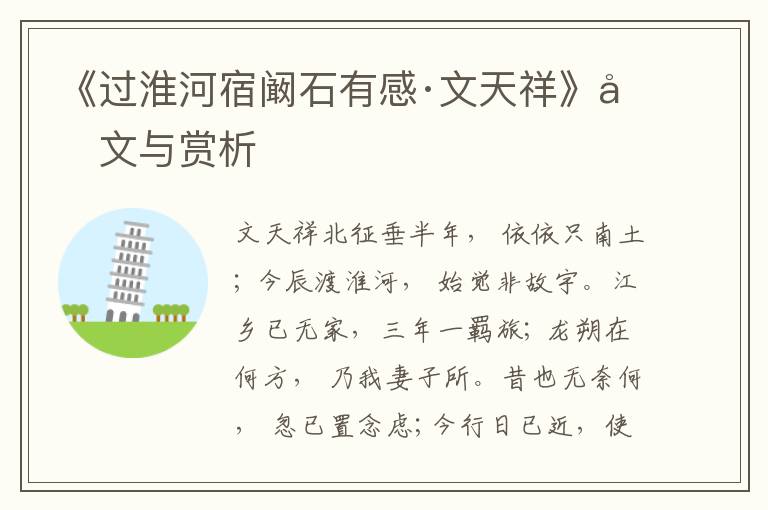
文天祥
北征垂半年, 依依只南土; 今辰渡淮河, 始覺非故宇。江鄉(xiāng)已無家,三年一羈旅; 龍朔在何方, 乃我妻子所。昔也無奈何, 忽已置念慮;今行日已近,使我淚如雨。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yè)緣在,骨肉當如故。
闞石,淮安縣的一個地名。這首充滿國破家亡之痛的詩作于南宋最后一年祥興二年(1279)。時文天祥在被元軍統(tǒng)帥、漢奸張弘范解往大都途中。第一句寫途中感受。“北征垂半年”,文天祥于四月二十二日被押離廣州北行,九月一日經(jīng)過淮安,將近半年。這段時間他經(jīng)過的都是南宋領土,因此極有感情,向鄉(xiāng)鎮(zhèn)一一“依依”惜別。現(xiàn)在要渡淮河——宋元分界線,進入異地,離開故國。本來心情就很痛苦,但一路所見南宋土地,還得到一些慰藉,現(xiàn)在是進入異國,詩人悵然若失,心痛欲摧,潸然涕下。再說三年前,也曾被蒙古貴酋押往北行,所幸在京口得脫,投奔儀征,在江淮一帶飄泊數(shù)月,最后回到了南方,這次看守極嚴,逃返祖國的機會是沒有了,詩人倍感悲怛。第二句憶鄉(xiāng),并寫要去的地方的情景。“江鄉(xiāng)已無家”,江鄉(xiāng),文天祥故家近贛江,恭帝趙隰德祐元年(1275),元軍進攻江西,文天祥毀家紓難,起義兵對抗。“三年一羈旅”,到祥興元年(1278)被俘止,這三年中,文天祥一直帶兵在外苦戰(zhàn),行止不定。“龍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龍朔,即龍城(今遼寧朝陽)與朔方(漢郡名,在今內蒙、寧夏一帶),這里泛指元都燕京。端宗趙昰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部在贛州、吉州二城與元兵鏖戰(zhàn)失利,退至空阬。他夫人及一子二女皆被擄去,此時關押在燕京。第三句抒發(fā)夫妻、父子的柔情,為國亡家毀而慟哭。“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行日已近,使我淚如雨。”以往戰(zhàn)斗頻仍,無法思念妻兒,快速游擊,也無暇顧及他們。置念慮,即不思念之義。現(xiàn)在我可以念及他們了,可是又都失卻了自由,不可能團圓,因而越向燕京接近,我越是掛念他們,不覺悲從中來,淚飛如雨。男兒有淚不輕彈,偉大的民族英雄也是兒女情長的。第四句表達為國捐軀的決心并以此勸勉妻兒。“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綱常,即三綱五常, 三綱中有君為臣綱一條,要求大臣服從帝君,而帝往往又是國的象征,這是封建社會維護政權的理論基礎,倫理標準。如所周知,儒家思想是文天祥重要的精神力量,他在《正氣歌》中說:“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絕命詞中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因此,“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實在是他忠君思想的袒露,為了維系臣綱愿意獻身。在我國古代忠君與愛國是統(tǒng)一的。北行是為祖國捐軀,所以“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沉痛、堅定、悲壯而又富于感情。第五句以浪漫的想象,跟妻兒相約來世團圓,勸慰他們?yōu)樽约旱墨I身節(jié)哀。“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yè)緣在,骨肉當如故。”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表面寫夫妻、父子不能見面之恨,實寫國破之恨,并表達來生仍為眷屬,合成一家的愿望。業(yè)緣,佛家語,據(jù)說善業(yè)為招善果的緣,惡業(yè)為招惡果的緣。作者借以表達自己為國獻身的正義行為必將永垂青史。
這首詩傾吐了忠于國家民族、矢志不移的浩然正氣。文天祥寫作勤敏,戰(zhàn)火紛飛,千難萬險,斧鋸加頸,都不放下彩筆。“在患難中,間以詩紀所遭。”目的是“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后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指南錄后序》、《集杜詩自序》)。這種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使作品反映了南宋末年廣闊的社會面貌,具有詩史的地位。在后期,他著力學習杜甫沉郁蒼涼、老辣渾厚的藝術風格,使其詩歌慷慨激昂,寄托遙深,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