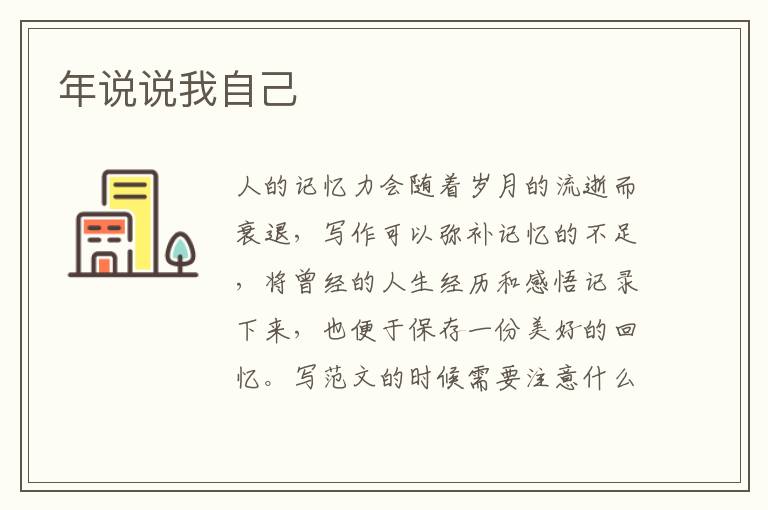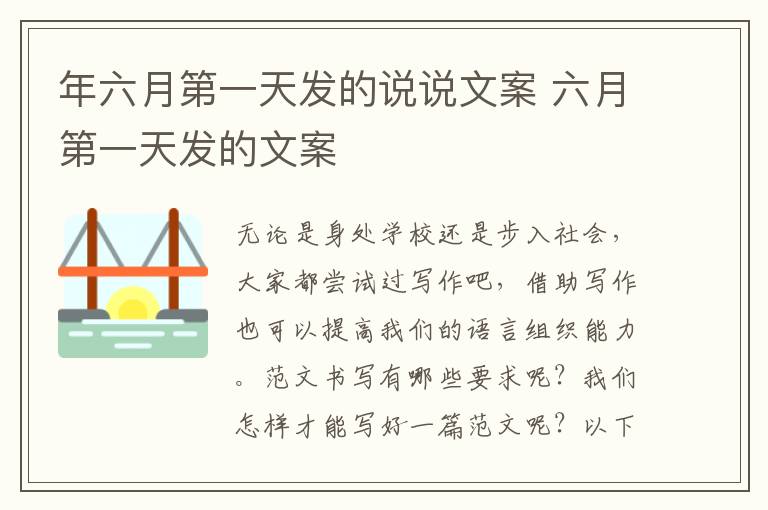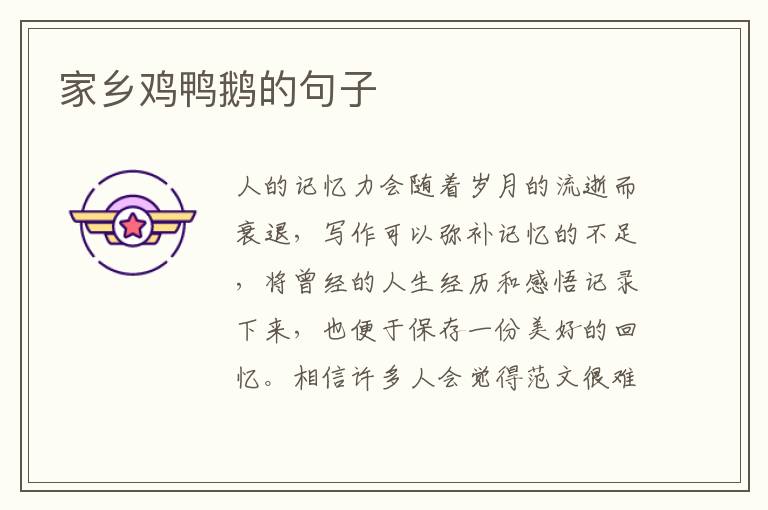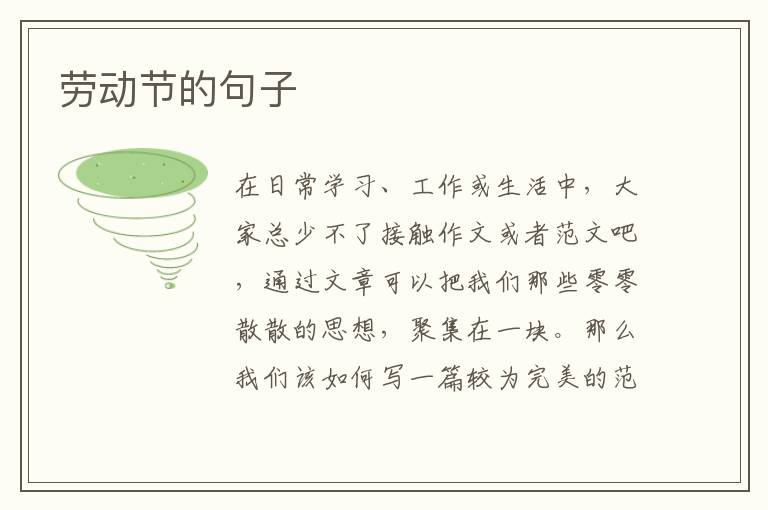邊城中描寫柔弱的水的句子合集50句

論沈從文《邊城》中的水文化意蘊(yùn)
在《邊城》中的故事就發(fā)生在臨近水邊的“茶峒”小鎮(zhèn)里,水在《邊城》有著什么樣的意義呢?下面小編給大家?guī)?lái)論沈從文《邊城》中的水文化意蘊(yùn)。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論沈從文《邊城》中的水文化意蘊(yùn)
摘 要:沈從文是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獨(dú)具個(gè)人魅力和文藝風(fēng)格的作家。沈從文的性情人格都與水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體現(xiàn)著水的特質(zhì),滲透出水文化的氣息。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大多以水為背景,講述發(fā)生在水邊或與水有關(guān)的故事,眾多的水意象及水的衍生意象共同形成了一個(gè)以水為中心的文化系統(tǒng)。在這一系統(tǒng)中,生命文化、愛(ài)情文化和神巫文化是其主干。
關(guān)鍵詞:沈從文 《邊城》 水文化意蘊(yùn)
【第1句】:沈從文與水的不解之緣
在《我的寫作與水的關(guān)系》一文中,沈從文一再?gòu)?qiáng)調(diào)自己“文學(xué)事業(yè)”的基礎(chǔ)并不是建筑在一本或一堆“合用的書”上,而只是建筑在“水”上。沈從文是一位將水溶進(jìn)自己生命的作家,水既是他性格的寫照,也是他作品的靈魂。沈從文出生于依山傍水的湘西鳳凰,湘西水系發(fā)達(dá),自古就有“五溪”之稱。沈從文生于斯長(zhǎng)于斯,水深深地透進(jìn)沈從文的血液,滋養(yǎng)著他的思想和性情。對(duì)于水的性格,沈從文也作了如下分析:“水的德性為兼容并包,柔弱中有強(qiáng)韌,從表面看,極容易范圍,其實(shí)則無(wú)堅(jiān)不摧。”〔1〕沈從文實(shí)際上是以心靈和精神來(lái)與水溝通,在水的滋養(yǎng)中,沈從文逐漸形成了對(duì)生命的領(lǐng)悟:“我是對(duì)一切無(wú)信仰的人,卻是信仰生命”〔2〕;“一個(gè)人過(guò)于愛(ài)有生的一切時(shí),必因?yàn)樵谝磺杏猩邪l(fā)現(xiàn)了‘美’,亦即發(fā)現(xiàn)了‘神’”〔3〕;“美固無(wú)所不在,凡屬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 即無(wú)不可見(jiàn)出其精巧處和完整處。生命之最高意義,即此種‘神在生命中’的認(rèn)識(shí)。”〔4〕正是用各種感覺(jué)捕捉“美”和“生命”的人,才會(huì)于沉思靜觀中領(lǐng)悟人生之道,因緣際會(huì),水造就了沈從文柔中帶剛、無(wú)堅(jiān)不摧的性格。
黃永玉曾這樣描述沈從文:“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樣平常,永遠(yuǎn)向下,向人民流動(dòng),滋善生靈,長(zhǎng)年累月生發(fā)出水磨石穿的力量。”這是對(duì)沈從文人格的由衷贊嘆和評(píng)價(jià),一語(yǔ)中的地指出沈從文人格中最重要的特質(zhì):追求“善”和“上”。
【第2句】:以水為中心的文化系統(tǒng)
水熏染著沈從文的性情和人格,自然對(duì)其創(chuàng)作也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沈從文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故事中我所最滿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為我在水邊船上所見(jiàn)到的人物性格。”〔6〕沈從文的作品形成了一個(gè)以水意象為主,水的衍生意象及與水有關(guān)的周邊意象的體系。無(wú)論是《邊城》、《長(zhǎng)河》等小說(shuō),還是《湘西》、《湘西散記》等散文,無(wú)不以水為背景而展開;水的衍化意象是指:水除了自然流動(dòng)的液體形態(tài)之外,還包括多種變體形式,如雨、云、霧等。沈從文不僅僅把目光投向了水意象本身,同時(shí)對(duì)云、雨、霧等衍化意象也不吝著墨,其中雨是最典型的水的衍生意象。沈從文常常以雨、云為作品命名,如《雨》、《雨后》、《水云》等。同云、雨一樣,沈從文作品的空氣中還到處彌漫著撩人的風(fēng)和縹緲的霧,這些富于詩(shī)意的意象的加入使其筆下美好的湘西世界更加令人神往。如小說(shuō)《漁》表現(xiàn)的是湘西駭人聽(tīng)聞的“殺魚節(jié)”;翠翠(《邊城》)、蕭蕭(《蕭蕭》)等少女都有過(guò)關(guān)于魚的夢(mèng),《第四》中“我”的朋友將魚比作女人;另外頻頻出現(xiàn)的有關(guān)水的周邊意象是船,沈從文直接以船命名的作品多如牛毛:《船上》、《船上岸上》、《石子船》等。船是水手柏子們謀生的工具,也是他們漂泊的家(《柏子》);吃“水上飯”的女子也有。除船外,沈從文還在作品中經(jīng)常描繪碾坊、吊腳樓等頗富地域色彩的近水意象。《三三》中那個(gè)天真活潑的女孩從小便在碾坊旁邊長(zhǎng)大;《邊城》中王鄉(xiāng)紳家的嫁妝是一座碾坊。
綜上所舉,我們可以將沈從文的作品歸屬為一個(gè)以水為大背景的系統(tǒng)。而這個(gè)系統(tǒng)并非只有客觀意象的意義。榮格說(shuō):“每一個(gè)原始意象中都有著人類精神和人類命運(yùn)的一塊碎片,都有著在我們祖先的歷史中重復(fù)了無(wú)數(shù)次歡樂(lè)和悲哀的一點(diǎn)殘余。”〔7〕水及其相關(guān)的意象在湘西這些閉塞的地方由古至今地延續(xù)和保存著,這些意象能通過(guò)歲月的淘洗一直延續(xù)至今,一方面說(shuō)明這些意象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shí)這些意象在其生命延續(xù)的同時(shí)也積淀著一定的歷史和文化。身為“五溪”之子的沈從文早已將水融入自己的生命中,水在沈從文那里,不僅是個(gè)客觀意象,同時(shí)也具有主觀寓意,促使他的作品形成了獨(dú)特的以水為背景的文化系統(tǒng),這一水文化系統(tǒng)的三個(gè)主要方面:生命文化、愛(ài)文化和神巫文化,而統(tǒng)觀這些作品,最能集中體現(xiàn)和透徹展現(xiàn)水文化寓意的是小說(shuō)《邊城》。
【第3句】:水文化的主要意蘊(yùn):生命文化;愛(ài)情文化;神巫文化
水乃萬(wàn)物之源,生命之源。沈從文通過(guò)水來(lái)折射生命,具體表現(xiàn)為:一是借水寓意人類的生存意志,人類強(qiáng)悍的生命力。因?yàn)樗巧衩氐淖匀幻Я?是人的生命韌性的明證。《邊城》中的老船夫和翠翠,老船夫失去了女兒,翠翠一出生沒(méi)了母親,他們都失去了生命中的至親,但他們依舊活著,一條渡船,一只黃狗,一間草屋就是他們的整個(gè)世界。翠翠和老船夫簡(jiǎn)單、純粹的生活,正是水――生命不息,流動(dòng)不止的體現(xiàn),展現(xiàn)出邊地人強(qiáng)悍的生命力。二是寫水邊人的一身蠻野之氣,呼喚人類的原始生命力。水乃陰柔的表征,但其陰柔里仍透著幾分“野蠻”、“雄強(qiáng)”的力量之美。《邊城》里最能體現(xiàn)水――柔中帶剛這一特質(zhì)的就是兩次賽龍舟場(chǎng)景。端午節(jié)是邊地人最重要的節(jié)日之一,端午節(jié)的賽龍舟又是每年端午必舉行的節(jié)日慶典。“帶頭的坐在船頭上,頭上纏裹著紅布包頭,受傷拿兩枝小令旗,左右揮動(dòng),指揮船只的進(jìn)退。擂鼓打鑼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劃動(dòng)即刻蓬蓬鐺鐺把鑼鼓很單純的敲打起來(lái),為劃槳水手調(diào)理下槳節(jié)拍。”〔1〕沈從文不吝筆墨地描繪了邊城里兩次端午節(jié),兩次賽龍舟,突現(xiàn)出邊地人與生俱來(lái)的自然力,那種自然(水)既養(yǎng)育同時(shí)也教育了邊地人的雄壯、澎湃、野蠻的剛強(qiáng)勁,這正是生命原始的力量和美的體現(xiàn)。
《邊城》里寫了水注入邊地人生命的活力,同時(shí)也寫到了生命的結(jié)束,而生命的結(jié)束也與水不可分割。細(xì)心的讀者會(huì)注意到,《邊城》里三次涉及死亡,每一次死亡都與水相聯(lián)。第一次死亡是翠翠的母親,母親的死是故意喝冷水導(dǎo)致的;第二次死亡是大佬,大佬為了成全弟弟決定駕船下行,不幸被水淹死;老船夫因?yàn)橐馔獾淖児识氖轮刂?終于在一個(gè)雷雨交加的夜里辭世,這是文中第三次涉及死亡。 “夜間果然落了大雨,夾以嚇人的雷聲,電光從屋背上掠過(guò)時(shí),接著就是訇的一個(gè)炸雷”。雷雨之后“門前已變成為一個(gè)水溝”,“屋房菜園地已為山水沖亂”, “泊在崖下的渡船,已不見(jiàn)了”。〔2〕老船夫就是在風(fēng)雨交織,雷雨將息的時(shí)候死去。至此,水(雨)已不再是往日的熨帖與柔情,而是成為奪去生命的'刀刃。筆者認(rèn)為,《邊城》里的水文化將其中的生命文化闡釋得最為透徹的緣由就在此。生命文化最主要的兩個(gè)內(nèi)容是生與死,《邊城》里,沈從文不僅展示了邊地人柔中帶剛的生命力,也借水更準(zhǔn)確是借由雨這一意象講述了死亡。正由于水(雨)這一憑借物,淡化了死亡的悲劇性,一定程度上使死亡升華,具有另一層意義:因?yàn)橛赀^(guò)后會(huì)天晴,所以在這里死亡其實(shí)是生命的重生,體現(xiàn)出邊地人向“死”而生的豁達(dá)堅(jiān)強(qiáng)。
就《邊城》的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而言,沈從文如是說(shuō):“我主意不在領(lǐng)導(dǎo)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gè)小城小市中幾個(gè)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tīng)窟B在一處時(shí),各人應(yīng)有的一分哀樂(lè),為人類‘愛(ài)’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shuō)明。”〔8〕《邊城》里,令讀者印象最深的還是翠翠和大佬二佬間隱忍的愛(ài)情。翠翠在陪伴祖父渡船的日子里漸漸接觸了愛(ài)情,情竇初開的翠翠每次思念心中的那個(gè)人(二佬)時(shí),她都會(huì)坐在船上或者岸邊,思緒被周圍的水汽煙霧牽引著走了很遠(yuǎn)。“黃昏照樣的溫柔,美麗和平靜。但一個(gè)人若體念到這個(gè)當(dāng)前一切時(shí),也就照樣地在著黃昏中會(huì)有點(diǎn)兒薄薄的凄涼。于是,這日子成為痛苦的東西了。翠翠覺(jué)得好像卻少了什么。好像眼見(jiàn)到這個(gè)日子過(guò)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3〕這是翠翠心底的觸動(dòng),她想著在千篇一律的日子里能有所改變,想結(jié)識(shí)新的人,新的事來(lái)給平凡的日子注入新鮮的活力,很明顯這是少女思春的心情。“翠翠坐在溪邊,望著溪面為暮色所籠罩的一切,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過(guò)度人……就忽然哭泣來(lái)了。祖父把船拉回來(lái)時(shí),見(jiàn)翠翠癡癡地坐在岸邊,問(wèn)她是什么事,翠翠不做聲……想了一會(huì)兒,覺(jué)得自己哭得可笑,一個(gè)人變回到屋中去。”〔4〕像這樣翠翠坐在水汽氤氳的煙霧中等待的場(chǎng)景讀者一定熟悉,沈從文總是把人物置身于煙霧繚繞的環(huán)境中,營(yíng)造出如煙似霧般的夢(mèng)境,制造出一種朦朧模糊的感覺(jué)。翠翠對(duì)二佬的感情,猶如這煙霧,看得見(jiàn)卻抓不住,若即若離;卻也仿佛是被這層層煙霧所阻隔,唯有將心底的愛(ài)意深藏。水汽煙霧的繚繞與翠翠心底的暗潮相得益彰,恰到好處地渲染了翠翠與二佬間朦朧飄忽隱忍的愛(ài)情。
湘楚的神巫文化極大地影響了沈從文觀照不同生命存在形式的視角,在沈從文的小說(shuō)中總透著一股“神靈”氣息。沈從文創(chuàng)作的《邊城》從宏觀和微觀兩個(gè)層面都反映了神巫文化,而神巫文化都是通過(guò)水及其與之相關(guān)的意象體現(xiàn)的。
從微觀來(lái)看,依山傍水的邊地人自然地生,自然地死,順應(yīng)自然給予的一切安排,把日子一天天地過(guò)下去。“一切總永遠(yuǎn)那么靜寂,所有人民每個(gè)日子皆在這種不可形容的單純寂寞里過(guò)去。一分安靜增加了人對(duì)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夢(mèng)。在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自然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懷了對(duì)于人事愛(ài)憎必然的期待。”〔5〕邊地人為何對(duì)自然如此順應(yīng)和服從?是因?yàn)樵谶叺厝诵闹袘延袑?duì)自然的敬畏,因?yàn)檫叺厝诵叛鎏欤叛錾耢`。每當(dāng)老船夫遇到難解的問(wèn)題時(shí),老船夫總是自我安慰和解脫地說(shuō):“天知道呢?”“一切順應(yīng)天命吧。”正是因?yàn)檫叺厝诵叛錾耢`,他們甘心將一切人事交給自然神靈來(lái)決定,也相信神會(huì)佑護(hù)這方水土百姓。
《邊城》最顯著地體現(xiàn)神巫文化要從宏觀層面來(lái)看:整個(gè)邊地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切都順應(yīng)自然的安排,也順從自然的決定,一水繞城的河流沉默不息地流動(dòng),既襯托著邊地人生命的韌勁和力量,也見(jiàn)證著邊地人的悲喜交加,生離死別:《邊城》里,母親拋下翠翠飲水而死,二佬受良心的譴責(zé)決定劃船下桃源離開了翠翠,最后,翠翠唯一的至親祖父,也在雷雨交加的夜里撒手人寰,遭遇了這一切的翠翠在一夜間長(zhǎng)大。自然既賜予她生命,賜予她苦楚,同時(shí)也賜予她活著的勇氣和力量,所以翠翠依照往常一樣把日子一天天地過(guò)下去。從宏觀來(lái)看,邊城的水就成了自然的縮影,透過(guò)這一派清波的映襯,通過(guò)一連串人事的變幻,折射出自然的“常”與“變”,折射出自然的“定”與“動(dòng)”等規(guī)律。我們讀《邊城》總覺(jué)得從中透著一股神靈之氣,正與沈從文思想里的神巫文化相呼應(yīng)。沈從文通過(guò)對(duì)“水”意象的獨(dú)特領(lǐng)會(huì)和挖掘,從中找到了極富詩(shī)意的藝術(shù)傳達(dá)方式。在水(自然)與人的交相輝映中,構(gòu)筑了一個(gè)和諧美好的湘西世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水中潛埋的文化精髓,水中滲透的文化底蘊(yùn),促使沈從文選擇水來(lái)折射平凡人生里的悲歡離合,理性地思考湘西這片水土這方人民的生命形式和生存方式。
注釋:
〔1〕沈從文・邊城(M)//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74
〔2〕沈從文・邊城(M)//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145
〔3〕沈從文・邊城(M)//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118
〔4〕沈從文・邊城(M)//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99
〔5〕沈從文・邊城(M)//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68
參考文獻(xiàn):
〔1〕〔6〕沈從文.沈從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第2句】:
〔2〕沈從文・水云〔M〕//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0卷・廣州:花城出版社, 19【第84句】:
〔3〕沈從文・燭虛・生命〔M〕//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1卷・廣州:花城出版社, 19【第84句】:
〔4〕沈從文・燭虛・潛淵〔M〕//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1卷・廣州:花城出版社, 19【第84句】:
〔5〕黃永玉.平常的沈從文〔J〕.讀書,2000,(1).
〔7〕榮格・心理學(xué)與文學(xué)〔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19【第87句】:
〔8〕沈從文.習(xí)作選集代序〔A〕.沈從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藝出版社, 200【第2句】:
《邊城》中的沈從文的文化意圖
沈從文在《邊城》中傾注了愛(ài)與理想。下面小編給大家?guī)?lái)。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從《邊城》中的愛(ài)情悲劇看沈從文的文化意圖
摘 要:沈從文在其代表作《邊城》中,構(gòu)建了一個(gè)如田園牧歌般清新純美的童話世界,并以此為背景敘寫了擺渡人的外孫女翠翠與團(tuán)總的兩個(gè)兒子天保和儺送的愛(ài)情悲劇,凄美動(dòng)人。本文從小說(shuō)中故事開展的環(huán)境所體現(xiàn)出的悲劇性出發(fā),深入分析了小說(shuō)愛(ài)情悲劇的原因,并由此探討作者沈從文的文化意圖和文學(xué)理念。
關(guān)鍵詞:邊城 沈從文 愛(ài)情悲劇 悲劇性 文化意圖
《邊城》是沈從文最優(yōu)秀的一部中篇小說(shuō),講述了一個(gè)發(fā)生在美麗的邊遠(yuǎn)小城中的愛(ài)情故事。整個(gè)小說(shuō)都融化在童話一般的色彩中,明凈澄澈,卻含著淡淡的憂傷,隱伏著濃濃的悲劇感。沈從文在小說(shuō)中構(gòu)造的環(huán)境是理想化的、不穩(wěn)定的,翠翠和儺送的愛(ài)情悲劇也有著復(fù)雜而深刻的現(xiàn)實(shí)原因,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對(duì)人性、傳統(tǒng)文明與民族未來(lái)的關(guān)注和對(duì)社會(huì)、文學(xué)的反思。
【第1句】:愛(ài)情悲劇的環(huán)境建構(gòu)
汪曾祺曾在《讀<邊城>》中說(shuō):“《邊城》的生活是真實(shí)的,同時(shí)又是理想化了的,這是一種理想化了的現(xiàn)實(shí)”。沈從文在《邊城》中構(gòu)建的世界是真實(shí)存在的,卻又是理想化了的。在風(fēng)景秀麗、民風(fēng)淳樸的邊城所發(fā)生的愛(ài)情悲劇,其部分原因正是這份童話般的不真實(shí),是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統(tǒng)一與矛盾。
“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dú)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gè)老人,一個(gè)女孩子,一只黃狗。”沈從文在小說(shuō)開始部分首先建造了一個(gè)由三方面組成的“童話世界”,這也是展現(xiàn)翠翠愛(ài)情的主要環(huán)境,隨后輔以風(fēng)景秀麗、民風(fēng)淳樸的邊城這個(gè)大環(huán)境,語(yǔ)言中又常常影射當(dāng)時(shí)被戰(zhàn)亂和商業(yè)文明所包裹的中國(guó)社會(huì),由此建構(gòu)出一個(gè)立體的、由三重空間構(gòu)成的環(huán)境,這樣多層次的環(huán)境有利于小說(shuō)情節(jié)的開展,提升文學(xué)文本的意義層次,但是它也帶有深刻的悲劇感,是愛(ài)情悲劇的一個(gè)重要原因。
首先,小說(shuō)中的“童話世界”是不穩(wěn)定的,本身具有悲劇性。一個(gè)老人,一個(gè)女孩子,一只黃狗,三個(gè)密不可分的個(gè)體組成了一個(gè)看似完美和諧的世界,但這個(gè)世界的平衡是注定要被打破的,老人注定要死亡,翠翠注定要嫁人,當(dāng)其中任何一方發(fā)生變化,或是有陌生人闖入這個(gè)世界時(shí),悲劇便不可避免地發(fā)生。小說(shuō)中愛(ài)情開展的環(huán)境自開始便帶有不可避免的悲劇因素,洋溢著美麗又滲透著憂傷。
其次,小說(shuō)中的“邊城”是作者在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上加以想像和虛構(gòu)的結(jié)果,并非完全真實(shí)存在,注定了它不可能存在持久的生命。沈從文非常堅(jiān)持文學(xué)的獨(dú)立性,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主要體現(xiàn)為內(nèi)容與政治的分離,《邊城》中的故事與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社會(huì)是嚴(yán)重脫離的。“邊城”以未被戰(zhàn)爭(zhēng)、政治、商業(yè)毀滅的湘西為原型,體現(xiàn)出一種未被現(xiàn)代文明所沾染的純潔感,但在沈從文寫作《邊城》的年代(1934年),真實(shí)的湘西雖仍然保有美麗與清新的外表,卻已被現(xiàn)代文明浸染,淳樸原始的生活被利益與人情世故取代,“邊城”不過(guò)是沈從文面對(duì)都市時(shí)對(duì)湘西的記憶與想象的化身,他面對(duì)真實(shí)的湘西時(shí)的失落感可以在其《湘西散記》明顯看出。由此可見(jiàn),沈從文為翠翠與儺送的愛(ài)情悲劇所構(gòu)建的環(huán)境是不真實(shí)的、脫離現(xiàn)實(shí)的,不論是自然環(huán)境,還是社會(huì)環(huán)境,都是注定要被現(xiàn)代文明毀滅的,在這種環(huán)境中孕育出的愛(ài)情,自然也不會(huì)穩(wěn)定持久,蘊(yùn)含著深深的悲劇感。
當(dāng)這具有美麗和憂傷色彩的環(huán)境融入沈從文那樸素清麗、自然明朗的語(yǔ)言中時(shí),《邊城》的不真實(shí)與理想化便得到更加深刻的凸顯,沈先生文字背后的哀傷和對(duì)民族的追憶與迷茫也從幕后走了出來(lái)。但是,《邊城》中人們的生命形式與生活形式是高度統(tǒng)一的,翠翠的悲劇并不僅僅源于環(huán)境構(gòu)建中的悲劇性因素,更包含了人性和文明等現(xiàn)實(shí)性的深層原因,折射出沈從文對(duì)社會(huì)、對(duì)文學(xué)的深入思考。
【第2句】: 愛(ài)情悲劇的深層原因與文化意圖
汪曾祺說(shuō):“《邊城》是一個(gè)溫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隱伏著作者的很深的悲劇感。”①翠翠的愛(ài)情悲劇有著多方面的現(xiàn)實(shí)原因,而這些也正是小說(shuō)深刻悲劇感的來(lái)源,體現(xiàn)出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
【第1句】:人性的孤獨(dú)
研究沈從文的美國(guó)學(xué)者金介甫曾說(shuō):“《邊城》總的'來(lái)說(shuō)是寫人類靈魂的相互孤立。”②
《邊城》中的人物都有著鮮明而美好的人性特征:爺爺真誠(chéng)熱情、耿直大方,翠翠單純可愛(ài)、天真活潑,順順豪爽灑脫、正直慷慨,天保心直口快、和氣忠義,儺送聰明美麗、真摯爽快,甚至連船上的小姐也重義輕利、鐘情守信,整個(gè)邊城的人民是淳樸真誠(chéng)的,到處洋溢著安靜和平的氛圍。他們都表現(xiàn)出一種“優(yōu)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③,沈從文曾多次在作品中對(duì)這種純樸自然的人生形式予以高度贊揚(yáng)。
但是,《邊城》中的人物雖都有著健康而優(yōu)美的人性,有著親情和愛(ài)情的羈絆,看似親密,但他們?cè)陟`魂上實(shí)則是相互孤立的,這種靈魂上的隔絕狀態(tài)導(dǎo)致了淳樸環(huán)境下、美好愛(ài)情中的一條條裂縫,最終串聯(lián)在一起導(dǎo)致了悲劇結(jié)局。例如,爺爺關(guān)心呵護(hù)著翠翠的成長(zhǎng),卻不懂得翠翠青春期少女的想法和心屬儺送的真意,他們之間從來(lái)沒(méi)有真正坦誠(chéng)地交談過(guò),這不僅誤導(dǎo)了天保,也造成了爺爺知道實(shí)情后的猶豫行為,最終被接連的打擊擊倒;而翠翠和儺送雖然兩情相悅,卻始終沒(méi)有敞開心扉坦誠(chéng)相待,翠翠的害羞被動(dòng)、儺送的消極不主動(dòng)使得他們的愛(ài)情從開始便不是對(duì)等的交流,以至于翠翠甚至不知道是誰(shuí)在向她唱歌求婚;而且,翠翠的天真害羞使得她對(duì)愛(ài)情采取了被動(dòng)逃避的態(tài)度,致使天保得到的答復(fù)含混其詞,進(jìn)一步導(dǎo)致了天保和儺送的競(jìng)爭(zhēng),從而加速了悲劇的產(chǎn)生。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實(shí)際上是他們?nèi)鄙凫`魂上的交流而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悲劇產(chǎn)生的最為直接的原因。
沈從文賦予了小說(shuō)中的人物以美好的人性和純真的心靈,他們善良、真誠(chéng)、相互愛(ài)護(hù)、不愿?jìng)λ耍谴浯涞膼?ài)情卻以悲劇收尾,作者正是通過(guò)這種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感與矛盾感,在暗指悲劇的原因不在于主人公的內(nèi)心和偶然的命運(yùn)因素,而在于外在的物質(zhì)力量和相互之間的精神力量的同時(shí),突出表現(xiàn)了其對(duì)美好人性的歌頌和對(duì)“真”與“愛(ài)”的追求,以及對(duì)人性的孤獨(dú)的深入思索。 【第2句】:文化的沖突
愛(ài)情悲劇產(chǎn)生的另外一個(gè)原因是文化沖突導(dǎo)致了從屬不同文化的人們之間的不理解與誤會(huì)。
一方面是翠翠和爺爺所代表的原始文化與團(tuán)總女兒和磨坊所代表的現(xiàn)代文明的沖突。翠翠與爺爺在自然、淳樸的邊城中生活,體現(xiàn)的是邊城的原住民文化特征:寂靜和平、單純寂寞地生活著,熱情慷慨,多贈(zèng)送的情分而少金錢的功利。鄉(xiāng)紳女兒的新鮮打扮和作為陪嫁的磨坊則最為鮮明地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文明的商業(yè)性質(zhì)和世俗特征。而處于兩者文化之間的儺送走南闖北,受到了現(xiàn)代文化的熏染,雖仍保持著邊城人民的淳樸熱情,但身上的原始特性已有所消失。因而,在原始與現(xiàn)代的沖突之下,如同文化的必然對(duì)立,翠翠與儺送雖相互傾慕卻似乎總有些“不湊巧”的巧合在離間著他們之間的情感。
另一方面則是苗族傳統(tǒng)文化與外來(lái)文化(包括漢文化)的沖突。爺爺是土生土長(zhǎng)的苗族人,在面對(duì)天保的求親時(shí),想的是“照規(guī)矩”,“車是車路,馬是馬路,各有走法”,要求天保按照苗族傳統(tǒng)求婚;而中寨人有意與順順結(jié)親時(shí),則是派鄉(xiāng)紳女兒與鄉(xiāng)紳太太親自前去查看作為陪嫁的磨坊和儺送。爺爺式的傳統(tǒng)是典型的苗族文化,而中寨人的做法則代表了日漸滲透并取代苗族傳統(tǒng)文化的外族文化特征,兩者的沖突其實(shí)也是一種精神文明的沖突,在兩者的對(duì)比下,翠翠與儺送的愛(ài)情悲劇意味更顯濃重。
1934 年的中國(guó)社會(huì)正面臨著外來(lái)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的強(qiáng)烈沖擊,生活上的變化引發(fā)了思想上的激蕩,沈先生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思考也流露在《邊城》中。正如他所說(shuō),“我就永遠(yuǎn)不習(xí)慣城里人所習(xí)慣的道德的愉快、倫理的愉快。我崇拜朝氣,喜歡自由,贊美膽量大的,精力強(qiáng)的。”④他向往自由、健康、甚至帶有些許愚昧的人生形態(tài),在文化沖突中選擇了傳統(tǒng)文化,并將這沖突表現(xiàn)在作品中,希望能夠進(jìn)一步引發(fā)讀者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注意與思索,期望能夠探索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未來(lái)。
【第3句】: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
我認(rèn)為翠翠的愛(ài)情悲劇最為根本的原因是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導(dǎo)致了邊城原始文明的剝離,“邊城”的逐漸消逝影響到了原有文明圈內(nèi)的個(gè)人。
《邊城》開始部分描述邊城是“有秩序”的,人民“安分樂(lè)生”,“中國(guó)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掙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遠(yuǎn)不會(huì)為這邊城人民所感到”。然而,在小說(shuō)結(jié)尾部分,作者又借經(jīng)歷了整個(gè)變動(dòng)的楊馬兵發(fā)出了“時(shí)代變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還消說(shuō)!”的感慨。可見(jiàn),現(xiàn)代物質(zhì)文明、現(xiàn)代政治對(duì)這個(gè)地方的平凡人物的生活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現(xiàn)實(shí)因素不斷反映在小說(shuō)中,“印花布”、“美孚燈罩”等工業(yè)文明成果的出現(xiàn),儺送與中寨團(tuán)總女兒的親事對(duì)儺送與翠翠的愛(ài)情的沖擊等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改變了中國(guó)社會(huì),也改變了《邊城》中人們的命運(yùn),翠翠的愛(ài)情悲劇不過(guò)是眾多被改變的命運(yùn)中的一點(diǎn)影子。在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下,邊城所代表的原始、淳樸、安靜和平的傳統(tǒng)文明、以及那種有別于都市的完整、協(xié)調(diào)的獨(dú)立環(huán)境必然消失的命運(yùn)是沈從文著重表現(xiàn)的,正如他在《〈邊城〉題記》中這樣說(shuō)道:“我的讀者應(yīng)是有理性,而這點(diǎn)理性便基于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社會(huì)有所關(guān)心,認(rèn)識(shí)這個(gè)民族的過(guò)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里很寂寞的從事于民族復(fù)興大業(yè)的人。”他企圖通過(guò)展現(xiàn)湘西民間社會(huì)與傳統(tǒng)文化之美,告誡讀者中國(guó)的生機(jī)在民間,中國(guó)的希望在民族傳統(tǒng)中,倡導(dǎo)人們向民族的輝煌歷史與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中國(guó)的出路。作者試圖通過(guò)對(duì)中華民族逝去歷史的追憶和對(duì)目前狀況的批判,引發(fā)人們對(duì)自身、對(duì)民族未來(lái)的思考,優(yōu)美的愛(ài)情悲劇之后隱藏的是作者熾熱的愛(ài)國(guó)之心和深刻的文化關(guān)懷。
參考文獻(xiàn):
[1] 沈從文,《沈從文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第84句】:
[2] 韓立群,《沈從文論――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化的反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第94句】:
[3] 沈從文,《沈從文批評(píng)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第98句】:
[4] 金介甫[美],《沈從文筆下的中國(guó)社會(huì)與文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第94句】:
[5] 金介甫[美],《沈從文傳》,北京:中國(guó)友誼出版公司,2000.
[6] 朱光潛,《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fēng)格》,《我所認(rèn)識(shí)的沈從文》,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第86句】:
注解
① 汪曾祺.《又讀<邊城>》,見(jiàn)《汪曾祺文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第93句】:
② 金介甫[美].《沈從文傳》.北京:中國(guó)友誼出版公司.2000.
③ 沈從文.《<從文小說(shuō)習(xí)作選>代序》,劉洪濤.見(jiàn)《沈從文批評(píng)文集》.珠海出版社,19【第98句】:
④ 沈從文.《序跋集<籬下集>題記》,見(jiàn)《沈從文文集》,第11卷.33頁(yè).廣州:城出版社;香港: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84年.
從《邊城》中的愛(ài)情悲劇看沈從文的文化意圖
沈從文一生寫下很多部小說(shuō)和散文集,但是在他眾多的作品之中,《邊城》則占據(jù)著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張地說(shuō),正是《邊城》奠定了沈從文先生在文學(xué)史上的歷史地位。下面小編給大家?guī)?lái) 從《邊城》中的愛(ài)情悲劇看沈從文的文化意圖。希望大家喜歡。
從《邊城》中的愛(ài)情悲劇看沈從文的文化意圖
摘 要:沈從文在其代表作《邊城》中,構(gòu)建了一個(gè)如田園牧歌般清新純美的童話世界,并以此為背景敘寫了擺渡人的外孫女翠翠與團(tuán)總的兩個(gè)兒子天保和儺送的愛(ài)情悲劇,凄美動(dòng)人。本文從小說(shuō)中故事開展的環(huán)境所體現(xiàn)出的悲劇性出發(fā),深入分析了小說(shuō)愛(ài)情悲劇的原因,并由此探討作者沈從文的文化意圖和文學(xué)理念。
關(guān)鍵詞:邊城 沈從文 愛(ài)情悲劇 悲劇性 文化意圖
《邊城》是沈從文最優(yōu)秀的一部中篇小說(shuō),講述了一個(gè)發(fā)生在美麗的邊遠(yuǎn)小城中的愛(ài)情故事。整個(gè)小說(shuō)都融化在童話一般的色彩中,明凈澄澈,卻含著淡淡的憂傷,隱伏著濃濃的悲劇感。沈從文在小說(shuō)中構(gòu)造的環(huán)境是理想化的、不穩(wěn)定的,翠翠和儺送的愛(ài)情悲劇也有著復(fù)雜而深刻的現(xiàn)實(shí)原因,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對(duì)人性、傳統(tǒng)文明與民族未來(lái)的關(guān)注和對(duì)社會(huì)、文學(xué)的反思。
【第1句】:愛(ài)情悲劇的環(huán)境建構(gòu)
汪曾祺曾在《讀<邊城>》中說(shuō):“《邊城》的生活是真實(shí)的,同時(shí)又是理想化了的,這是一種理想化了的現(xiàn)實(shí)”。沈從文在《邊城》中構(gòu)建的世界是真實(shí)存在的,卻又是理想化了的。在風(fēng)景秀麗、民風(fēng)淳樸的邊城所發(fā)生的愛(ài)情悲劇,其部分原因正是這份童話般的不真實(shí),是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統(tǒng)一與矛盾。
“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dú)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gè)老人,一個(gè)女孩子,一只黃狗。”沈從文在小說(shuō)開始部分首先建造了一個(gè)由三方面組成的“童話世界”,這也是展現(xiàn)翠翠愛(ài)情的主要環(huán)境,隨后輔以風(fēng)景秀麗、民風(fēng)淳樸的邊城這個(gè)大環(huán)境,語(yǔ)言中又常常影射當(dāng)時(shí)被戰(zhàn)亂和商業(yè)文明所包裹的中國(guó)社會(huì),由此建構(gòu)出一個(gè)立體的、由三重空間構(gòu)成的環(huán)境,這樣多層次的環(huán)境有利于小說(shuō)情節(jié)的開展,提升文學(xué)文本的意義層次,但是它也帶有深刻的悲劇感,是愛(ài)情悲劇的一個(gè)重要原因。
首先,小說(shuō)中的“童話世界”是不穩(wěn)定的,本身具有悲劇性。一個(gè)老人,一個(gè)女孩子,一只黃狗,三個(gè)密不可分的個(gè)體組成了一個(gè)看似完美和諧的世界,但這個(gè)世界的平衡是注定要被打破的,老人注定要死亡,翠翠注定要嫁人,當(dāng)其中任何一方發(fā)生變化,或是有陌生人闖入這個(gè)世界時(shí),悲劇便不可避免地發(fā)生。小說(shuō)中愛(ài)情開展的環(huán)境自開始便帶有不可避免的悲劇因素,洋溢著美麗又滲透著憂傷。
其次,小說(shuō)中的“邊城”是作者在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上加以想像和虛構(gòu)的結(jié)果,并非完全真實(shí)存在,注定了它不可能存在持久的生命。沈從文非常堅(jiān)持文學(xué)的獨(dú)立性,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主要體現(xiàn)為內(nèi)容與政治的分離,《邊城》中的故事與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社會(huì)是嚴(yán)重脫離的。“邊城”以未被戰(zhàn)爭(zhēng)、政治、商業(yè)毀滅的湘西為原型,體現(xiàn)出一種未被現(xiàn)代文明所沾染的純潔感,但在沈從文寫作《邊城》的年代(1934年),真實(shí)的湘西雖仍然保有美麗與清新的外表,卻已被現(xiàn)代文明浸染,淳樸原始的生活被利益與人情世故取代,“邊城”不過(guò)是沈從文面對(duì)都市時(shí)對(duì)湘西的記憶與想象的化身,他面對(duì)真實(shí)的湘西時(shí)的失落感可以在其《湘西散記》明顯看出。由此可見(jiàn),沈從文為翠翠與儺送的愛(ài)情悲劇所構(gòu)建的.環(huán)境是不真實(shí)的、脫離現(xiàn)實(shí)的,不論是自然環(huán)境,還是社會(huì)環(huán)境,都是注定要被現(xiàn)代文明毀滅的,在這種環(huán)境中孕育出的愛(ài)情,自然也不會(huì)穩(wěn)定持久,蘊(yùn)含著深深的悲劇感。
當(dāng)這具有美麗和憂傷色彩的環(huán)境融入沈從文那樸素清麗、自然明朗的語(yǔ)言中時(shí),《邊城》的不真實(shí)與理想化便得到更加深刻的凸顯,沈先生文字背后的哀傷和對(duì)民族的追憶與迷茫也從幕后走了出來(lái)。但是,《邊城》中人們的生命形式與生活形式是高度統(tǒng)一的,翠翠的悲劇并不僅僅源于環(huán)境構(gòu)建中的悲劇性因素,更包含了人性和文明等現(xiàn)實(shí)性的深層原因,折射出沈從文對(duì)社會(huì)、對(duì)文學(xué)的深入思考。
【第2句】: 愛(ài)情悲劇的深層原因與文化意圖
汪曾祺說(shuō):“《邊城》是一個(gè)溫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隱伏著作者的很深的悲劇感。”①翠翠的愛(ài)情悲劇有著多方面的現(xiàn)實(shí)原因,而這些也正是小說(shuō)深刻悲劇感的來(lái)源,體現(xiàn)出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
【第1句】:人性的孤獨(dú)
研究沈從文的美國(guó)學(xué)者金介甫曾說(shuō):“《邊城》總的來(lái)說(shuō)是寫人類靈魂的相互孤立。”②
《邊城》中的人物都有著鮮明而美好的人性特征:爺爺真誠(chéng)熱情、耿直大方,翠翠單純可愛(ài)、天真活潑,順順豪爽灑脫、正直慷慨,天保心直口快、和氣忠義,儺送聰明美麗、真摯爽快,甚至連船上的妓也重義輕利、鐘情守信,整個(gè)邊城的人民是淳樸真誠(chéng)的,到處洋溢著安靜和平的氛圍。他們都表現(xiàn)出一種“優(yōu)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③,沈從文曾多次在作品中對(duì)這種純樸自然的人生形式予以高度贊揚(yáng)。
但是,《邊城》中的人物雖都有著健康而優(yōu)美的人性,有著親情和愛(ài)情的羈絆,看似親密,但他們?cè)陟`魂上實(shí)則是相互孤立的,這種靈魂上的隔絕狀態(tài)導(dǎo)致了淳樸環(huán)境下、美好愛(ài)情中的一條條裂縫,最終串聯(lián)在一起導(dǎo)致了悲劇結(jié)局。例如,爺爺關(guān)心呵護(hù)著翠翠的成長(zhǎng),卻不懂得翠翠青春期少女的想法和心屬儺送的真意,他們之間從來(lái)沒(méi)有真正坦誠(chéng)地交談過(guò),這不僅誤導(dǎo)了天保,也造成了爺爺知道實(shí)情后的猶豫行為,最終被接連的打擊擊倒;而翠翠和儺送雖然兩情相悅,卻始終沒(méi)有敞開心扉坦誠(chéng)相待,翠翠的害羞被動(dòng)、儺送的消極不主動(dòng)使得他們的愛(ài)情從開始便不是對(duì)等的交流,以至于翠翠甚至不知道是誰(shuí)在向她唱歌求婚;而且,翠翠的天真害羞使得她對(duì)愛(ài)情采取了被動(dòng)逃避的態(tài)度,致使天保得到的答復(fù)含混其詞,進(jìn)一步導(dǎo)致了天保和儺送的競(jìng)爭(zhēng),從而加速了悲劇的產(chǎn)生。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實(shí)際上是他們?nèi)鄙凫`魂上的交流而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悲劇產(chǎn)生的最為直接的原因。
沈從文賦予了小說(shuō)中的人物以美好的人性和純真的心靈,他們善良、真誠(chéng)、相互愛(ài)護(hù)、不愿?jìng)λ耍谴浯涞膼?ài)情卻以悲劇收尾,作者正是通過(guò)這種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感與矛盾感,在暗指悲劇的原因不在于主人公的內(nèi)心和偶然的命運(yùn)因素,而在于外在的物質(zhì)力量和相互之間的精神力量的同時(shí),突出表現(xiàn)了其對(duì)美好人性的歌頌和對(duì)“真”與 “愛(ài)”的追求,以及對(duì)人性的孤獨(dú)的深入思索。
【第2句】:文化的沖突
愛(ài)情悲劇產(chǎn)生的另外一個(gè)原因是文化沖突導(dǎo)致了從屬不同文化的人們之間的不理解與誤會(huì)。
一方面是翠翠和爺爺所代表的原始文化與團(tuán)總女兒和磨坊所代表的現(xiàn)代文明的沖突。翠翠與爺爺在自然、淳樸的邊城中生活,體現(xiàn)的是邊城的原住民文化特征:寂靜和平、單純寂寞地生活著,熱情慷慨,多贈(zèng)送的情分而少金錢的功利。鄉(xiāng)紳女兒的新鮮打扮和作為陪嫁的磨坊則最為鮮明地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文明的商業(yè)性質(zhì)和世俗特征。而處于兩者文化之間的儺送走南闖北,受到了現(xiàn)代文化的熏染,雖仍保持著邊城人民的淳樸熱情,但身上的原始特性已有所消失。因而,在原始與現(xiàn)代的沖突之下,如同文化的必然對(duì)立,翠翠與儺送雖相互傾慕卻似乎總有些“不湊巧”的巧合在離間著他們之間的情感。
另一方面則是苗族傳統(tǒng)文化與外來(lái)文化(包括漢文化)的沖突。爺爺是土生土長(zhǎng)的苗族人,在面對(duì)天保的求親時(shí),想的是“照規(guī)矩”,“車是車路,馬是馬路,各有走法”,要求天保按照苗族傳統(tǒng)求婚;而中寨人有意與順順結(jié)親時(shí),則是派鄉(xiāng)紳女兒與鄉(xiāng)紳太太親自前去查看作為陪嫁的磨坊和儺送。爺爺式的傳統(tǒng)是典型的苗族文化,而中寨人的做法則代表了日漸滲透并取代苗族傳統(tǒng)文化的外族文化特征,兩者的沖突其實(shí)也是一種精神文明的沖突,在兩者的對(duì)比下,翠翠與儺送的愛(ài)情悲劇意味更顯濃重。
1934年的中國(guó)社會(huì)正面臨著外來(lái)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的強(qiáng)烈沖擊,生活上的變化引發(fā)了思想上的激蕩,沈先生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思考也流露在《邊城》中。正如他所說(shuō), “我就永遠(yuǎn)不習(xí)慣城里人所習(xí)慣的道德的愉快、倫理的愉快。我崇拜朝氣,喜歡自由,贊美膽量大的,精力強(qiáng)的。”④他向往自由、健康、甚至帶有些許愚昧的人生形態(tài),在文化沖突中選擇了傳統(tǒng)文化,并將這沖突表現(xiàn)在作品中,希望能夠進(jìn)一步引發(fā)讀者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注意與思索,期望能夠探索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未來(lái)。
【第3句】: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
我認(rèn)為翠翠的愛(ài)情悲劇最為根本的原因是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導(dǎo)致了邊城原始文明的剝離,“邊城”的逐漸消逝影響到了原有文明圈內(nèi)的個(gè)人。
《邊城》開始部分描述邊城是“有秩序”的,人民“安分樂(lè)生”,“中國(guó)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掙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遠(yuǎn)不會(huì)為這邊城人民所感到”。然而,在小說(shuō)結(jié)尾部分,作者又借經(jīng)歷了整個(gè)變動(dòng)的楊馬兵發(fā)出了“時(shí)代變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還消說(shuō)!”的感慨。可見(jiàn),現(xiàn)代物質(zhì)文明、現(xiàn)代政治對(duì)這個(gè)地方的平凡人物的生活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現(xiàn)實(shí)因素不斷反映在小說(shuō)中,“印花布”、“美孚燈罩”等工業(yè)文明成果的出現(xiàn),儺送與中寨團(tuán)總女兒的親事對(duì)儺送與翠翠的愛(ài)情的沖擊等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改變了中國(guó)社會(huì),也改變了《邊城》中人們的命運(yùn),翠翠的愛(ài)情悲劇不過(guò)是眾多被改變的命運(yùn)中的一點(diǎn)影子。在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下,邊城所代表的原始、淳樸、安靜和平的傳統(tǒng)文明、以及那種有別于都市的完整、協(xié)調(diào)的獨(dú)立環(huán)境必然消失的命運(yùn)是沈從文著重表現(xiàn)的,正如他在《〈邊城〉題記》中這樣說(shuō)道:“我的讀者應(yīng)是有理性,而這點(diǎn)理性便基于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社會(huì)有所關(guān)心,認(rèn)識(shí)這個(gè)民族的過(guò)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里很寂寞的從事于民族復(fù)興大業(yè)的人。”他企圖通過(guò)展現(xiàn)湘西民間社會(huì)與傳統(tǒng)文化之美,告誡讀者中國(guó)的生機(jī)在民間,中國(guó)的希望在民族傳統(tǒng)中,倡導(dǎo)人們向民族的輝煌歷史與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中國(guó)的出路。作者試圖通過(guò)對(duì)中華民族逝去歷史的追憶和對(duì)目前狀況的批判,引發(fā)人們對(duì)自身、對(duì)民族未來(lái)的思考,優(yōu)美的愛(ài)情悲劇之后隱藏的是作者熾熱的愛(ài)國(guó)之心和深刻的文化關(guān)懷。
參考文獻(xiàn):
[1] 沈從文,《沈從文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第84句】:
[2] 韓立群,《沈從文論——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化的反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第94句】:
[3] 沈從文,《沈從文批評(píng)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第98句】:
[4] 金介甫[美],《沈從文筆下的中國(guó)社會(huì)與文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第94句】:
[5] 金介甫[美],《沈從文傳》,北京:中國(guó)友誼出版公司,2000.
[6] 朱光潛,《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fēng)格》,《我所認(rèn)識(shí)的沈從文》,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第86句】:
注解
① 汪曾祺.《又讀<邊城>》,見(jiàn)《汪曾祺文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第93句】:
② 金介甫[美].《沈從文傳》.北京:中國(guó)友誼出版公司.2000.
③ 沈從文.《<從文小說(shuō)習(xí)作選>代序》,劉洪濤.見(jiàn)《沈從文批評(píng)文集》.珠海出版社,19【第98句】:
④ 沈從文.《序跋集·<籬下集>題記》,見(jiàn)《沈從文文集》,第11卷.33頁(yè).廣州:城出版社;香港: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84年.
沈從文的文化意圖
在《邊城》中的翠翠的悲劇愛(ài)情故事,反映了在那個(gè)時(shí)代的一些人文方面的文化內(nèi)涵,但是還反映了沈從文先生的辦文化意圖。下面小編給大家?guī)?lái)看沈從文的文化意圖。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從《邊城》中的愛(ài)情悲劇看沈從文的文化意圖
摘 要:沈從文在其代表作《邊城》中,構(gòu)建了一個(gè)如田園牧歌般清新純美的童話世界,并以此為背景敘寫了擺渡人的外孫女翠翠與團(tuán)總的兩個(gè)兒子天保和儺送的愛(ài)情悲劇,凄美動(dòng)人。本文從小說(shuō)中故事開展的環(huán)境所體現(xiàn)出的悲劇性出發(fā),深入分析了小說(shuō)愛(ài)情悲劇的原因,并由此探討作者沈從文的文化意圖和文學(xué)理念。
關(guān)鍵詞:邊城 沈從文 愛(ài)情悲劇 悲劇性 文化意圖
《邊城》是沈從文最優(yōu)秀的一部中篇小說(shuō),講述了一個(gè)發(fā)生在美麗的邊遠(yuǎn)小城中的愛(ài)情故事。整個(gè)小說(shuō)都融化在童話一般的色彩中,明凈澄澈,卻含著淡淡的憂傷,隱伏著濃濃的悲劇感。沈從文在小說(shuō)中構(gòu)造的環(huán)境是理想化的、不穩(wěn)定的,翠翠和儺送的愛(ài)情悲劇也有著復(fù)雜而深刻的現(xiàn)實(shí)原因,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對(duì)人性、傳統(tǒng)文明與民族未來(lái)的關(guān)注和對(duì)社會(huì)、文學(xué)的反思。
【第1句】:愛(ài)情悲劇的環(huán)境建構(gòu)
汪曾祺曾在《讀<邊城>》中說(shuō):“《邊城》的生活是真實(shí)的,同時(shí)又是理想化了的,這是一種理想化了的現(xiàn)實(shí)”。沈從文在《邊城》中構(gòu)建的世界是真實(shí)存在的,卻又是理想化了的。在風(fēng)景秀麗、民風(fēng)淳樸的邊城所發(fā)生的愛(ài)情悲劇,其部分原因正是這份童話般的不真實(shí),是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統(tǒng)一與矛盾。
“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dú)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gè)老人,一個(gè)女孩子,一只黃狗。”沈從文在小說(shuō)開始部分首先建造了一個(gè)由三方面組成的“童話世界”,這也是展現(xiàn)翠翠愛(ài)情的主要環(huán)境,隨后輔以風(fēng)景秀麗、民風(fēng)淳樸的邊城這個(gè)大環(huán)境,語(yǔ)言中又常常影射當(dāng)時(shí)被戰(zhàn)亂和商業(yè)文明所包裹的中國(guó)社會(huì),由此建構(gòu)出一個(gè)立體的、由三重空間構(gòu)成的環(huán)境,這樣多層次的環(huán)境有利于小說(shuō)情節(jié)的開展,提升文學(xué)文本的意義層次,但是它也帶有深刻的悲劇感,是愛(ài)情悲劇的一個(gè)重要原因。
首先,小說(shuō)中的“童話世界”是不穩(wěn)定的,本身具有悲劇性。一個(gè)老人,一個(gè)女孩子,一只黃狗,三個(gè)密不可分的個(gè)體組成了一個(gè)看似完美和諧的世界,但這個(gè)世界的平衡是注定要被打破的,老人注定要死亡,翠翠注定要嫁人,當(dāng)其中任何一方發(fā)生變化,或是有陌生人闖入這個(gè)世界時(shí),悲劇便不可避免地發(fā)生。小說(shuō)中愛(ài)情開展的環(huán)境自開始便帶有不可避免的悲劇因素,洋溢著美麗又滲透著憂傷。
其次,小說(shuō)中的“邊城”是作者在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上加以想像和虛構(gòu)的結(jié)果,并非完全真實(shí)存在,注定了它不可能存在持久的生命。沈從文非常堅(jiān)持文學(xué)的獨(dú)立性,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主要體現(xiàn)為內(nèi)容與政治的分離,《邊城》中的故事與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社會(huì)是嚴(yán)重脫離的。“邊城”以未被戰(zhàn)爭(zhēng)、政治、商業(yè)毀滅的湘西為原型,體現(xiàn)出一種未被現(xiàn)代文明所沾染的純潔感,但在沈從文寫作《邊城》的年代(1934年),真實(shí)的湘西雖仍然保有美麗與清新的外表,卻已被現(xiàn)代文明浸染,淳樸原始的生活被利益與人情世故取代,“邊城”不過(guò)是沈從文面對(duì)都市時(shí)對(duì)湘西的記憶與想象的化身,他面對(duì)真實(shí)的湘西時(shí)的失落感可以在其《湘西散記》明顯看出。由此可見(jiàn),沈從文為翠翠與儺送的愛(ài)情悲劇所構(gòu)建的環(huán)境是不真實(shí)的、脫離現(xiàn)實(shí)的,不論是自然環(huán)境,還是社會(huì)環(huán)境,都是注定要被現(xiàn)代文明毀滅的,在這種環(huán)境中孕育出的愛(ài)情,自然也不會(huì)穩(wěn)定持久,蘊(yùn)含著深深的悲劇感。
當(dāng)這具有美麗和憂傷色彩的環(huán)境融入沈從文那樸素清麗、自然明朗的語(yǔ)言中時(shí),《邊城》的不真實(shí)與理想化便得到更加深刻的凸顯,沈先生文字背后的哀傷和對(duì)民族的追憶與迷茫也從幕后走了出來(lái)。但是,《邊城》中人們的生命形式與生活形式是高度統(tǒng)一的,翠翠的悲劇并不僅僅源于環(huán)境構(gòu)建中的悲劇性因素,更包含了人性和文明等現(xiàn)實(shí)性的深層原因,折射出沈從文對(duì)社會(huì)、對(duì)文學(xué)的深入思考。
【第2句】: 愛(ài)情悲劇的深層原因與文化意圖
汪曾祺說(shuō):“《邊城》是一個(gè)溫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隱伏著作者的很深的悲劇感。”①翠翠的愛(ài)情悲劇有著多方面的現(xiàn)實(shí)原因,而這些也正是小說(shuō)深刻悲劇感的來(lái)源,體現(xiàn)出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
【第1句】:人性的孤獨(dú)
研究沈從文的美國(guó)學(xué)者金介甫曾說(shuō):“《邊城》總的來(lái)說(shuō)是寫人類靈魂的相互孤立。”②
《邊城》中的人物都有著鮮明而美好的人性特征:爺爺真誠(chéng)熱情、耿直大方,翠翠單純可愛(ài)、天真活潑,順順豪爽灑脫、正直慷慨,天保心直口快、和氣忠義,儺送聰明美麗、真摯爽快,甚至連船上的妓(ji)女也重義輕利、鐘情守信,整個(gè)邊城的人民是淳樸真誠(chéng)的,到處洋溢著安靜和平的氛圍。他們都表現(xiàn)出一種“優(yōu)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③,沈從文曾多次在作品中對(duì)這種純樸自然的人生形式予以高度贊揚(yáng)。
但是,《邊城》中的.人物雖都有著健康而優(yōu)美的人性,有著親情和愛(ài)情的羈絆,看似親密,但他們?cè)陟`魂上實(shí)則是相互孤立的,這種靈魂上的隔絕狀態(tài)導(dǎo)致了淳樸環(huán)境下、美好愛(ài)情中的一條條裂縫,最終串聯(lián)在一起導(dǎo)致了悲劇結(jié)局。例如,爺爺關(guān)心呵護(hù)著翠翠的成長(zhǎng),卻不懂得翠翠青春期少女的想法和心屬儺送的真意,他們之間從來(lái)沒(méi)有真正坦誠(chéng)地交談過(guò),這不僅誤導(dǎo)了天保,也造成了爺爺知道實(shí)情后的猶豫行為,最終被接連的打擊擊倒;而翠翠和儺送雖然兩情相悅,卻始終沒(méi)有敞開心扉坦誠(chéng)相待,翠翠的害羞被動(dòng)、儺送的消極不主動(dòng)使得他們的愛(ài)情從開始便不是對(duì)等的交流,以至于翠翠甚至不知道是誰(shuí)在向她唱歌求婚;而且,翠翠的天真害羞使得她對(duì)愛(ài)情采取了被動(dòng)逃避的態(tài)度,致使天保得到的答復(fù)含混其詞,進(jìn)一步導(dǎo)致了天保和儺送的競(jìng)爭(zhēng),從而加速了悲劇的產(chǎn)生。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實(shí)際上是他們?nèi)鄙凫`魂上的交流而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悲劇產(chǎn)生的最為直接的原因。
沈從文賦予了小說(shuō)中的人物以美好的人性和純真的心靈,他們善良、真誠(chéng)、相互愛(ài)護(hù)、不愿?jìng)λ耍谴浯涞膼?ài)情卻以悲劇收尾,作者正是通過(guò)這種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感與矛盾感,在暗指悲劇的原因不在于主人公的內(nèi)心和偶然的命運(yùn)因素,而在于外在的物質(zhì)力量和相互之間的精神力量的同時(shí),突出表現(xiàn)了其對(duì)美好人性的歌頌和對(duì)“真”與 “愛(ài)”的追求,以及對(duì)人性的孤獨(dú)的深入思索。
【第2句】:文化的沖突
愛(ài)情悲劇產(chǎn)生的另外一個(gè)原因是文化沖突導(dǎo)致了從屬不同文化的人們之間的不理解與誤會(huì)。
一方面是翠翠和爺爺所代表的原始文化與團(tuán)總女兒和磨坊所代表的現(xiàn)代文明的沖突。翠翠與爺爺在自然、淳樸的邊城中生活,體現(xiàn)的是邊城的原住民文化特征:寂靜和平、單純寂寞地生活著,熱情慷慨,多贈(zèng)送的情分而少金錢的功利。鄉(xiāng)紳女兒的新鮮打扮和作為陪嫁的磨坊則最為鮮明地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文明的商業(yè)性質(zhì)和世俗特征。而處于兩者文化之間的儺送走南闖北,受到了現(xiàn)代文化的熏染,雖仍保持著邊城人民的淳樸熱情,但身上的原始特性已有所消失。因而,在原始與現(xiàn)代的沖突之下,如同文化的必然對(duì)立,翠翠與儺送雖相互傾慕卻似乎總有些“不湊巧”的巧合在離間著他們之間的情感。
另一方面則是苗族傳統(tǒng)文化與外來(lái)文化(包括漢文化)的沖突。爺爺是土生土長(zhǎng)的苗族人,在面對(duì)天保的求親時(shí),想的是“照規(guī)矩”,“車是車路,馬是馬路,各有走法”,要求天保按照苗族傳統(tǒng)求婚;而中寨人有意與順順結(jié)親時(shí),則是派鄉(xiāng)紳女兒與鄉(xiāng)紳太太親自前去查看作為陪嫁的磨坊和儺送。爺爺式的傳統(tǒng)是典型的苗族文化,而中寨人的做法則代表了日漸滲透并取代苗族傳統(tǒng)文化的外族文化特征,兩者的沖突其實(shí)也是一種精神文明的沖突,在兩者的對(duì)比下,翠翠與儺送的愛(ài)情悲劇意味更顯濃重。
1934年的中國(guó)社會(huì)正面臨著外來(lái)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的強(qiáng)烈沖擊,生活上的變化引發(fā)了思想上的激蕩,沈先生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思考也流露在《邊城》中。正如他所說(shuō),“我就永遠(yuǎn)不習(xí)慣城里人所習(xí)慣的道德的愉快、倫理的愉快。我崇拜朝氣,喜歡自由,贊美膽量大的,精力強(qiáng)的。”④他向往自由、健康、甚至帶有些許愚昧的人生形態(tài),在文化沖突中選擇了傳統(tǒng)文化,并將這沖突表現(xiàn)在作品中,希望能夠進(jìn)一步引發(fā)讀者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注意與思索,期望能夠探索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未來(lái)。
【第3句】: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
我認(rèn)為翠翠的愛(ài)情悲劇最為根本的原因是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導(dǎo)致了邊城原始文明的剝離,“邊城”的逐漸消逝影響到了原有文明圈內(nèi)的個(gè)人。
《邊城》開始部分描述邊城是“有秩序”的,人民“安分樂(lè)生”,“中國(guó)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掙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遠(yuǎn)不會(huì)為這邊城人民所感到”。然而,在小說(shuō)結(jié)尾部分,作者又借經(jīng)歷了整個(gè)變動(dòng)的楊馬兵發(fā)出了“時(shí)代變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還消說(shuō)!”的感慨。可見(jiàn),現(xiàn)代物質(zhì)文明、現(xiàn)代政治對(duì)這個(gè)地方的平凡人物的生活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現(xiàn)實(shí)因素不斷反映在小說(shuō)中,“印花布”、“美孚燈罩”等工業(yè)文明成果的出現(xiàn),儺送與中寨團(tuán)總女兒的親事對(duì)儺送與翠翠的愛(ài)情的沖擊等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改變了中國(guó)社會(huì),也改變了《邊城》中人們的命運(yùn),翠翠的愛(ài)情悲劇不過(guò)是眾多被改變的命運(yùn)中的一點(diǎn)影子。在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下,邊城所代表的原始、淳樸、安靜和平的傳統(tǒng)文明、以及那種有別于都市的完整、協(xié)調(diào)的獨(dú)立環(huán)境必然消失的命運(yùn)是沈從文著重表現(xiàn)的,正如他在《〈邊城〉題記》中這樣說(shuō)道:“我的讀者應(yīng)是有理性,而這點(diǎn)理性便基于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社會(huì)有所關(guān)心,認(rèn)識(shí)這個(gè)民族的過(guò)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里很寂寞的從事于民族復(fù)興大業(yè)的人。”他企圖通過(guò)展現(xiàn)湘西民間社會(huì)與傳統(tǒng)文化之美,告誡讀者中國(guó)的生機(jī)在民間,中國(guó)的希望在民族傳統(tǒng)中,倡導(dǎo)人們向民族的輝煌歷史與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中國(guó)的出路。作者試圖通過(guò)對(duì)中華民族逝去歷史的追憶和對(duì)目前狀況的批判,引發(fā)人們對(duì)自身、對(duì)民族未來(lái)的思考,優(yōu)美的愛(ài)情悲劇之后隱藏的是作者熾熱的愛(ài)國(guó)之心和深刻的文化關(guān)懷。
參考文獻(xiàn):
[1] 沈從文,《沈從文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第84句】:
[2] 韓立群,《沈從文論——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化的反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第94句】:
[3] 沈從文,《沈從文批評(píng)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第98句】:
[4] 金介甫[美],《沈從文筆下的中國(guó)社會(huì)與文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第94句】:
[5] 金介甫[美],《沈從文傳》,北京:中國(guó)友誼出版公司,2000.
[6] 朱光潛,《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fēng)格》,《我所認(rèn)識(shí)的沈從文》,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第86句】:
注解
① 汪曾祺.《又讀<邊城>》,見(jiàn)《汪曾祺文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第93句】:
② 金介甫[美].《沈從文傳》.北京:中國(guó)友誼出版公司.2000.
③ 沈從文.《<從文小說(shuō)習(xí)作選>代序》,劉洪濤.見(jiàn)《沈從文批評(píng)文集》.珠海出版社,19【第98句】:
④ 沈從文.《序跋集·<籬下集>題記》,見(jiàn)《沈從文文集》,第11卷.33頁(yè).廣州:城出版社;香港: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