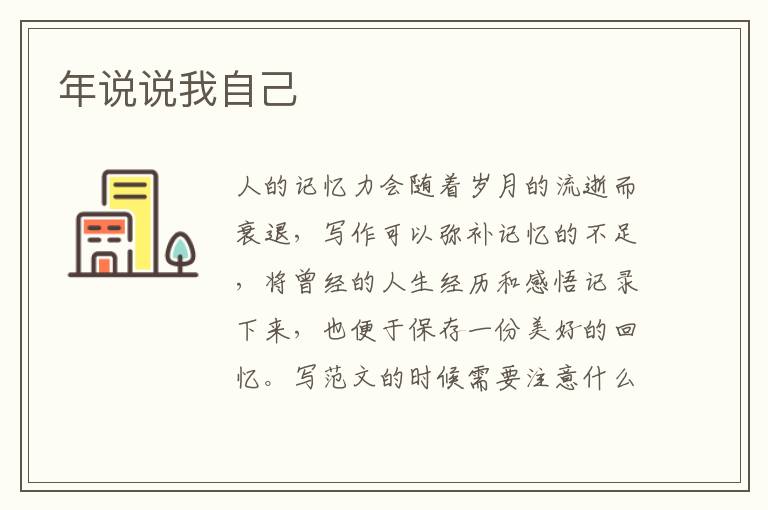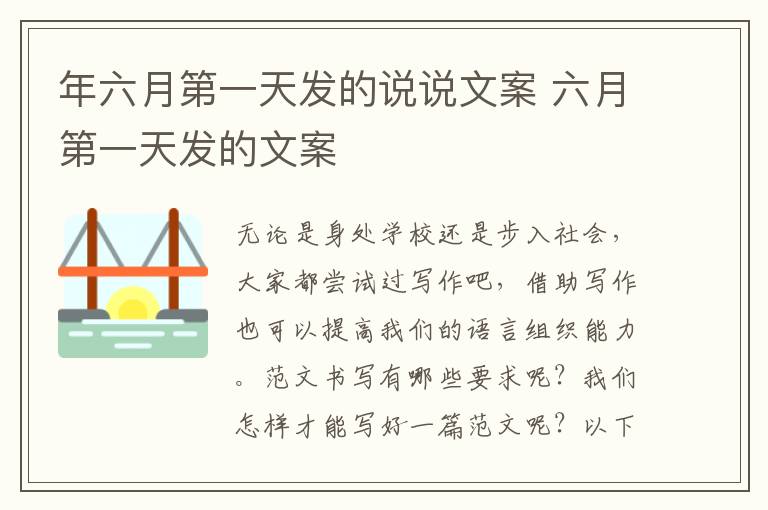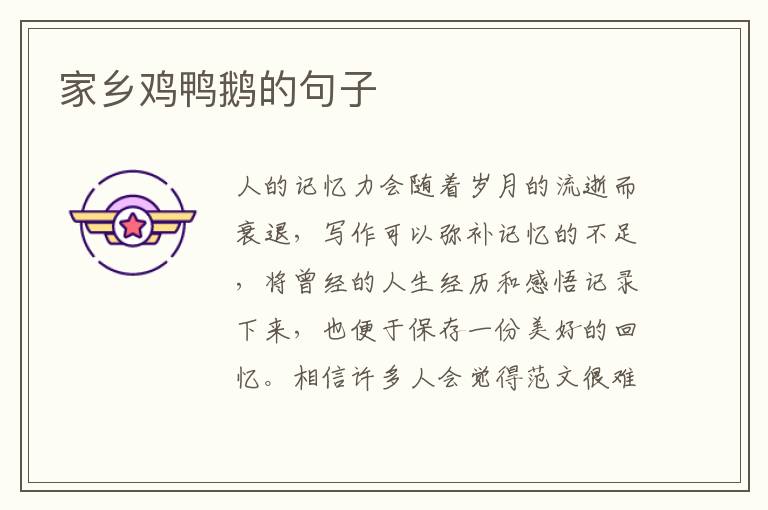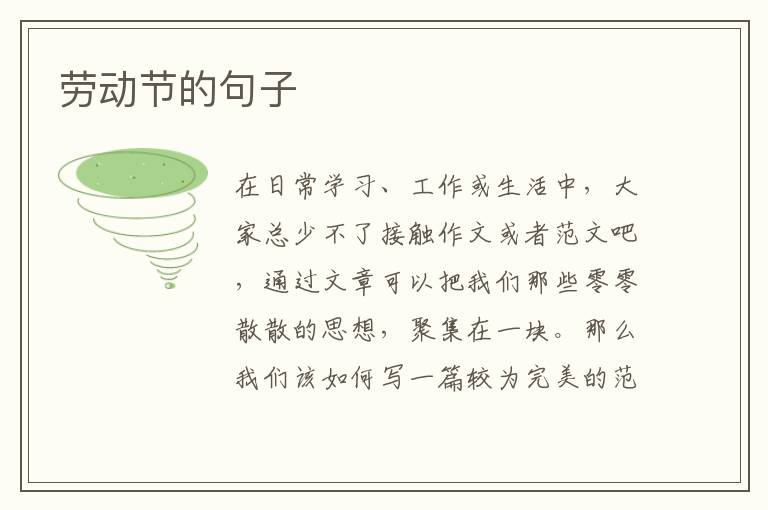吃栗子吃半個的說說聚集90條

梁實秋談吃-栗子
引導(dǎo)語:在家庭生活中如果再增添一點飲食文化,那么梁實秋談吃的文字是不可不讀,我們一起閱讀下文小編收集的梁實秋談吃中的栗子。
栗子以良鄉(xiāng)的為最有名。良鄉(xiāng)縣在河北,北平的西南方,平漢鐵路線上。其地盛產(chǎn)栗子。然栗樹北方到處皆有,固不必限于良鄉(xiāng)。
我家住在北平大取燈胡同的時候,小園中亦有栗樹一株,初僅丈許,不數(shù)年高二丈以上,結(jié)實累累。果苞若刺猬,若老雞頭,遍體芒刺,內(nèi)含栗兩三顆。熟時不摘取則自行墜落,苞破而栗出。搗碎果苞取栗,有漿液外流,可做染料。后來我在嶗山上看見過巨大的栗子樹,高三丈以上,果苞落下狼藉滿地,無人理會。
在北平,每年秋節(jié)過后,大街上幾乎每一家干果子鋪門外都支起一個大鐵鍋,翹起短短的一截?zé)焽瑁粋€小利巴揮動大鐵鏟,翻炒栗子。不是干炒,是用沙炒,加上糖使沙結(jié)成大大小小的粒,所以叫做糖炒栗子。煙煤的黑煙擴散,嘩啦嘩啦的翻炒聲,間或有栗子的爆炸聲,織成一片好熱鬧的晚秋初冬的景致。孩子們沒有不愛吃栗子的,幾個銅板買一包,草紙包起,用麻莖兒捆上,熱乎乎的,有時簡直是燙手熱,拿回家去一時舍不得吃完,藏在被窩垛里保溫。
煮咸水栗子是另一種吃法。在栗子上切十字形裂口,在鍋里煮,加鹽。栗子是甜滋滋的,加上咸,別有風(fēng)味。煮時不妨加些八角之類的香料。冷食熱食均佳。
但是最妙的是以栗子做點心。北平西車站食堂是有名的西餐館。所制“奶油栗子面兒”或稱“奶油栗子粉”實在是一絕。栗子磨成粉,就好像花生粉一樣,干松松的,上面澆大量奶油。所謂奶油就是打攪過的奶油(whipped cream)。用小勺取食,味妙無窮。奶油要新鮮,打攪要適度,打得不夠稠固然不好吃,打過了頭卻又稀釋了。東安市場的中興茶樓和國強西點鋪后來也仿制,工料不夠水準,稍形遜色。北海仿膳之栗子面小窩頭,我吃不出栗子味。
杭州西湖煙霞嶺下翁家山的桂花是出名的,尤其是滿家弄,不但桂花特別的香,而且桂花盛時栗子正熟,桂花煮栗子成了路邊小店的`無上佳品。徐志摩告訴我,每值秋后必去訪桂,吃一碗煮栗子,認為是一大享受。有一年他去了,桂花被雨摧殘凈盡,他感而寫了一首詩“這年頭活著不易”。
十幾年前在西雅圖海濱市場閑逛,出得門來忽聞異香,遙見一意大利人推小車賣炒栗。論個賣——五角錢一個,我們一家六口就買了六顆,坐在車里分而嘗之。如今我們這里到冬天也有小販賣“良鄉(xiāng)栗子”了。韓國進口的栗子大而無當(dāng),并且糊皮,不足取。
讀《梁實秋談吃》有感
冰心說:“一個人應(yīng)當(dāng)像一朵花不論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要好的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算梁實秋最像一朵花。”讀了《梁實秋談吃》這本書,更加理解了冰心的這句話,無怪乎作家冰心評價他是才、情、趣并舉的男人中的“一枝花”。 梁實秋散文成就很高,曠達幽默,文學(xué)造詣極高的他,博古通今,談起吃來,信手拈來,體現(xiàn)了梁實秋的“才”。如首篇《饞》一文中,談到:“在英文里找不到一個十分適當(dāng)?shù)淖帧A_馬暴君尼祿,以至于英國的亨利八世,在大宴群臣的時候,常見其撕下一根根又粗又壯的雞腿,舉起來大嚼,旁若無人,好一副饕餮相!但那不是饞。埃及廢王法魯克,據(jù)說每天早餐一口氣吃二十個荷包蛋,也不是饞,只是放肆,只是沒有吃相。對有某一種食物有所偏好,對于大量的吃,這是貪得無厭。饞,則著重在食物的質(zhì),最需要滿足的是品味。上天生人,在他嘴里安放一條舌,舌上還有無數(shù)的味蕾,教人焉得不饞?饞,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發(fā)展成為近于藝術(shù)的趣味。也許我們中國人特別饞一些。饞字從食毚聲。毚音饞,本義是狡兔,善于奔走,人為了口腹之欲,不惜多方奔走以膏饞吻,所謂‘為了一張嘴,跑斷兩條腿’。真正的饞人,為了吃,決不懶。”梁實秋從亨利八世的饕餮相、埃及廢王法魯克的貪得無厭到解釋饞的真正含義以及真正的饞人,可見梁實秋知識之豐富。我們再看他寫的食物,感情上十分坦率,沒有大家的氣派,語言平實,沒有花架子,但里面卻有著文人那種的淵博與風(fēng)雅,一棵白菜、一塊豬肉、一個湯包、一只燒鴨、一碗豆汁兒,就可以談及典故、縱橫南北,就可以管窺這大千世界。幾乎在每一篇談吃的散文中,融入了不少典籍知識和名家詩詞,使讀者在用視覺享受美食的同時,品味著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
1949年6月,梁實秋負笈移臺,在臺灣,他一方面執(zhí)教,一方面勤奮地從事散文創(chuàng)作,很多談吃的篇章往往托物抒懷,故鄉(xiāng)的“魚丸”連吃三天,使他“齒頰留芬”;想起北平的烤羊肉,使他“垂涎欲滴”;“北平的醬肘子鋪賣一種炸丸子,至今回想起來還回味無窮”。梁實秋在《火腿》一文中對火腿的回憶,不僅是一種飲食需求,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寄托。文章中有三處精彩的描寫,其中有一處記敘了自己在上海吃火腿的往事,“每經(jīng)大馬路,輒至天福市得熟火腿四角錢,店員以利刃切成薄片,瘦肉鮮明似火,肥肉依稀透明,佐酒下飯為無上妙品。至今思之猶有余香。”分明流露出一種懷鄉(xiāng)的情緒。第二處是將家鄉(xiāng)的火腿與臺灣的火腿作對比。“臺灣氣候太熱,不適于制作火腿,但有不少人仿制,結(jié)果不是粗制濫制,
便是腌曬不足急于發(fā)售,帶有死尸味;幸而無尸臭,亦是一味死咸,與‘家鄉(xiāng)肉’無殊。”第三處是晚年偶然間得到一只真的金華火腿時的精彩描寫。“金華火腿,瘦小堅硬,大概是收藏有年。菁清持往熟識商肆,老板奏刀,砉的一聲,劈成兩截。他怔住了。鼻孔翕張,好像是嗅到了異味,驚叫:“這是道地的金華火腿,數(shù)十年不聞此味矣!”他嗅了又嗅不忍釋手,他要求把爪尖送給他,結(jié)果連蹄帶爪都送給他了。他說回家去要好好燉一鍋湯吃。”落筆于老板的情思,其實在心弦的共鳴中,梁實秋的思鄉(xiāng)情結(jié)含蓄而動情地表現(xiàn)了出來。
梁實秋中年以后飄零到孤島,一別就是30多年,幾乎相當(dāng)于自己半生的時間,再也無緣故土,只能眼望海峽對岸,遙念著母親和一雙兒女。這種情況下,當(dāng)年的一雙筷子一只碗,都易勾起他心中絲絲縷縷的感慨,帶有幾許鄉(xiāng)愁,體現(xiàn)了他的“情”。如《豆汁兒》一文中提到:“兒時夏天,梁實秋喝豆汁,總是先脫光上衣,然后喝下豆汁,等到汗落再穿上衣服。”他常說:“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自從離開北平,想念豆汁兒不能自已。有一年我路過濟南,在車站附近一個小飯鋪墻上貼著條子說有“豆汁”發(fā)售。叫了一碗來吃,原來是豆?jié){。是我自己疏忽,寫明的是“豆汁”,不是“豆汁兒”。來到臺灣,有朋友說有一家飯館兒賣豆汁兒,乃偕往一嘗。烏糟糟的兩碗端上來,倒是有一股酸餿之味觸鼻,可是稠糊糊的像麥片粥,到嘴里很難下咽。可見在什么地方吃什么東西,勉強不得。”他坦誠的說過:“自從離開北平,想念豆汁不能自已。”晚年他與北京的長女梁文茜取得聯(lián)系后,在一封信中說:“給我?guī)c豆汁來!”女兒回信道:“豆汁沒法帶,你到北京來喝吧!”他才知道自己糊涂了,不禁啞然失笑。
看這本書時正值春節(jié),每天沉浸于各種吃吃喝喝中,把各種好吃的往嘴里送,一直覺得吃是人生的一種享受。正像梁實秋說的“饞非罪,反而是胃口好、健康的現(xiàn)象,比食而不知其味要好得多。”書中的每一篇篇幅不長卻食之有味,每一道美食躍然于紙上,都體現(xiàn)了梁實秋先生語言的幽默風(fēng)趣。如在描寫車夫的粗獷吃相時寫道:“他把菜肴分為兩份,一份倒在一張餅上,把餅一卷,比拳頭要粗,兩手扶著矗立在盤子上,張開血盆巨口,左一口,右一口,中間一口!不大的功夫,一張餅下肚,又一張也不見了,直吃得他青筋暴露滿臉大汗,挺起腰身連打兩個大飽膈。”描寫細致入微,還帶些夸張,如同漫畫一般,令人捧腹。
從《梁實秋談吃》一書中,感受到了梁先生的才、情、趣。韓少功說:‘如果說美食如今有幾個人還會去從沈從文、汪曾祺他們的散文隨筆中領(lǐng)略?也許,許多人覺得還不如看看眼下火爆的《舌尖上的中國》更活色生香„„” 我想,今天的我們,在提高自身的消費質(zhì)量的同時,在家庭生活中再增添一點飲食文化,梁實秋談吃的文字不可不讀,此書不可不讀!
梁實秋《雅舍談吃》散文集:《栗子》
引導(dǎo)語:我國栗子品種豐富,根據(jù)外形分類大致為兩種,一種為錐栗,主要生產(chǎn)在福建以北山區(qū)。下文是小編整理的梁實秋先生的《雅舍談吃》散文集中的《栗子》原文,我們一起閱讀學(xué)習(xí)吧。
栗子以良鄉(xiāng)的為最有名。良鄉(xiāng)縣在河北,北平的西南方,平漢鐵路線上。其地盛產(chǎn)栗子。然栗樹北方到處皆有,固不必限于良鄉(xiāng)。
我家住在北平大取燈胡同的時候,小園中亦有栗樹一株,初僅丈許,不數(shù)年高二丈以上,結(jié)實累累。果苞若刺謂,若老雞頭,遍體芒刺,內(nèi)含栗兩三顆。熟時不摘取則自行墜落,苞破而栗出。搗碎果苞取栗,有漿液外流,可做染料。后來我在嶗山上看見過巨大的栗子樹,高三丈以上,果苞落下狼藉滿地,無人理會。
在北平,每年秋節(jié)過后,大街上幾乎每一家干果子鋪門外都支起一個大鐵鍋,翹起短短的一截?zé)焽瑁粋€小力巴揮動大鐵鏟,翻炒栗子。不是干炒,是用沙炒,加上糖使沙結(jié)成大大小小的粒,所以叫做糖炒栗子。煙煤的黑煙擴散,嘩啦嘩啦的翻炒聲,間或有粟子的爆炸:聲,織成一片好熱鬧的晚秋初冬的景致。孩子們沒有不愛吃栗子的,幾個銅板買一包,草紙包起,用麻莖兒捆上,熱呼呼的,有時簡直是燙手熱,拿回家去一時舍不得吃完,藏在被窩垛里保溫。
煮咸水栗子是另一種吃法。在栗子上切十字形裂口,在鍋里煮,加鹽。栗子是甜滋滋的,加上咸,別有風(fēng)味。煮時不妨加些八角之類的香料。冷食熱食均佳。
但是最妙的是以栗子做點心。北平西車站食堂是有名的西餐館。所制“奶油栗子面兒”或稱“奶油栗子粉”實在是一絕。栗子磨成粉,就好像花生粉一樣,干松松的,上面澆大量奶油。所謂奶油就是打攪過的奶油(whipped cream)。用小勺取食,味妙無窮。奶油要新鮮,打攪要適度,打得不夠稠自然不好吃;打過了頭卻又稀釋了。東安市場的中興茶樓和國強西點鋪后來也仿制,工料不夠水準,稍形遜色。北海仿膳之栗子面小窩頭,我吃不出栗子味。
杭州西湖煙霞嶺下翁家山的桂花是出名的,尤其是滿家弄,不但桂花特別的香,而且桂花盛時栗子正熟,桂花煮栗子成了路邊小店的無上佳品。徐志摩告訴我,每值秋后必去訪桂,吃一碗煮栗子,認為是一大享受。有一年他去了,桂花被雨摧殘凈盡,他感而寫了一首詩《這年頭活著不易》。
十幾年前在西雅圖海濱市場閑逛,出得門來忽聞異香,遙見一意大利人推小車賣炒栗。論個賣————五角錢一個,我們一家六口就買了六穎,坐在車里分而嘗之。如今我們這里到冬天也有小販賣“良鄉(xiāng)栗子”了。韓國進口的栗子大而無當(dāng),并且糊皮,不足取。
栗子味道--梁實秋
深秋或冬天上街,冷空氣嗖嗖地往鼻腔里鉆,鉆得不知道是心里還是胃里沒來由地有一種空落落的感覺,這時候味覺也敏感起來,有些香味飄過來,好像能彌補這種空,讓人很難拒絕。比如糖炒栗子。
以前不明白栗子為什么加糖炒,加再多的糖其實也給栗子增加不了多少甜味,有些根本沒炒開口呢,難道讓我們嘬皮上的甜味?就算炒進了甜味反而破壞了栗子的'本味,最不能忍受的是吃著黏手,后來才知道單炒栗子容易炒焦和爆炸,加了砂和糖受熱均勻不會爆,而且香甜。就香甜味來說,空氣中那股香甜味里不少是糖的功勞,甜味是很能安慰人的一種味道,這是不容置疑的。
有一朋友客居美國快二十年,年年秋冬季節(jié)都去法拉盛賣煎餅的攤子前問什么時候有炒栗子,賣煎餅的大叔今年就拍著胸脯保證過一陣一定有,而且是空運來的。這是讓人高興的消息,于是滿懷期待,就等著哪天在街上走著走著就飄來那種熟悉的香味兒。她說,曼哈頓五大道燈火最亮的地方冬天也有意大利人揮著小鏟子炒栗子,五塊錢一小紙袋,大概有十來顆,常常看著異國的藍天,就著熱咖啡吃糖炒栗子,那栗子因加了奶油的緣故,味道有些奇怪,但吃著還是有幸福的感覺。
梁實秋寫過杭州西湖邊的滿家弄桂花特別好,而且桂花盛時栗子也熟了,桂花煮栗子成了街邊小店的無上佳品,徐志摩愛吃,每到秋后必去訪桂,吃一碗煮栗子,認為是一大享受,有一年桂花被雨摧殘凈盡,他還因此寫了一首詩《這年頭活著不易》。桂花沒了栗子沒了,于是連活著不易的感慨都生出來了,詩人太感性了,活著真是不易。
我家前后都是山,山上有很多野板栗樹,年年花開得不多,板栗開花跟毛毛蟲似的,顏色也淡,開了遠遠也看不出來,結(jié)球不多。偶爾爸媽上山撿柴,回來兜里揣一把。板栗小得可憐,最大的才拇指肚大。小時候不懂事,往爐子里一扔,火邊的老人一邊罵“也不怕崩瞎了眼”,一邊趕緊用火鉗從火堆里撈出來,咬開口后又往火里一扔。板栗雖小,但好吃得沒法沒法的,不過就那么幾顆,再怎么吧唧嘴也沒有了。沒撈出來的偶爾便炸開了,那陣勢跟放鞭炮似的,村里有個小伙伴也是在火堆里燒栗子,吃得心急了,板栗在嘴里炸開了,人嚇得彈了幾丈遠,雖然沒咋受傷,但故事作為反面教材在村里流傳開了。
有時候也自己上山撿去,得穿雙厚實的解放鞋,那鞋前面有塊膠皮子,鞋面也密,上山穿倒是輕便,也不容易被什么毛刺扎進鞋里,用來搓板栗球最好不過了。樹上的板栗球就別想了,夠不著,要是拿桿子捅下來,板栗球刺猬一樣不留神能扎破頭。就在落葉間扒拉扒拉,有的球綻著,里面就有幾顆,運氣好的話,蟲子還沒光顧過,有些球沒綻開,拎起來放在石上,用腳去碾搓板栗球,運氣好也能得著一兩顆顏色不深不太飽滿的板栗。
長大了就不愛費那勁了,一入秋板栗好買,而且不貴。前天去菜市場買板栗,那大叔問我怎么吃,是燉雞還是怎么著,我說就隔水蒸,他還不放心地交代,“留神別崩了,最好拿菜刀開個小口”。我覺得板栗蒸著吃比煮或炒的好處是一不會含水太多,二又不會崩開或黏手,熱氣騰騰端上來,又甜又沙,天然又健康。吃出幸福感也不奇怪。
汪曾祺談吃 栗子
栗子的形狀很奇怪,像一個小刺猬。栗有“斗”,斗外長了長長的硬刺,很扎手。栗子在斗里圍著長了一圈,一顆一顆緊挨著,很團結(jié)。當(dāng)中有一顆是扁的,叫做臍栗。臍栗的味道和其他栗子沒有什么兩樣。堅果的外面大都有保護層,松子有鱗瓣,核桃、白果都有苦澀的外皮,這大概都是為了對付松鼠而長出來的。
新摘的生栗子很好吃,脆嫩,只是栗殼很不好剝,里面的內(nèi)皮尤其不好去。
把栗子放在竹籃里,掛在通風(fēng)的地方吹幾天,就成了“風(fēng)栗子”。風(fēng)栗子肉微有皺紋,微軟,吃起來更為細膩有韌性。不像吃生栗子會弄得滿嘴都是碎粒,而且更甜。賈寶玉為一件事生了氣,襲人給他打岔,說:“我想吃風(fēng)栗子了。你給我取去。”怡紅院的檐下是掛了一籃風(fēng)栗子的`。風(fēng)栗子入《紅樓夢》,身價就高起來,雅了。這栗子是什么來頭,是賈蓉送來的?劉老老送來的?還是寶玉自己在外面買的?不知道,書中并未交待。
栗子熟食的較多。我的家鄉(xiāng)原來沒有炒栗子,只是放在火里烤。冬天,生一個銅火盆,丟幾個栗子在通紅的炭火里,一會兒,砰的一聲,蹦出一個裂了殼的熟栗子,抓起來,在手里來回倒,連連吹氣使冷,剝殼入口,香甜無比,是雪天的樂事。不過烤栗子要小心,弄不好會炸傷眼睛。烤栗子外國也有,西方有“火中取栗”的寓言,這栗子大概是烤的。
北京的糖炒栗子,過去講究栗子是要良鄉(xiāng)出產(chǎn)的。良鄉(xiāng)栗子比較小,殼薄,炒熟后個個裂開,輕輕一捏,殼就破了,內(nèi)皮一搓就掉,不“護皮”。據(jù)說良鄉(xiāng)栗子原是進貢的,是西太后吃的(北方許多好吃的東西都說是給西太后進過貢)。
北京的糖炒栗子其實是不放糖的,昆明的糖炒栗子真的放糖。昆明栗子大,炒栗子的大鍋都支在店鋪門外,用大如玉米豆的粗砂炒,不時往鍋里倒一碗糖水。昆明炒栗子的外殼是黏的,吃完了手上都是糖汁,必須洗手。栗肉為糖汁沁透,很甜。
炒栗子宋朝就有。筆記里提到的“栗”,我想就是炒栗子。汴京有個叫李和兒的,栗有名。南宋時有一使臣(偶忘其名姓)出使,有人遮道獻栗一囊,即汴京李和兒也。一囊栗,寄托了故國之思,也很感人。
日本人愛吃栗子,但原來日本沒有中國的炒栗子。有一年我在廣交會的座談會上認識一個日本商人,他是來買栗子的(每年都來買)。他在天津曾開過一家炒栗子的店,回國后還賣炒栗子,而且把他在天津開的炒栗子店鋪的招牌也帶到日本去,一直在東京的炒栗子店里掛著。他現(xiàn)在發(fā)了財,很感謝中國的炒栗子。
北京的小酒鋪過去賣煮栗子。栗子用刀切破小口,加水,入花椒大料煮透,是極好的下酒物。現(xiàn)在不見有賣的了。
栗子可以做菜。栗子雞是名菜,也很好做,雞切塊,栗子去皮殼,加蔥、姜、醬油,加水淹沒雞塊,雞塊熟后,下綿白糖,小火燜二十分鐘即得。雞須是當(dāng)年小公雞,栗須完整不碎。羅漢齋亦可加栗子。
我父親曾用白糖煨栗子,加桂花,甚美。
北京東安市場原來有一家賣西式蛋糕、冰點心的鋪子賣奶油栗子粉。栗子粉上澆稀奶油,吃起來很過癮。當(dāng)然,價錢是很貴的。這家鋪子現(xiàn)在沒有了。
羊羹的主料是栗子面。“羊羹”是日本話,其實只是潮濕的栗子面壓成長方形的糕,與羊毫無關(guān)系。
河北的山區(qū)缺糧食,山里多栗樹,鄉(xiāng)民以栗子代糧。栗子當(dāng)零食吃是很好吃的,但當(dāng)糧食吃恐怕胃里不大好受。
梁實秋《談吃》簡介
【梁實秋《談吃》內(nèi)容簡介】
饞非罪,反而是胃口好、健康的現(xiàn)象,比食而不知其要好得多。
饞,則著重在食物的質(zhì),最需要滿足的是品味。上天生人,在他嘴里安放一條舌,舌上還有無數(shù)的味蕾,教人焉得不饞?饞,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發(fā)展成為近于藝術(shù)的趣味。
收錄了梁實秋談吃的全部散文93篇,除了《雅舍談吃》中的57篇外,還找到梁先在其他地方發(fā)表的36篇,是目前梁實秋談吃的最全讀本。
本書不是食譜,不是教人烹飪,不是解析營養(yǎng),只是一位文學(xué)家不忘鄉(xiāng)情,不忘故舊,藉一飲一啄,寫其當(dāng)年的體會。讓我們欣賞其文字,體會其心情。在了解中國吃文化的精雅細致外,唇齒留香,物我交融,愉悅陶然。
梁實秋與唐魯孫、鄧云鄉(xiāng)一起被稱為華人三大美食家。如果您也喜歡吃,并且對吃的感受超過吃的本身,就和這位美食家一起去大飽口福吧!保證讓您吃得更有趣、更煽情!
【梁實秋簡介】
梁實秋(1903—1987),著名文學(xué)評論家、散文家、翻譯家。曾與徐志摩、聞一多創(chuàng)辦新月書店,主編《新月》月刊。后遷至臺,歷任臺北師范學(xué)院英語系主任、英語教研所主任、文學(xué)院院長、國立編譯館館長。代表作有《雅舍小品》、《雅舍談吃》、《看云集》、《偏見集》、《秋室雜文》、長篇散文集《槐園夢憶》等。譯有《莎士比亞全集》等。主編有《遠東英漢大辭典》。
【梁實秋《談吃》精彩摘錄】
蟹是美味,人人喜愛,無間南北,不分雅俗。當(dāng)然我說的是河蟹,不是海蟹。在臺灣有人專程飛到香港去吃大閘蟹。好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從香港帶回了一簍螃蟹,分飧我兩只,得膏饞吻。蟹不一定要大閘的,秋高氣爽的時節(jié),大陸上任何湖沼溪流,岸邊稻米高粱一熟,率多盛產(chǎn)螃蟹。在北平,在上海,小販擔(dān)著螃蟹滿街吆喚。
七尖八團,七月里吃尖臍(雄),八月里吃團臍(雌),那是蟹正肥的季節(jié)。記得小時候在北平,每逢到了這個季節(jié),家里總要大吃幾頓,每人兩只,一尖一團。照例通知長發(fā)送五斤花雕全家共飲。有蟹無酒,那是大殺風(fēng)景的事。晉書·畢卓傳:“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我們雖然沒有那樣狂,也很覺得樂陶陶了。母親對我們說,她小時候在杭州家里吃螃蟹,要慢條斯理,細吹細打,一點蟹肉都不能糟踏,食畢要把破碎的蟹殼放在戥子上稱一下,看誰的一份兒分量輕,表示吃的最干凈,有獎。我心粗氣浮,沒有耐心,蟹的`小腿部分總是棄而不食,肚子部分囫圇略咬而已。每次食畢,母親教我們到后院采擇艾尖一大把,搓碎了洗手,去腥氣。
在餐館里吃“炒蟹肉”,南人稱蟹粉,有肉有黃,免得自己剝殼,吃起來痛快,味道就差多了。西餐館把蟹肉剝出來,填在蟹匡里烤,那種吃法別致,也索然寡味。食蟹而不失原味的唯一方法是放在籠屜里整只的蒸。在北平吃螃蟹唯一好去處是前門外肉市正陽樓。他家的蟹特大而肥,從天津運到北平的大批蟹,到車站開包,正陽樓先下手挑揀其中最肥大者,比普通擺在市場或攤販手中者可以大一倍有余,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獲得這一特權(quán)的。蟹到店中畜在大缸里,澆雞蛋白催肥,一兩天后才應(yīng)客。我曾掀開缸蓋看過,滿缸的蛋白泡沫。食客每人一份小木槌小木墊,黃楊木制,旋床子定制的,小巧合用,敲敲打打,可免牙咬手剝之勞。我們因是老主顧,伙計送了我們好幾副這樣的工具。這個伙計還有一樣絕活,能吃活蟹,請他表演他也不辭。他取來一只活蟹,兩指掐住蟹匡,任它雙螯亂舞輕輕把臍掰開,咔嚓一聲把蟹殼揭開,然后扯碎入口大嚼,看得人無不心驚。據(jù)他說味極美,想來也和吃熗活蝦差不多。在正陽樓吃蟹,每客一尖一團足矣,然后補上一碟烤羊肉夾燒餅而食之,酒足飯飽。別忘了要一碗汆大甲,這碗湯妙趣無窮,高湯一碗煮沸,投下剝好了的蟹螯七八塊,立即起鍋注在碗內(nèi),灑上芫荽末,胡椒粉,和切碎了的回鍋老油條。除了這一味汆大甲,沒有任何別的羹湯可以壓得住這一餐飯的陣腳。以蒸蟹始,以大甲湯終,前后照應(yīng),猶如一篇起承轉(zhuǎn)合的文章。
蟹黃蟹肉有許多種吃法,燒白菜,燒魚唇,燒魚翅,都可以。蟹黃燒賣則尤其可口,惟必須真有蟹黃蟹肉放在餡內(nèi)才好,不是一兩小塊蟹黃擺在外面作樣子的。蟹肉可以腌后收藏起來,是為蟹胥,俗名為蟹醬,這是我們古已有之的美味。周禮·天官·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青州在山東,我在山東住過,卻不曾吃過青州蟹胥,但是我有一佄患以譎競?耐?В??蛹蟻绱?艘恍√承方錘?搖?打開壇子,黃澄澄的蟹油一層,香氣撲鼻。一碗陽春面,加進一兩匙蟹醬,豈止是“清水變雞湯”?
海蟹雖然味較差,但是個子粗大,肉多。從前我乘船路過煙臺威海衛(wèi),停泊之后,舢板云集,大半是販賣螃蟹和大蝦的。都是煮熟了的。價錢便宜,買來就可以吃。雖然微有腥氣,聊勝于無。生平吃海蟹最滿意的一次,是在美國華盛頓州的安哲利斯港的碼頭附近,買得兩只巨蟹,碩大無朋,從冰柜里取出,卻十分新鮮,也是煮熟了的,一家人乘等候輪渡之便,在車上分而食之,味甚鮮美,和河蟹相比各有千秋,這一次的享受至今難忘。
陸放翁詩:“磊落金盤薦糖蟹。”我不知道螃蟹可以加糖。可是古人記載確有其事。《清異錄》:“煬帝幸江州,吳中貢糖蟹。”《夢溪筆談》:“大業(yè)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大抵南人嗜咸,北有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于北俗也。
”如今北人沒有這種風(fēng)俗,至少我沒有吃過甜螃蟹,我只吃過南人的醉蟹,真咸!螃蟹蘸姜醋,是標準的吃法,常有人在醋里加糖,變成酸甜的味道,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