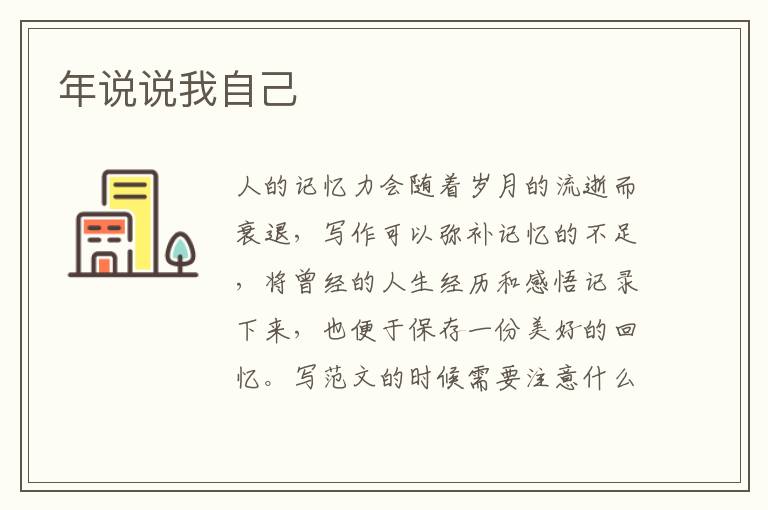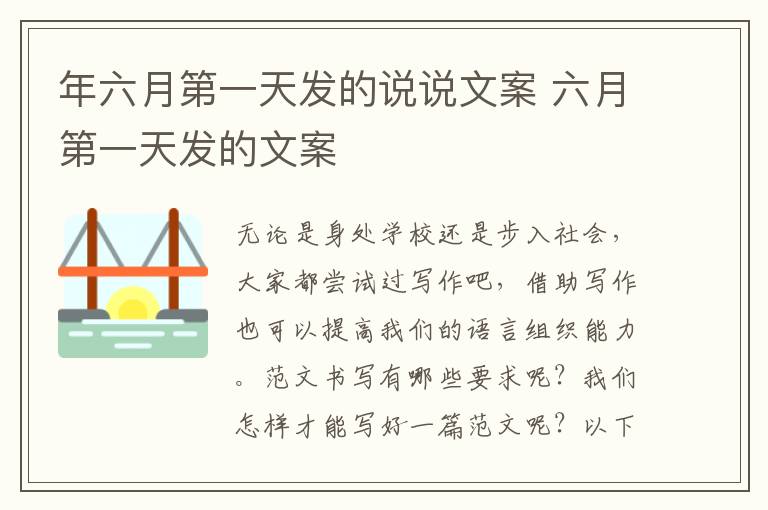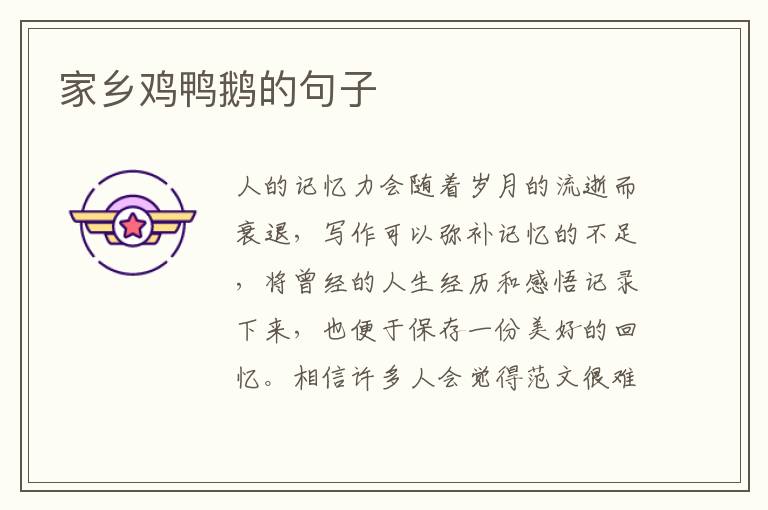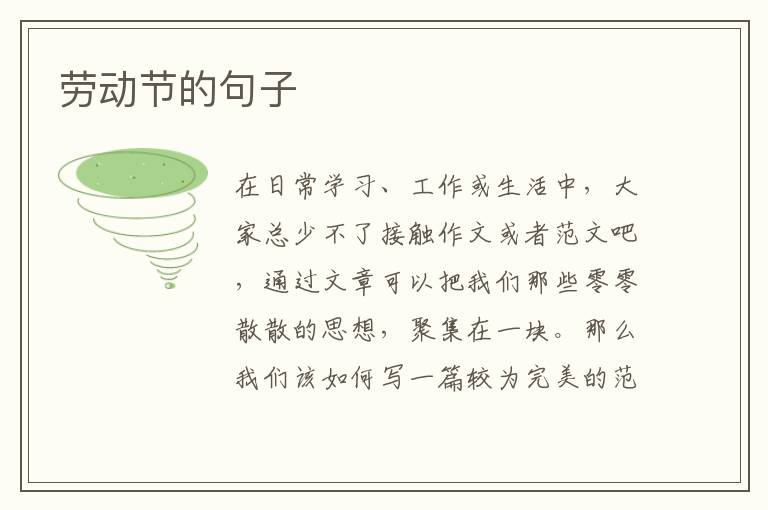李商隱錦瑟描寫珠玉的句子合集90條

李商隱《錦瑟》一詩朦朧美的表現(xiàn)
李商隱的“無題詩”所描繪的畫面唯美、感情真摯、邏輯跳躍、意蘊(yùn)含蓄,為其增添了許多朦朧之美、悲愴之美、生命之美。
隨著唐王朝的日漸衰弱,唐代詩歌的風(fēng)格也由陳子昂提倡“漢魏風(fēng)骨”時(shí)所表現(xiàn)的開闊胸懷、恢宏氣度、積極進(jìn)取的精神走向了由李商隱所建立的深婉精麗、富于感傷、帶有象征暗示色彩的詩歌演變與發(fā)展。在人們看來,李商隱“無題詩”的總體基調(diào)是“濃厚的感傷”,“凄艷而不輕佻”,“濃烈而凄清”。袁行霈在《中國文學(xué)史》中將李詩的基調(diào)概括為“凄艷渾融”,認(rèn)為“他把感傷的情緒注入朦朧瑰麗的詩境,融多方面感觸于沉博絕麗之中,形成凄艷之美”,“并能以艷麗通于渾融,使詩歌在藝術(shù)上有博大的氣象和完整性”。在意境方面,則是具有一種超凡脫俗的朦朧美。“它們要表現(xiàn)的不是一個(gè)故事,而是一種情緒;不是一幅時(shí)間、地點(diǎn)清晰可考的畫面,而只是一種空靈縹緲但是可以把握的意境……在一定程度上,它們具有可以意會(huì)、較難言傳的特點(diǎn)。”這也是從唐向宋蔓延的一種過渡情感,不同于豪放、張揚(yáng)的“盛唐之音”,而是尋求一種含蓄蘊(yùn)藉的“韻外之致”、“味外之趣”。作為“無題詩”之一的《錦瑟》也具有以上特點(diǎn),并且巧妙地運(yùn)用了復(fù)義理論構(gòu)建起一幅幅縹緲、朦朧的美麗畫卷,書寫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世事滄桑,感傷之余又產(chǎn)生無盡的共鳴,朦朧之間又給人余味不盡美的體驗(yàn)。
復(fù)義理論是20世紀(jì)英美新批評(píng)派的代表理論之一。新批評(píng)的代表人物瑞恰慈將語義學(xué)分析方法應(yīng)用于文學(xué)語言的分析,他強(qiáng)調(diào)對(duì)文本進(jìn)行細(xì)讀式的解讀,從文本的意思、情感、語調(diào)、用意入手,結(jié)合語境分析來把握作品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和意義,最終達(dá)到與作者情感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有效交流的目的。燕卜遜在《朦朧的七種類型》中對(duì)“復(fù)義” 所做的定義是“任何語義上的差別,不論如何細(xì)微,只要它使同一句話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映 ”。他認(rèn)為在古典詩歌中,復(fù)義現(xiàn)象是普遍存在的,因?yàn)橹袊械淖衷~都是具有多重意義的整體,復(fù)義理論的使用可以大大增強(qiáng)詩歌的表現(xiàn)力和感染力。在我們現(xiàn)在看來,李商隱的《錦瑟》一詩就運(yùn)用了復(fù)義理論創(chuàng)造出無窮無盡的藝術(shù)魅力。
錦瑟無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mèng)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lán)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dāng)時(shí)已惘然。
首先,此詩語境含混不明,從而引起主旨復(fù)義。人們歷來對(duì)其主旨頗有異議,有“自傷生平說” 、“悼亡說 ”、“政治寄托說” 、“詩序說”、“寄托不明說”、“自寓創(chuàng)作說” 等。通讀全詩,感受到的不是具體的情與事,而是彌漫在詩中的迷茫恍惚和哀怨情結(jié)。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是“錦瑟”之弦勾起作者的回憶,而不是其他的弦?“錦瑟”在此有什么重要的含義或是作用?“華年” 是指什么?莊生夢(mèng)蝶、望帝杜鵑、滄海珠淚、藍(lán)田玉煙這些典故和意象與 “錦瑟”有什么關(guān)系?“此情”是哪種情感,是愛情、親情、友情,還是自懷心事的悲哀之情?為何“可待” 的情感卻成為“追憶”……這么多的不確定造成詩歌語境的模糊,從而給讀者以閱讀后巨大的想象空間,根據(jù)自己的主觀情感對(duì)詩歌進(jìn)行再創(chuàng)造,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千個(gè)讀者就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但全詩追憶感傷的主題與其模糊、朦朧的意境卻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是由隱喻引起的復(fù)義。薩特認(rèn)為,隱喻不僅體現(xiàn)在語言細(xì)節(jié)上,有的詩整體就是一種不明顯的隱喻結(jié)構(gòu),《錦瑟》就是如此。《錦瑟》的隱喻性在于大量用典,這些典故不僅有它的出處和本身的意義,而且作為一種象征性的意象并不僅僅代表本義,它直接參與了詩歌意境的營造,這些典故不是要追憶具體事實(shí),而是構(gòu)造一種象征性結(jié)構(gòu)。四個(gè)典故描繪出四種藝術(shù)意境,即幻夢(mèng)、哀怨、清寥(失意)、縹緲,這也是生命體驗(yàn)的四種象征性符號(hào)的隱喻。
“莊生夢(mèng)蝶”出自《莊子・齊物論》,意在闡述一種“均物我,外形骸” 的道家哲理,“莊生” 喻指精神世界的富足。原文“昔者” ,即昨夜的意思,而作者加上“曉”,不僅與“春”相對(duì),而且表達(dá)了詩人的心境。“曉夢(mèng)”指天明時(shí)的夢(mèng),隱含夢(mèng)境的短暫。蝴蝶在中國文化里象征自由、美麗,也象征靈魂與死亡。蝴蝶還代表著蛻變與變形,幼蟲時(shí)的丑陋不堪象征著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殘酷無形,化蝶后蝴蝶輕盈的彩翼象征著美好與自由的精神世界,但美如幻影,短暫如夢(mèng)。現(xiàn)實(shí)也許是丑陋不盡人意的,但是詩人追求的精神世界卻是美麗崇高的,然而這種美麗與崇高卻也是如此的短暫,如過眼煙云般隨風(fēng)飄逝,也只不過是一個(gè)虛渺的夢(mèng)罷了。
“望帝春心托杜鵑”出自《華陽國志・蜀志》,講的是蜀國君主杜宇,為蜀除水患有功,禪位隱退后,不幸國亡身死,死后魂魄化為鳥,暮春啼苦以至于口中流血,其聲哀怨凄悲,動(dòng)人心腑,名為杜鵑。“望帝”借指“達(dá)則兼濟(jì)天下,窮則獨(dú)善其身” 的人生理想。“春” 即“歲之始也”(《公羊傳・ 隱公元年》),指美好、富有生機(jī)的時(shí)光,“春心”表達(dá)了作者一種美好、愉悅的心情;“杜鵑”其聲如“不如歸去,不如歸去”,象征著不舍與哀怨,喻指宏偉的理想抱負(fù)久久不能實(shí)現(xiàn)的失望與失落。對(duì)“春心” 的追求、向往、執(zhí)著,與杜鵑的悲鳴聯(lián)結(jié)在一起,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包含了無限傷春的意蘊(yùn)。事物雖美好,但是會(huì)被毀滅。詩中“春心”是美好的,但寄托于“杜鵑”卻是哀怨的,“這是何等難以放棄的春心”體現(xiàn)一種理想難以達(dá)成的失意悵惘。⑥
關(guān)于“珠淚”,《博物志》曰:“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jī)織,其眼泣則能出珠。”淚,美麗而易逝。“藍(lán)田玉”,《困學(xué)紀(jì)聞》卷18記載:“戴容州謂詩家之景,如藍(lán)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于此。”玉氣升騰,遠(yuǎn)觀則有,近看卻無,這代表了一種美好的理想,然而它卻無法把握、無法親近,“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頸聯(lián)“滄海月明珠有淚,藍(lán)田日暖玉生煙”,“珠”與“玉” 象征著一切美好的事物;而“月明”與“日暖”,雖一冷一暖,但都象征著美好的情境。“海”與“田”象征著世事的變遷,“滄海桑田”;“月”與“日”又象征著永恒,“與日月同輝”。美好與永恒卻隨著世事變遷成為“淚”與“煙”。“淚”和“煙”象征著美好、縹緲而不可及的事物,同時(shí)也蘊(yùn)含著如煙般輕薄的孤獨(dú)、傷感和憂郁。
這四個(gè)象喻具有多層次性,但邏輯上又是跳躍的,因此難以確定其含義。《錦瑟》的魅力也正體現(xiàn)在用典的獨(dú)特性上,即使明白了典故本來的意思但卻仍然無法詳細(xì)知曉詩人創(chuàng)作詩歌的主旨。因?yàn)槔钌屉[用典有增殖現(xiàn)象,對(duì)所用典故進(jìn)行了再創(chuàng)造,引起讀者對(duì)人生體驗(yàn)的思考,從而具有了多義性。這四個(gè)典故各自表達(dá)意思,彼此獨(dú)立,但在豐富各異的內(nèi)涵之中又有著共同的情趣:莊生夢(mèng)蝶中有迷惘的感嘆,杜鵑啼血與滄海珠淚中有悲涼的.感傷,藍(lán)田日暖、良玉生煙隱約地描摹了世間風(fēng)情迷離恍惚,都深含著渺茫的希望與迷茫的失望。所以說李商隱在詩中更多呈現(xiàn)的是深埋于回憶里的那種迷惘、哀怨、傷感、失意的情緒和心境。《錦瑟》中典故的運(yùn)用充分體現(xiàn)了詩句語義組合的朦朧性和復(fù)義性,這也是李商隱詩歌的藝術(shù)魅力所在。
綜上所述,《錦瑟》這首詩的“審美趣味和藝術(shù)主題完全不同于盛唐,而是沿著中唐這一條線,走進(jìn)更為細(xì)膩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在接受了西方文學(xué)理論的現(xiàn)代人看來,在詩中作者恰巧運(yùn)用了新批評(píng)復(fù)義理論,通過某種朦朧、模糊、復(fù)義的手段或形式,含蓄蘊(yùn)藉地表現(xiàn)出“象外之象,味外之味,韻外之致”,從而塑造出一種“迷離”、“忽隱忽現(xiàn)”、“忽有忽無”的朦朧美。作者懷才不遇,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痛苦、迷惘、孤獨(dú)鑄就了他的詩歌在字里行間所表現(xiàn)的情緒悵惘、混混沌沌、若即若離的朦朧之美。全詩籠罩著一層濃重的哀傷低徊、凄迷朦朧的情調(diào)氛圍,反映出一個(gè)衰頹沒落的時(shí)代正直而不免軟弱的知識(shí)分子典型的悲劇心理:既不滿于環(huán)境的壓抑,又無力反抗黑暗社會(huì);既有所追求向往,又時(shí)感空虛幻滅;既為自己的悲劇命運(yùn)而深沉哀傷,又對(duì)造成悲劇的原因感到惘然。透過這種時(shí)代、人生悲劇心理的表達(dá),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晚唐時(shí)期對(duì)人才志士的摧殘是何等殘忍,封建知識(shí)分子面對(duì)時(shí)代、階級(jí)的局限及自身性格的軟弱是何等的無奈與彷徨。
解讀李商隱詩《錦瑟》
從整體著眼去解析李商隱的名篇《錦瑟》,主要要如何解讀呢?下面來看看!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mèng)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lán)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dāng)時(shí)已惘然。
這首詩歷來眾說紛紜,難以確解。有的認(rèn)為是詩人晚年對(duì)自己一生的總結(jié);有的認(rèn)為是悼亡詩,懷念其亡妻王氏;或是懷念其青年時(shí)所愛戀的一位女道士。甚至有人認(rèn)為是追念已故宰相李德裕。這些理解都有道理,我誰的觀點(diǎn)都不敢否定。詩無達(dá)詁嘛!更何況此詩又將人事全部隱去,全用幾個(gè)典故傳之,更造成一種多義性。不過也無須為此頭痛。更不必逐字逐句胡亂揣測(cè),不妨像陶淵明一樣“不求甚解”地去讀書,你喜歡怎樣理解就怎樣理解,怎樣理解覺得有趣就怎樣理解。其實(shí),你非得像完成選擇題一樣,選出一項(xiàng)標(biāo)準(zhǔn)答案來,恐怕本身就是自討苦吃。
詩是用形象說話的,故而本身就具有多義性,講究含蓄蘊(yùn)藉。讀詩應(yīng)學(xué)會(huì)慢慢品讀,但我不贊成像解剖醫(yī)生一樣肢解作品,更討厭以為字字都有出處或字字都有著落的考證之法。比如李商隱這首《錦瑟》,為什么不試著從整體著眼去理解呢?
首先,“錦瑟”這只是詩人創(chuàng)作的一個(gè)感情觸發(fā)點(diǎn),應(yīng)是它觸發(fā)了詩人對(duì)人生的感慨。首聯(lián)兩句就是直抒胸臆式的感慨之語:這錦瑟為什么要弄五十根弦呢?難道就是為了使其曲調(diào)悲涼嗎?聽其曲便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自己的一生,想起一生的夢(mèng)想,想起年輕時(shí)所愛戀的對(duì)象。
頷聯(lián)、頸聯(lián)四句四個(gè)典故是對(duì)自己一生的形象表述。追憶往事難免使人有往事如煙、人生如夢(mèng)之嘆。四句以“夢(mèng)”起,以“煙”收,是否就暗含了這樣一種感慨呢?不過回想起來,許多事、許多人還是歷歷在目,感情也常常是很復(fù)雜的,遺憾、后悔、傷感、不甘、甜美、懷戀、惆悵,實(shí)在說不清楚。所以,詩人很巧妙地運(yùn)用四個(gè)典故進(jìn)行了非常形象、非常概括地表述。“莊生曉夢(mèng)迷蝴蝶”運(yùn)用的是“莊周夢(mèng)蝶”的典故。《莊子·齊物論》中說:一次莊子晚上夢(mèng)見自己化為蝴蝶,早晨醒來竟然弄不清是自己變成了蝴蝶,還是蝶變成了自己。這是一種什么境界?應(yīng)該就是物我兩忘的無我境界。那種哲學(xué)境界我們不易達(dá)到,可是年輕時(shí)對(duì)事業(yè)的追求、對(duì)愛情的追求,因?yàn)閳?zhí)著、因?yàn)榘V情,就很容易進(jìn)入這種忘我的境界,在別人看來可笑,可自己一無所覺。所以,夢(mèng)醒之后的痛苦就會(huì)更讓外人難以理解。“望帝”死后化為杜鵑的故事,不是抒寫的正是這種痛苦心情嗎?“望帝”,周末蜀王杜宇,號(hào)望帝,相傳他死后魂魄化為啼血的杜鵑鳥。自己苦心經(jīng)營的事業(yè),竟然不堪一擊,或者原本就只是一場(chǎng)夢(mèng)。自己愛戀的人卻陰差陽錯(cuò)地最后嫁給了別人,或者出家為你尼了,怎能不令人像杜鵑鳥一樣啼淚成血呢?我這樣談這兩句詩可不是簡(jiǎn)單臆測(cè),是有根據(jù)的,那么根據(jù)是什么?這就真得說說知人論世,以詩解詩的方法了。“知人論世”,就是要結(jié)合作者身世經(jīng)歷愛好興趣、氣質(zhì)性格來讀詩文。聯(lián)系它作來解讀此作即“以詩解詩”。李商隱出生的時(shí)間不對(duì)頭,已是唐王朝晚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雖說他科第早登,開成二年(837)中進(jìn)士時(shí)年僅25歲。可是仕途并不暢達(dá),尤其是有意無意地竟然卷入了“牛李黨爭(zhēng)”的政治漩渦中,給他帶來許多不幸。一個(gè)骨子里就是詩人的人,怎么能應(yīng)對(duì)無恥的政客官僚們之間那種勾心斗角呢?《憶梅》一詩中有這樣的句子“寒梅最堪恨,長作去年花。”這早凋早秀之“寒梅”不是詩人自己的寫照嗎?它能傲霜雪,能“俏也不爭(zhēng)春,只把春來報(bào)”,可是“待到百花爛漫時(shí)”,它可早已笑不起來了,早已凋落塵泥之中了。能像毛澤東那樣“笑”起來的人不多,那樣高的境界更難達(dá)。尤其是被人摧殘,被人排擠,或遭人陷害就更難“笑”起來了。這是仕途或“事業(yè)”。下面再談?wù)勂?ldquo;風(fēng)流”。才子風(fēng)流,沒有點(diǎn)“風(fēng)流”,哪算“才子”。別誤會(huì)我所說的.風(fēng)流,我不是說有點(diǎn)才華你就應(yīng)該愛情不忠,而是說比常人更懂得真情,更懂愛情一些。你看詩人筆下對(duì)愛情的表述:“相見時(shí)難別亦難,東風(fēng)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diǎn)通。”“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dāng)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shí)。”僅這些詩句我們就可以想象生活中的李商隱之“風(fēng)流”,想見李商隱愛一個(gè)人愛得之執(zhí)著和深沉。但是唯其執(zhí)著、投入、失敗后之打擊痛苦就更非常人能及。故而“望帝春心托杜鵑”一句實(shí)在讓人為之不忍多想。
不過回想起來痛苦的往事。即使是失敗的經(jīng)歷也是美麗的,使人泣淚成珠。藍(lán)田日暖,良玉生煙,兩個(gè)典故中這“珠”“玉”不是寄托了詩人回憶往事時(shí)那種甜美的感情嗎?“滄海月明珠有淚”不該只是“鮫人泣哭”一個(gè)典故。為什么寫“明月”呢?也有一個(gè)非常美麗的傳說。珠生于蚌,蚌生于海,每當(dāng)月明宵靜,蚌則像月張開,以養(yǎng)其珠,珠得月華,始極光瑩。聯(lián)系這個(gè)傳說,這“珠”的意味才更耐人咀嚼。不可只注意“淚”字。那“藍(lán)田日暖玉生煙”一句也一樣,不可只注意“煙”字,珍珠美玉可都是自古被人珍愛之物啊。但是,一切的一切,無論是痛苦還是甜美,都已成往事,無法追回,往事如煙,令人悵惘。關(guān)于“玉生煙”,《封神記》中還記了這樣一則故事,吳王夫差小女紫玉和童子韓重相愛,未能結(jié)合,紫玉氣結(jié)而死。后來韓重坐到紫玉墓前祭吊,紫玉顯形,韓重想擁抱她,她卻像煙一樣地消失了。莫非詩人也有過類似的凄美經(jīng)歷嗎?
尾聯(lián)與開頭的感慨呼應(yīng),更是直抒胸臆式的抒情:此情哪堪再去追憶,就是在當(dāng)時(shí)便已感到惘然了。開頭“思華年”及收尾處之“惘然”,其實(shí)就是此詩詩眼。
你看,這樣讀這首詩不是很有趣嗎?閱讀首先是為了從中獲得審美享受。讀詩,不妨不求甚解,得意而忘形最是有味。
錦瑟 李商隱
《錦瑟》
——李商隱
錦瑟無端五十弦(xián),一弦一柱思(sì)華年。
莊生曉夢(mèng)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lán)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dāng)時(shí)已惘然。
注釋:
【第1句】:錦瑟:裝飾華美的瑟。瑟:撥弦樂器,通常二十五弦。
【第2句】:無端:猶何故。怨怪之詞。
【第3句】:五十弦:這里是托古之詞。作者的原意,當(dāng)也是說錦瑟本應(yīng)是二十五弦。
【第4句】:莊生句:意謂曠達(dá)如莊生,尚為曉夢(mèng)所迷。莊生:莊周。
【第5句】:望帝句:意謂自己的心事只能寄托在化魂的杜鵑上。望帝:相傳蜀帝杜宇,號(hào)望帝,死后其魂化為子規(guī),即杜鵑鳥。
【第6句】:珠有淚:傳說南海外有鮫人,其淚能泣珠。
【第7句】:藍(lán)田:山名,在今陜西,產(chǎn)美玉。
參考翻譯:
錦瑟無緣由地有五十弦,引起我近五十載豐富人生的傷心往事。追思已逝的歲月,其中有一件事對(duì)我半百的人生來說,更是悠悠難忘。
我像莊生夢(mèng)蝶一樣夢(mèng)到了你,到彼岸與你短暫相會(huì),但未來得急暢敘幽情,就夢(mèng)醒在痛苦的另一岸。我醒了,但悲痛未絕,我的思緒又來到杜宇的年代,我化作了杜鵑鳥,你看到我哀啼中泣出的鮮血了嗎?歸來吧!歸來吧!
曾經(jīng)的夜晚,你我共賞明月,傷心處看到你淚眼婆娑;而今的白天,風(fēng)和日麗,只待與你把玩,你卻香消玉殞,化作縷縷輕煙。
悲乎!對(duì)你的款款思念之情,本待慢慢地、詳細(xì)地、長久地追憶,只是自從你玉殞之后,就不堪思量,每當(dāng)思量都悲痛欲絕,腦袋里一片模糊,迷失掉自我。
賞析:
這首《錦瑟》,是李商隱的代表作,愛詩的無不樂道喜吟,堪稱最享盛名;然而它又是最不易講解的一篇難詩。自宋元以來,揣測(cè)紛紛,莫衷一是。 詩題“錦瑟”,是用了起句的頭二個(gè)字。舊說中,原有認(rèn)為這是詠物詩的,但近來注解家似乎都主張:這首詩與瑟事無關(guān),實(shí)是一篇借瑟以隱題的“無題”之作。學(xué)者周汝昌認(rèn)為,它確是不同于一般的詠物體,可也并非只是單純“截取首二字”以發(fā)端比興而與字面毫無交涉的無題詩。它所寫的情事分明是與瑟相關(guān)的。
起聯(lián)兩句,從來的'注解也多有誤會(huì),以為據(jù)此可以判明此篇作時(shí),詩人已“行年五十”,或“年近五十”,故爾云云。其實(shí)不然。“無端”,猶言“沒來由地”、“平白無故地”。此詩人之癡語也。錦瑟本來就有那么多弦,這并無“不是”或“過錯(cuò)”;詩人卻硬來埋怨它:錦瑟呀,你干什么要有這么多條弦?瑟,到底原有多少條弦,到李商隱時(shí)代又實(shí)有多少條弦,其實(shí)都不必“考證”,詩人不過借以遣詞見意而已。據(jù)記載,古瑟五十弦,所以玉溪寫瑟,常用“五十”之?dāng)?shù),如“雨打湘靈五十弦”,“因令五十絲,中道分宮徵”,都可證明,此在詩人原無特殊用意。 “一弦一柱思華年”,關(guān)鍵在于“華年”二字。一弦一柱猶言一音一節(jié)。瑟具弦五十,音節(jié)最為繁富可知,其繁音促節(jié),常令聽者難以為懷。詩人絕沒有讓人去死摳“數(shù)字”的意思。他是說:聆錦瑟之繁弦,思華年之往事;音繁而緒亂,悵惘以難言。所設(shè)五十弦,正為“制造氣氛”,以見往事之千重,情腸之九曲。要想欣賞玉溪此詩,先宜領(lǐng)會(huì)斯旨,正不可膠柱而鼓瑟。宋詞人賀鑄說:“錦瑟華年誰與度?”(《青玉案》)元詩人元好問說:“佳人錦瑟怨華年!” 更多唐詩欣賞敬請(qǐng)關(guān)注“習(xí)古堂國學(xué)網(wǎng)”的唐詩三百首欄目。
(《論詩三十首》)華年,正今語所謂美麗的青春。玉溪此詩最要緊的“主眼”端在華年盛景,所以“行年五十”這才追憶“四十九年”之說,實(shí)在不過是一種迂見罷了。
起聯(lián)用意既明,且看他下文如何承接。
頷聯(lián)的上句,用了《莊子》的一則寓言典故,說的是莊周夢(mèng)見自己身化為蝶,栩栩然而飛,渾忘自家是“莊周”其人了;后來夢(mèng)醒,自家仍然是莊周,不知蝴蝶已經(jīng)何往。玉溪此句是寫:佳人錦瑟,一曲繁弦,驚醒了詩人的夢(mèng)景,不復(fù)成寐。迷含迷失、離去、不至等義。試看他在《秋日晚思》中說:“枕寒莊蝶去”,去即離、逝,亦即他所謂迷者是。曉夢(mèng)蝴蝶,雖出莊生,但一經(jīng)玉溪運(yùn)用,已經(jīng)不止是一個(gè)“栩栩然”的問題了,這里面隱約包涵著美好的情境,卻又是虛緲的夢(mèng)境。本聯(lián)下句中的望帝,是傳說中周朝末年蜀地的君主,名叫杜宇。后來禪位退隱,不幸國亡身死,死后魂化為鳥,暮春啼苦,至于口中流血,其聲哀怨凄悲,動(dòng)人心腑,名為杜鵑。杜宇啼春,這與錦瑟又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呢?原來,錦瑟繁弦,哀音怨曲,引起詩人無限的悲感,難言的冤憤,如聞杜鵑之凄音,送春歸去。一個(gè)“托”字,不但寫了杜宇之托春心于杜鵑,也寫了佳人之托春心于錦瑟,手揮目送之間,花落水流之趣,詩人妙筆奇情,于此已然達(dá)到一個(gè)高潮。
看來,玉溪的“春心托杜鵑”,以冤禽托寫恨懷,而“佳人錦瑟怨華年”提出一個(gè)“怨”字,正是恰得其真實(shí)。玉溪之題詠錦瑟,非同一般閑情瑣緒,其中自有一段奇情深恨在。寫出二人被迫分別之苦,與分別的戀戀不舍,作者以托王之心暗喻對(duì)面對(duì)的結(jié)局的憤恨,與此情的戀戀不舍。
律詩一過頷聯(lián),“起”“承”之后,已到“轉(zhuǎn)”筆之時(shí),筆到此間,大抵前面文情已然達(dá)到小小一頓之處,似結(jié)非結(jié),含意待申。在此下面,點(diǎn)筆落墨,好像重新再“起”似的。其筆勢(shì)或如奇峰突起,或如藕斷絲連,或者推筆宕開,或者明緩暗緊。手法可以不盡相同,而神理脈絡(luò),是有轉(zhuǎn)折而又始終貫注的。當(dāng)此之際,玉溪就寫出了“滄海月明珠有淚”這一名句來。
珠生于蚌,蚌在于海,每當(dāng)月明宵靜,蚌則向月張開,以養(yǎng)其珠,珠得月華,始極光瑩。這是美好的民間傳統(tǒng)之說。月本天上明珠,珠似水中明月;淚以珠喻,自古為然,鮫人泣淚,顆顆成珠,亦是海中的奇情異景。如此,皎月落于滄海之間,明珠浴于淚波之界,月也,珠也,淚也,三耶一耶?一化三耶?三即一耶?在詩人筆下,已然形成一個(gè)難以分辨的妙境。唐人詩中,一筆而有如此豐富的內(nèi)涵、奇麗的聯(lián)想的,舍玉溪生實(shí)不多覯。 那么,海月、淚珠和錦瑟是否也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可以尋味呢?錢起的詠瑟名句不是早就說“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卻飛來”嗎?所以,瑟宜月夜,清怨尤深。如此,滄海月明之境,與瑟之關(guān)聯(lián),不是可以窺探的嗎?
對(duì)于詩人玉溪來說,滄海月明這個(gè)境界,尤有特殊的深厚感情。有一次,他因病中未能躬與河?xùn)|公的“樂營置酒”之會(huì),就寫出了“只將滄海月,高壓赤城霞”的句子。如此看來,他對(duì)此境,一方面于其高曠皓凈十分愛賞,一方面于其凄寒孤寂又十分感傷:一種復(fù)雜的難言的悵惘之懷,溢于言表。
晚唐詩人司空?qǐng)D,引過比他早的戴叔倫的一段話:“詩家美景,如藍(lán)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這里用來比喻的八個(gè)字,簡(jiǎn)直和此詩頸聯(lián)下句的七個(gè)字一模一樣,足見此一比喻,另有根源,可惜后來古籍失傳,竟難重覓出處。今天解此句的,別無參考,引戴語作解說,是否貼切,亦難斷言。晉代文學(xué)家陸機(jī)在他的《文賦》里有一聯(lián)名句:“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藍(lán)田,山名,在今陜西藍(lán)田東南,是有名的產(chǎn)玉之地。此山為日光煦照,蘊(yùn)藏其中的玉氣(古人認(rèn)為寶物都有一種一般目力所不能見的光氣),冉冉上騰,但美玉的精氣遠(yuǎn)察如在,近觀卻無,所以可望而不可置諸眉睫之下,—這代表了一種異常美好的理想景色,然而它是不能把握和無法親近的。玉溪此處,正是在“韞玉山輝,懷珠川媚”的啟示和聯(lián)想下,用藍(lán)田日暖給上句滄海月明作出了對(duì)仗,造成了異樣鮮明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而就字面講,藍(lán)田對(duì)滄海,也是非常工整的,因?yàn)闇孀直玖x是青色。玉溪在詞藻上的考究,也可以看出他的才華和工力。
頸聯(lián)兩句所表現(xiàn)的,是陰陽冷暖、美玉明珠,境界雖殊,而悵恨則一。詩人對(duì)于這一高潔的感情,是愛慕的、執(zhí)著的,然而又是不敢褻瀆、哀思嘆惋的。
尾聯(lián)攏束全篇,明白提出“此情”二字,與開端的“華年”相為呼應(yīng),筆勢(shì)未嘗閃遁。詩句是說:如此情懷,豈待今朝回憶始感無窮悵恨,即在當(dāng)時(shí)早已是令人不勝惘惘了—話是說的“豈待回憶”,意思正在:那么今朝追憶,其為悵恨,又當(dāng)如何!詩人用兩句話表出了幾層曲折,而幾層曲折又只是為了說明那種悵惘的苦痛心情。詩之所以為詩者在于此,玉溪詩之所以為玉溪詩者,尤在于此。
玉溪一生經(jīng)歷,有難言之痛,至苦之情,郁結(jié)中懷,發(fā)為詩句,幽傷要眇,往復(fù)低徊,感染于人者至深。他的一首送別詩中說:“瘐信生多感,楊朱死有情;弦危中婦瑟,甲冷想夫箏!”則箏瑟為曲,常系乎生死哀怨之深情苦意,可想而知。循此以求,如謂錦瑟之詩中有生離死別之恨,恐怕也不能說是全出臆斷。
《錦瑟》中,詩人大量借用莊生夢(mèng)蝶,杜鵑啼血,滄海珠淚、良田生煙等典故,采用比興手法,運(yùn)用聯(lián)想與想象,把聽覺的感受,轉(zhuǎn)化為視覺形象,以片段意象的組合,創(chuàng)造朦朧的境界,從而借助可視可感的詩歌形象來傳達(dá)其真摯濃烈而又幽約深曲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