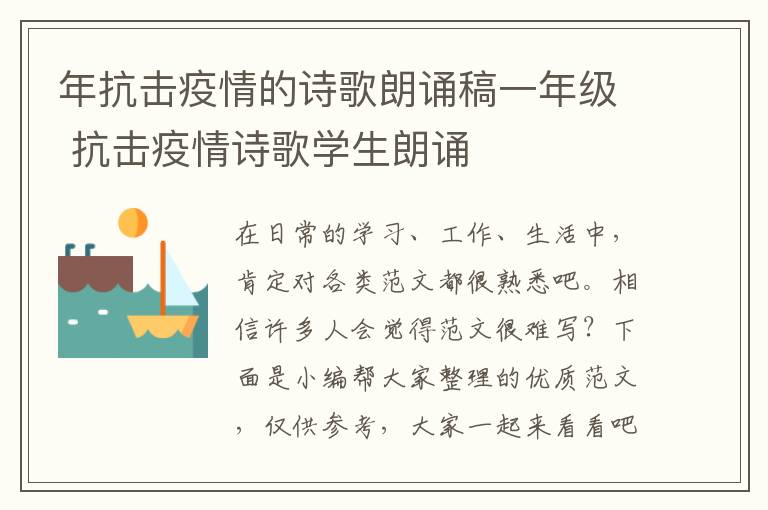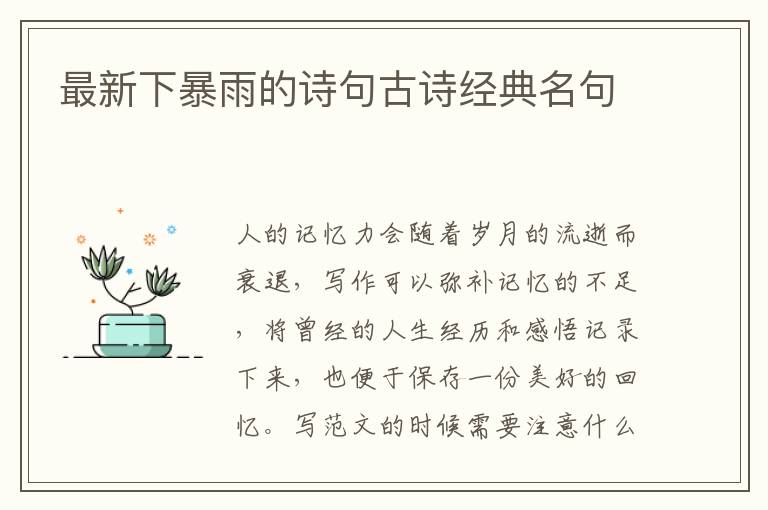我們窮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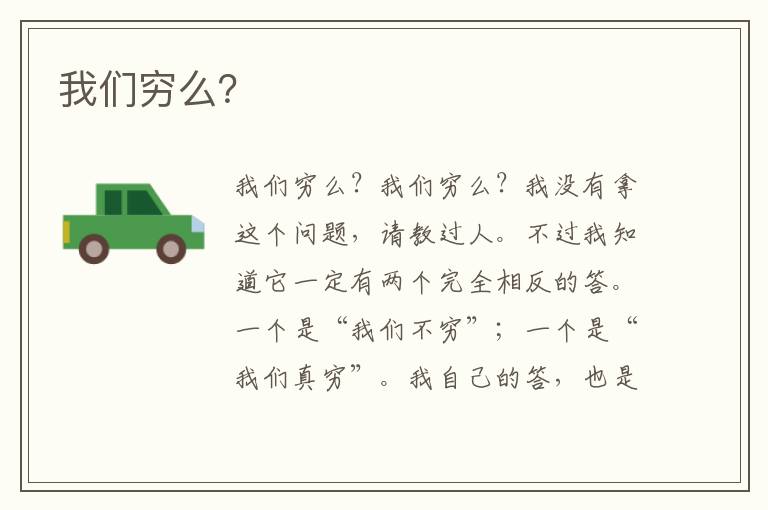
我們窮么?
我們窮么?
我沒(méi)有拿這個(gè)問(wèn)題,請(qǐng)教過(guò)人。不過(guò)我知道它一定有兩個(gè)完全相反的答。一個(gè)是“我們不窮”;一個(gè)是“我們真窮”。我自己的答,也是這樣,也是兩個(gè)—— 一個(gè)是窮,一個(gè)不窮。我作答的理由,恐怕與別人的有些不同。請(qǐng)閱下文:
窮有兩種:(一)身窮,(二)心窮。
何為身窮?沒(méi)有衣穿,沒(méi)有飯吃,沒(méi)有屋住,沒(méi)有車(chē)坐——這都是身窮。沒(méi)有紙來(lái)印報(bào),沒(méi)有電來(lái)開(kāi)機(jī)——這也是身窮。
何為心窮?沒(méi)有禮貌,沒(méi)有道德,沒(méi)有科學(xué),沒(méi)有智識(shí)——這都是心窮。沒(méi)有能力自習(xí),沒(méi)有方法教人——這也是心窮。
身窮易治,心窮難療。
我們?nèi)珖?guó)的人,心窮者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身窮者至多百分之二十。
我先言我國(guó)的——尤其是上海的——心窮者:
他們天天喊窮,天天說(shuō)沒(méi)有飯吃。然而到了中午,到了夜晚,哪一個(gè)酒館不客滿?他們說(shuō)“賺的鈔票不夠化”;但是他們穿的是筆挺的西裝,坐的是自備的三輪,看的是最新的影片。并且他們今日頂進(jìn)一所單幢——八十萬(wàn),明天頂進(jìn)一所洋房——一百三十萬(wàn);今天買(mǎi)黃金——五條,十條,明天買(mǎi)股票——千股,萬(wàn)股。倘然有了鈔票,就成富翁,倘然鈔票是富,富是鈔票,那末,他們還算得窮么?
他們已經(jīng)富了,他們?nèi)耘f口口聲聲地說(shuō)窮,他們真的全無(wú)智識(shí)——真的心窮。
繼言我國(guó)的身窮者:
我國(guó)的身窮者,約占人口中百分之二十——上文已經(jīng)提過(guò)。這種身窮者,有了衣穿,沒(méi)有飯吃,有了飯吃,沒(méi)有屋住。他們大概怠惰,貪懶。他們不喜歡作工而欲得衣食,漸漸成為兩手空空的人。多數(shù)乞丐,是這種人。我說(shuō)“多數(shù)乞丐”,因?yàn)樯虾A碛小吧贁?shù)”乞丐,也不真窮,并不缺乏衣食住行。上海少數(shù)的乞丐,固然在馬路上喊痛苦,告地狀。我們看見(jiàn)他們真窮,然而他們并非真窮。他們以求乞?yàn)槁殬I(yè),以叫喊為廣告,以馬路為辦公室。等到鈔票收夠了,居然有“家”可歸,有飯可吃。據(jù)說(shuō)上海覓一個(gè)乞丐頭腦,每月所入,除開(kāi)支外,在五萬(wàn)元以上。我們?cè)隈R路上所見(jiàn)的那些穿破衣而哀哭的男女小孩,大半是他的“討人”。他本人有妻有妾,覓廚司,覓奶娘。不知他是乞丐頭腦者,一定以為他是闊得很的商人,乞丐頭腦這樣闊,當(dāng)然算不真窮。他的“討人”,作“工”度日,為主人出力,受主人保護(hù),也算不得真窮。
真窮——我們從前以為真窮的人,是那些苦力——拉車(chē),拖車(chē),搬貨,掮貨的苦力。他們的腳總是赤的,他們的衣總是破的。他們現(xiàn)在的衣仍舊是破的,他們現(xiàn)在的腳仍舊是赤的,但是情形大大的改變了。現(xiàn)在的他們,每日所入,至少六百元。三人合拉一輛榻車(chē),送貨一次,價(jià)一千二百元。除三分之一歸車(chē)主外,可凈得八百元。試問(wèn):每日可送貨若干次?三輪車(chē)夫每日所入,想必不小。他們每日到處可得多少——我還沒(méi)有找到可靠的統(tǒng)計(jì)。據(jù)別人說(shuō),小舞場(chǎng)中常常有理發(fā)師及三輪車(chē)夫的足跡。那末白天愿意勞力的人,已經(jīng)身不窮了。作工時(shí)雖然赤腳,雖然穿的是破衣舊褲,但“公”畢之后,娛樂(lè)之時(shí),何嘗不可西裝革履?何嘗不可與大少爺,小官吏“并駕齊驅(qū)”?
所以上海很少真正身窮的人。依照上海的人口計(jì)算,真窮的人決不到一百萬(wàn)。心窮的人,恐怕不止四百萬(wàn)。你看!在這種緊急的時(shí)候,他們(我們?)還要宴飲,還要看戲,……我們連軋電車(chē)的排班都不整齊;何必多提制造飛機(jī),制造大炮呢?我們自己沒(méi)有智;為什么還要罵他人欺侮我們?
原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文友》第三卷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