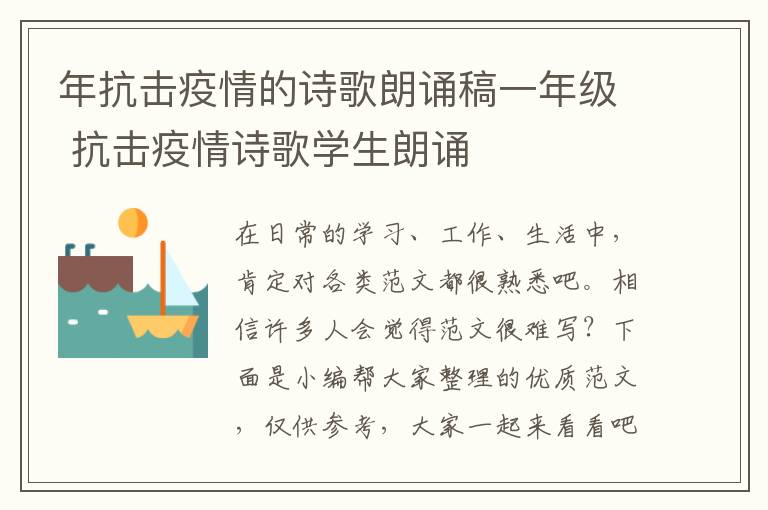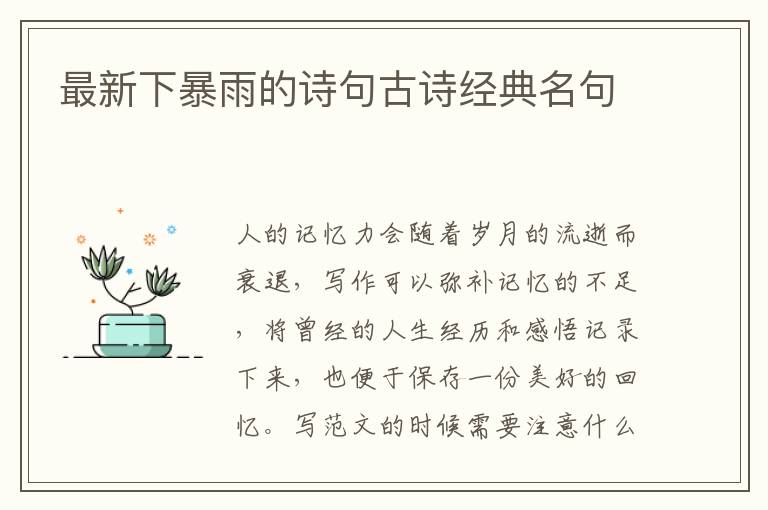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怪物》鑒賞

作者: 張俊山
石民
在我的靈魂的洞窟里,伏著一個(gè)怪物。
他出來(lái)作祟了:捉住了我的心,簸弄著,揶揄著,而且甚至于污蔑著……
“什么鬼!”如果我警醒地抬起頭來(lái),睜眼一喝——不見(jiàn)了,他躲避得這樣地急速。
幾多次,幾多次他那樣地?cái)_害了我,而且?guī)锥啻危瑤锥啻挝夷菢拥赝樍怂峭魅?我并不能將他鎮(zhèn)住。
有時(shí)他突然地跳了出來(lái),猴一般地鹵莽;有時(shí)他偷偷地爬了出來(lái),狐一般地狡獪——教我何從防備起?
于是我只好向他哀訴,懇求他離開(kāi)——永遠(yuǎn)地離開(kāi)了我,“可憐,可憐罷,我的心給你糟蹋了!”
顯然地,他并不曾理會(huì)。
我憤恨極了,決定嚴(yán)厲地對(duì)付他。一瞥見(jiàn),便盡力向他一擊——噯!這痛苦卻落在我自己的靈魂上。
“奈我何!”隱隱地聽(tīng)到他的嘲笑。
人作為會(huì)思想、有智慧的高級(jí)靈長(zhǎng)類,有時(shí)會(huì)比其它動(dòng)物活得更加痛苦。客觀世界的傾洞風(fēng)沙,微飔細(xì)瀾,都會(huì)在相關(guān)人們的內(nèi)心激起情感反應(yīng),于是人才有喜怒哀樂(lè)種種心態(tài)。而在許多情況下,人會(huì)陷入莫名的煩惱,無(wú)以自慰,無(wú)可排解,猶如怨鬼糾纏著靈魂,使你痛不欲生。這就是人從野蠻進(jìn)化到文明之后遭遇的生存困境。所以,從生存狀態(tài)說(shuō),在人類的進(jìn)化鏈上永遠(yuǎn)伴隨著一種悖論現(xiàn)象。
石民的《怪物》展示的就是個(gè)體的具有普遍性的心態(tài)。每個(gè)人內(nèi)心煩憂的因由也許千差萬(wàn)別,各不相同,但是那種莫可奈何、苦苦掙扎而又難以解脫的情感體驗(yàn),卻是相似乃爾,如出同轍。“怪物”是一種心理的比擬實(shí)體,它或許就是潛意識(shí)的幻化。所以當(dāng)它“出來(lái)作祟”的時(shí)候,它“捉住”你的心,“簸弄著,揶揄著,而且甚至于污蔑著……”,你無(wú)論怎樣也制服不了它。最終的結(jié)果是:
“奈我何!”隱隱地聽(tīng)到他的嘲笑。
詩(shī)人以現(xiàn)身說(shuō)法,用委宛曲折的描述充分揭示了人類特有的這種心理的生存狀態(tài),應(yīng)當(dāng)說(shuō)達(dá)到了相當(dāng)?shù)牡湫托浴?/p>
現(xiàn)代派文學(xué)有表現(xiàn)人的“內(nèi)宇宙”一種傾向。法國(guó)象征派詩(shī)人波特萊爾的《巴黎的憂郁》,抒寫的就是詩(shī)人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huì)重壓下感受到的種種痛苦和煩惱。其中第六篇《每個(gè)人的怪獸》就是表現(xiàn)詩(shī)人特有的內(nèi)心世界的。石民曾經(jīng)評(píng)介過(guò)這篇作品,他創(chuàng)作《怪物》乃是受了波氏作品的影響,當(dāng)是無(wú)疑的。但是,這一點(diǎn)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石民自己的生活依據(jù)。顯然,生活在二十世紀(jì)初期舊中國(guó)黑暗現(xiàn)實(shí)的詩(shī)人有他自己關(guān)于社會(huì)的、家庭的、乃至個(gè)人命運(yùn)的感受和體驗(yàn),因此,當(dāng)他捕捉到個(gè)人“內(nèi)宇宙”的一方風(fēng)景,并將之表現(xiàn)于筆端的時(shí)候,也就獲得了時(shí)代的色彩。作品發(fā)表于1925年的《莽原》周刊第九期,那么,它表現(xiàn)的不正是那個(gè)“風(fēng)雨如盤”年代里一大批彷徨無(wú)路的知識(shí)分子共同的心態(tài)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