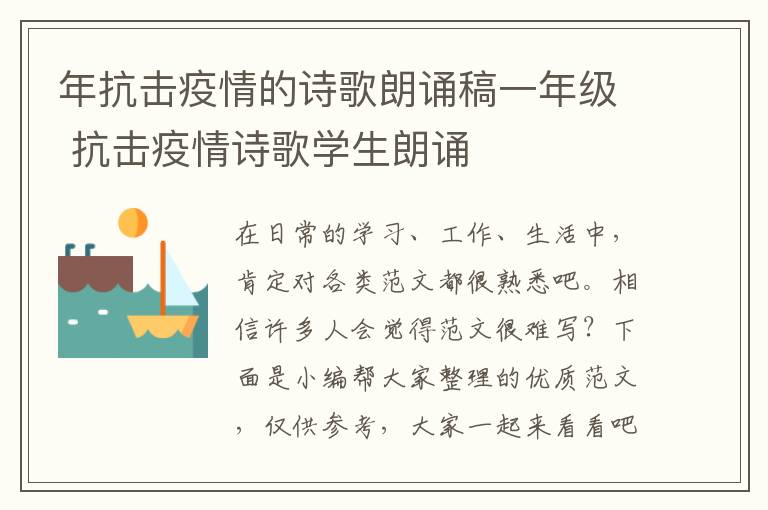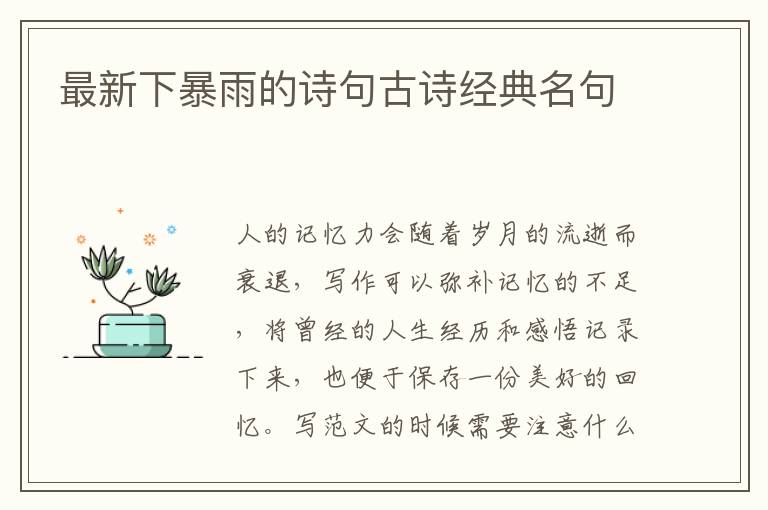王國(guó)維《人間詞話·水光云影遠(yuǎn)》經(jīng)典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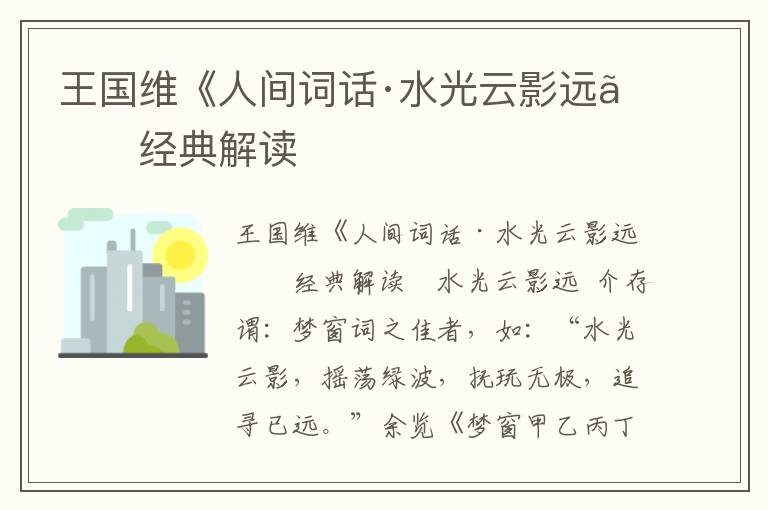
王國(guó)維《人間詞話·水光云影遠(yuǎn)》經(jīng)典解讀
水光云影遠(yuǎn)
介存謂:夢(mèng)窗詞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搖蕩綠波,撫玩無(wú)極,追尋已遠(yuǎn)。”余覽《夢(mèng)窗甲乙丙丁稿》中,實(shí)無(wú)足當(dāng)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fēng)菰葉生愁怨”二語(yǔ)乎?
踏莎行
吳文英
潤(rùn)玉籠綃,檀櫻倚扇。繡圈猶帶脂香淺。榴心空疊舞裙紅,艾枝應(yīng)壓愁鬟亂。
午夢(mèng)千山,窗陰一箭。香瘢新褪紅絲腕。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fēng)菰葉生愁怨。
“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fēng)菰葉生愁怨。”此句愁情幾許,都散卻風(fēng)雨之中。
風(fēng)雨之中,愁情難寄。
渾然的清麗,正所謂柔美的只能感受,伸手一觸摸便隨風(fēng)而散。
這恐怕是吳文英最清秀的句子了。
周濟(jì)說(shuō)吳文英的詞如:“水光云影,搖蕩綠波,撫玩無(wú)極,追尋已遠(yuǎn)。”指的是吳文英的詞水光云影共徘徊,若綠波之搖蕩,撫玩不足以啟遠(yuǎn),追求難達(dá)于雋永。
王國(guó)維同意他的觀點(diǎn),但是只針對(duì)一句“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fēng)菰葉生愁怨”表達(dá)同意的態(tài)度。
這句寫景寫情,情景交融,情感真摯自然,正符合王國(guó)維的不隔之說(shuō)。
而吳文英之詞,整體來(lái)看似乎走不出南宋詞在遣詞造句上的局限,太過(guò)于修飾以及想尋找新奇之感,依舊在境界上難有突破。
而在詞中,王國(guó)維看重的是詞的品行,外在的修飾再華麗,也不過(guò)是個(gè)繡花枕頭。
遣詞造句向來(lái)是詞人的本事,如果在句子里沒(méi)有埋下高雅的靈魂,那無(wú)疑是在用文字的華美來(lái)欺瞞讀者。
吳文英寫詞之時(shí)信誓旦旦,立求自成一家,可是由于自身?xiàng)l件不足,論胸襟比不上辛棄疾,才情天賦比不上姜夔,他的詞往往在藝術(shù)技巧上追求新奇。
他喜搭配文字,寫池水用“膩漲紅波”,寫云彩是“倩霞艷棉”,寫花容“腴紅鮮麗”。
初讀之,覺(jué)得有些新意之感,可是再讀之,便覺(jué)得裝得厲害,好像女人的妝化得太濃,臉上盡是脂粉,漂亮卻是不真實(shí)的空,看起來(lái)虛無(wú)得厲害,這樣的假只會(huì)叫人望而生畏,不敢對(duì)她生情。
他喜好寫幻覺(jué),他的詞總是似幻似真。
比如:“黃蜂頻撲秋千索,有當(dāng)時(shí)、纖手香凝。”(《風(fēng)入松》)黃蜂撲秋千,是眼前之景,已亡之美人的纖纖細(xì)手曾經(jīng)在這秋千上留下過(guò)香氣。黃蜂撲秋千的原因恰似撲尋曾經(jīng)美人之香。這里真實(shí)和虛幻結(jié)合,化虛幻為真實(shí)。
比如:“渺空煙四遠(yuǎn),是何年、青天墜長(zhǎng)星。”(《八聲甘州·陪庾幕諸公游靈巖》)
這里是化真實(shí)為虛幻,將靈巖山比作是從青天隕落的長(zhǎng)星。
他的詞多用此手法,一首詞似乎過(guò)多地強(qiáng)調(diào)了修辭,依舊是缺少性情之感,多閱之,頗有文人賣弄文采之感。
張炎在《詞源》中就批評(píng)他的詞:“如七寶樓臺(tái),炫人眼目,拆碎下來(lái),不成片段。”
張炎指責(zé)吳文英的詞缺乏邏輯性和連貫性,在文辭上卻有描繪過(guò)甚、堆砌晦澀、故作新奇之弊。
猶似用盛裝來(lái)掩蓋天生的缺陷。
盛裝若是卸下,缺陷便暴露無(wú)遺。
無(wú)境界之詞,如無(wú)情之人。
思佳客·賦半面女骷髏
吳文英
釵燕攏云睡起時(shí),隔墻折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妝如畫,細(xì)雨三更花又飛。
輕愛(ài)別,舊相知。斷腸青冢幾斜暉。斷紅一任風(fēng)吹起,結(jié)習(xí)空時(shí)不點(diǎn)衣。
詞中依舊是以幻為真的手法,將一具恐怖女骷髏寫成妙齡綽約之少女。
盡管詞中文字華麗漂亮,它沒(méi)有蒲松齡作品里鬼妖與人談情說(shuō)愛(ài)的浪漫,除了此人對(duì)著一具骷髏盡情地遐想之外,也再無(wú)其他東西,想想也就是想想罷了。
這具盛裝之女骷髏,用來(lái)形容吳文英之詞風(fēng)或許也是極其恰當(dāng)?shù)摹?/p>
外表再美麗,不過(guò)是裝點(diǎn)而已,內(nèi)里干枯,已無(wú)動(dòng)人之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