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代的揚雄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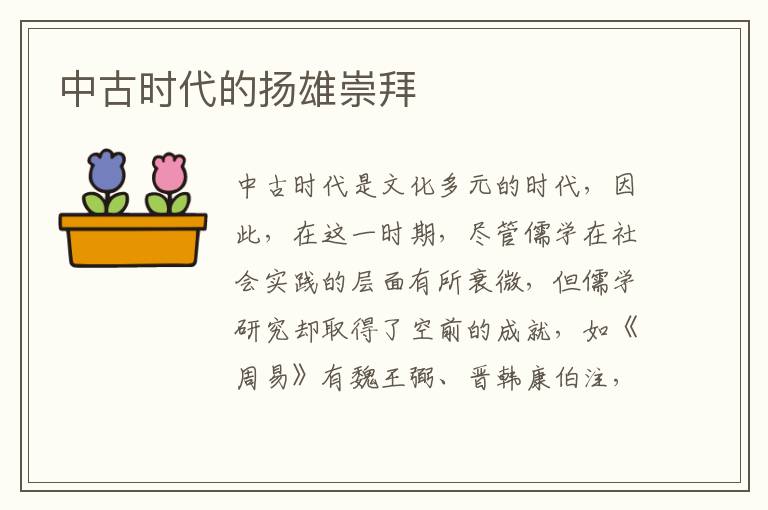
中古時代是文化多元的時代,因此,在這一時期,盡管儒學在社會實踐的層面有所衰微,但儒學研究卻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周易》有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左傳》有晉杜預集解,《春秋谷梁傳》有晉范寧集解,《爾雅》有晉郭璞注,《論語》有魏何晏集解等,這些著作上承兩漢,下開唐宋,幾乎占據了《十三經注疏》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見中古儒學的成就是很高的。人們通常尊奉的中古儒學式微的通行觀點,實際是將儒學的社會實踐與儒學自身混為一談了。文化之多元來自文化信仰之多元。中古的士林精英,能夠以純理性純文化純學術的眼光和襟懷來審視和接受真正的偉人及其思想,這是其最為卓絕不俗之處。
除了孔、孟、老、莊,揚雄在中古時代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中古士人崇拜的文化巨人之一——被視為誕生在漢代的新圣,具有極高的文化地位。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二十四“齊楚圣人”條引桓譚《新論》:
張子侯曰:“揚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云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圣人也。”
張子侯與桓譚的對話表明,在東漢時代,他已經被視為和孔子一樣的光耀華夏的圣人。漢王充《論衡·超奇篇》:
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云作《太玄經》,造于助思,極窅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圣之才者也。王公子問于桓君山以揚子云,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諸子集成》,第七冊,王充《論衡》,上海書店1986年版)
所謂“蹈孔子之跡”,“參貳圣之才”也是說揚雄乃是孔子以外的圣人,而桓譚則認為揚雄是獨步于漢代的文化巨人。再如葛洪《抱樸子外篇》卷三《吳失》第三十四:
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楊明照《抱樸子外篇校箋》,下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三稱“揚子云齊圣廣淵”,卷十上稱“子云玄達,煥乎宏圣”,都是同樣的意思。這些評價都是一致的。這里我們再以嵇康和陶淵明為例,進一步說明當時人們對揚雄的推尊。《世說新語·簡傲》第3條:
鐘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鐘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鐘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下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
嵇康和鐘會問答之語中的著名的“所字結構”本于《法言·淵騫》:
七十子之于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汪榮寶《法言義疏》,下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
在中古時期,揚雄的《法言》是馳譽學林的名著,所以嵇、鐘二名士隨口便可稱引。《法言·問神》:“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李軌注:“童烏,子云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云傷育童烏而不苗。”“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子云論《玄》。”(汪榮寶《法言義疏》,上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童烏是中古時代著名的神童,他九歲就能和父親揚雄討論《太玄》的問題。這位神童引起了魏晉名士的廣泛關注。嵇康《秋胡行》:“顏回短折,下及童烏。”(戴明揚《嵇康集校注》,上冊,中華書局2014年版)嵇康對童烏的了解正來自《法言》,這可以為筆者關于“所字結構”淵源于《法言》的推測作一旁證。
陶淵明由晉入宋以后,更名為陶潛,前人對此多有解說(參見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之問題》,《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這實際也是受揚雄《法言》影響的結果。《法言·問神》: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于人乎?況于事倫乎?”“敢問潛心于圣。”曰:“昔乎,仲尼潛心于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于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汪榮寶《法言義疏》,上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
“神在所潛”就是陶潛之名的寓意。陶淵明不僅熟讀《法言》,對《太玄》也極為諳熟。《連雨獨飲》詩:“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天豈”句,古直注引揚雄《太玄·玄摛》:“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于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古直《陶靖節先生詩注》卷二,臺灣廣文書局1964年版)可見這四句陶詩不過是《太玄》此文的翻版而已。至于《飲酒》二十首其十八直接歌詠“子云性嗜酒”,更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嵇康和陶潛對揚雄的推崇并非特例,揚雄作為魏晉玄學的祖師爺,其影響對中古士人是深入骨髓的。我們只有通過文本細讀才能發現這種文化崇拜的痕跡。
作為漢代之新圣,揚雄的突出特征在于“尚智”,這是中古士林崇拜揚雄的首要原因。《法言·問明》: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
所謂“智”,就是智慧,就是知識。在揚雄看來,追求知識和智慧是人的本質特征。知識就是美,智慧就是力量。他把“智”放在了高于儒家道德、仁義和禮儀的位置上,這是對傳統儒學的重要突破。而揚雄一生的文化實踐始終貫穿著“尚智”的理念,充分體現了柏拉圖所說的那種“愛智的熱情”,他是一個“為知識而知識”的人。《漢書·揚雄傳》:
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括于勢利乃知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倉頡》,作《訓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于內,不求于外,于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班固《漢書》,第11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
所謂“括于勢利”“好古樂道”,“用心于內,不求于外”就是《文心雕龍·體性》所說的“子云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對此,我們可以引用德國哲學家亞斯貝爾斯的話加以解釋:“本真的科學研究工作是一種貴族的事業,只有極少數人甘愿寂寞地選擇了它。原初的求知欲是對人生而俱來的挑戰,但僅僅依憑這種求知欲就不可能有科學的風險。……有史以來研究工作就不屬于普通人所能從事的工作。一個運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人,只有當他把追求真理當做一種內在需要時,才算是真正參與學術研究。”(《什么是教育》,鄒進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對揚雄而言,“追求真理”是他一生最本真的“內在需要”。這與其純潔的心靈和靜穆的性格是相一致的。這是中古士人崇拜揚雄的第二個原因。揚雄的這種品格使他創造了不朽的學術輝煌。出于“愛智”的熱情,他曾經對屈原的自殺深表惋惜。確實,如果屈原不自殺的話,以其《離騷》和《天問》所體現出來的科學文化修養從事于科學文化研究,也許就會成為我國先秦時代的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而揚雄的清醒和冷靜就在于,他珍惜自己的生命,為了從事學術研究必須留在宮廷之內,以獲得和保持探求真理的必備條件,所以他不惜與王莽之流以及世間的俗人虛與委蛇,隱忍不發,畢生的勤奮與執著,使他成為我國中古時代的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其思想之深湛,涉獵之廣博,精神之崇高,建樹之卓越,求諸我國近兩千年學術文化史,殆罕其匹。揚雄一生,默然自守,辛勤耕耘,在文學、哲學、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天文學、地志學、譜牒學、諸子學和歷史學等諸多領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譬如,其所著《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一書,為現代方言學與方言地理學開疆奠基,導夫先路,領先西方學術界一千多年,至近三百年成為我國學界之顯學。其孤光獨照與孤明先發,千載以下,仍然令人震撼。其所著《太玄》,更是曠世的奇書:“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太玄·玄摛》)(司馬光《太玄集注》,劉韶軍點校,中華書局1998年版)張衡“常耽好玄經”,曾經對崔瑗說:“吾觀太玄,方知子云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后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傳》)魏晉時代玄學的興起和昌盛,證明了張衡的預言。而以司馬光之博學,其于《太玄》也未能完全懂,故其文化密碼尚有待于人們去研究去破解。在文學方面,揚雄是“漢賦四大家”之一。《昭明文選》收錄了他的《甘泉賦并序》、《羽獵賦并序》、《長楊賦并序》、《解嘲并序》、《趙充國頌》和《劇秦美新》等六篇作品,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揚雄也給予極高的評價。杰出的學術成就和卓越的文化建樹是中古士人崇拜揚雄的第三個原因。
揚雄生前是寂寞的,也是缺少知音的。《漢書·揚雄傳》:
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巨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
在《文心雕龍·程器》中,劉勰列舉“文士之疵”,稱“揚雄嗜酒而少算”,意思是說揚雄愛酒而不善于為自己謀劃,是其一病;而與揚雄同時代的著名學者劉歆在看了《太玄》《法言》之后,說揚雄是徒勞無益,因為當時的學者大都以追逐“祿利”為第一要務,連《周易》都看不懂,更別說《太玄》了,所以擔心后人會用這部名著去遮蓋醬甕。當時,對揚雄所知最深的是桓譚。在揚雄去世不久。桓譚對王邑和嚴尤說:“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后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云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后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圣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桓譚預言揚雄在未來可能會“度越諸子”(《漢書·揚雄傳》),即超越春秋時代的諸子百家。而西晉太康時期的著名詩人左思在《詠史》八首其四中對揚雄生前的生活和身后的輝煌進行了精彩的描寫: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區。(《文選》卷二十一)
“濟濟”八句寫新莽之際趨炎附勢的世態和浮華的人心,“寂寂”六句寫揚雄甘于寂寞,著述不輟,詩人運用對比的手法,突出了揚雄的高尚品格和人生追求,而以“悠悠”二句作結,將揚雄推上不朽的文化巔峰。也就是說,在新莽時代虛矯殘酷的專制主義社會和人性的荒原中,在舉國趨利、終日馳騖的世俗氛圍中,在以讀書做官為普遍追求的價值體系中,在“為官之拓落”,“位不過侍郎”,“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漢書·揚雄傳》)的譏諷和嘲笑聲中,揚雄以其寄情來世的遠見卓識和清凈自守的文化品格超越了自己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但是,作為一位文化巨人,他的現實感和歷史感都是很強的。在《解嘲》中,揚雄曾經激情澎湃地宣稱:
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班固:《漢書》,第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
這是一代文化巨人的道德宣言和歷史預言!揚雄對歷史的預見和預判,完全被歷史本身證實了。那些手握權柄、好人佞己、妄自尊大的王莽之流,早已在歷史的秋風中煙消云散了,而揚子所創造的文化輝煌卻永遠垂范于后世,為華夏文明和人類文化增光添彩。一切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應當秉持揚雄式的道德操守和文化品格。
揚雄的人格和思想以及文化建樹,為中古士人彰顯了一條無限寬廣的文化道路,也指引了一條趨向永恒、垂聲后世的人生道路。在揚雄辭世2000年的今日,揚雄對我們來說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