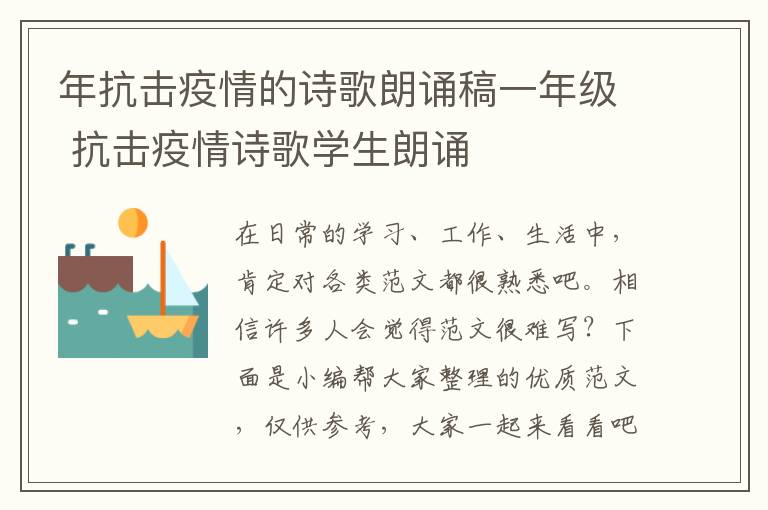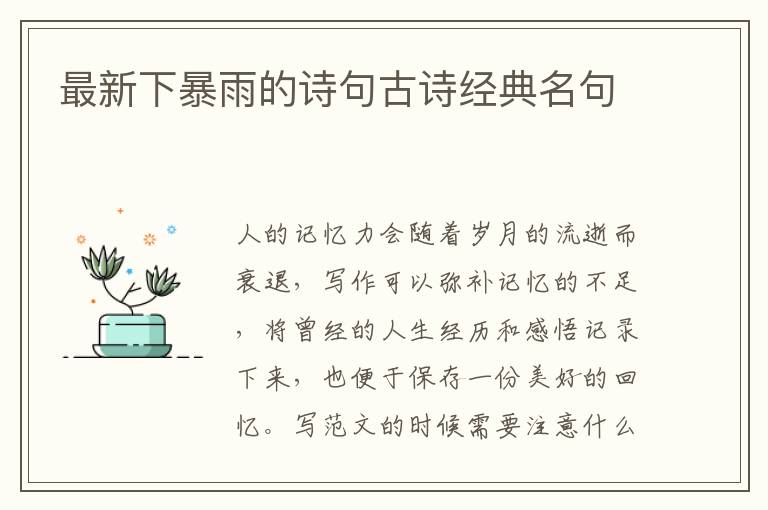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青山依舊,幾度夕陽”——讀《華爾街變革》一書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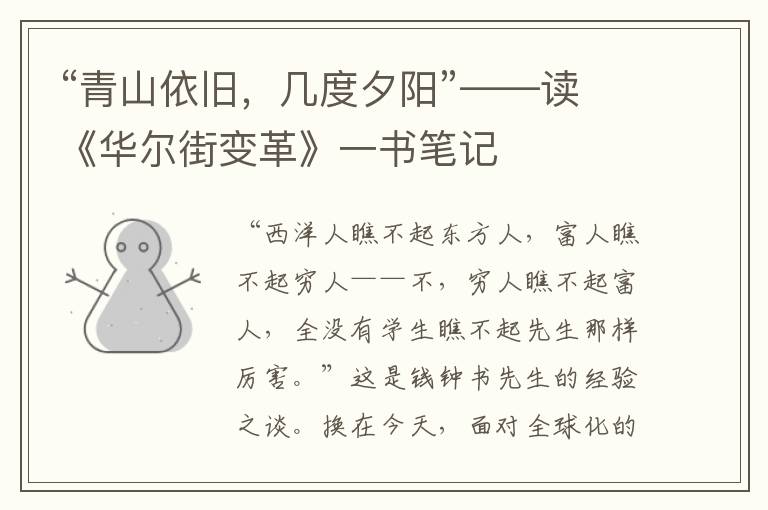
“西洋人瞧不起東方人,富人瞧不起窮人——不,窮人瞧不起富人,全沒有學生瞧不起先生那樣厲害。”這是錢鐘書先生的經驗之談。換在今天,面對全球化的滔天巨浪,錢先生或許還會加上“看不起美國人”。確實,美國經常在法治和證券業方面以師長自居,有唯我獨尊的意思。這就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感——尤其是激起了要去美國留學或是要送子女去美國留學的人的強烈反感。不過,“親者知其善,仇者知其惡”——美國人在法治方面也有經驗之談。利用歷史講法律便是一例。
《華爾街變革》英文原版封面
利用歷史講法律:這是美國人的一大發明
美國的歷史是太短,短到大學者都不好意思寫美國通史。美國人會說,他們是古羅馬的傳人,其法治是羅馬共和國傳統的繼續和光大。但傳統是傳統,傳統有別于歷史。
美國歷史短,所以分門別類地講歷史。美國是金融帝國,其歷史也是金融發家史。美國還是一個帝國。看一看美國—西班牙戰爭后的美國軍事史,便能了解美國的歷史要點。但美國更是一個法治國家,其歷史就是一部法律史,每個判例都是一個故事。看了這些判例,對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來龍去脈就可大致有所了解。斯坦福大學的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教授所著《美國法律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就是融法律與歷史為一體的一本好書。弗里德曼教授做了件好事,把法律從法學家的課堂中解放出來。
喬爾·斯里格曼(Joel Sligman)教授所著《華爾街變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Wall Street)也是以史講法。該書的副標題就是“證券交易委員會歷史與現代公司融資”(A History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d Modern Corporate Finance)。書與書的副標題一樣長,連注解索引在內有700多頁。斯里格曼教授羅列的內容很多,當然是“大學者的放任”,而沒有小匠人的“瑣碎”。斯里格曼教授的文筆遠不如弗里德曼教授的機智、流暢,美國學法律的人看起來也比較吃力。當然,證券法本身比較枯燥、煩瑣,遠沒有刑法或憲法那樣激動人心。
《華爾街變革》沒有中文譯本。據說幾年前國內有人要譯,無奈書太厚,專業性太強,所以至今還沒有譯出來。《華爾街變革》最新版是1995年的,在美國也幾乎脫銷。估計當時印數就不多,需求也不會很大。法律書不同于暢銷小說,據說能賣一萬冊便是暢銷書。法律書還有個麻煩,就是再版必須修訂。修訂不容易,時間拖得很長。
國內對新書較感興趣,書出了幾年,問津的人便銳減。其實經典不怕舊,尤其是法律和文字方面的經典不怕舊。比如,《布萊克法律辭典》(Black Law Dictionary)國內的最新版是1991年的,《牛津當代英語袖珍詞典》(The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的最新版是1984年的,但兩本書仍然是經典,仍然很實用。法律和文字會出現若干新名詞,但根本性的內容不會輕易改變。《華爾街變革》也是一部經典,是對美國證券交易會(以下簡稱證交會)的家史全面披露。
“話語是法官的墓志銘”
斯里格曼教授以證交會的各屆主席作為主線,追蹤記述了證交會各個時期的工作任務和經驗教訓。在斯里格曼教授眼里,證交會主席中的英雄首推道格拉斯。
1.“一個當局的結束”
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于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曾在哥大和耶魯法學院執教。道格拉斯當過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證交會的成績反而不見凸顯,而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也確實要比證交會主席更讓人敬畏。但斯里格曼教授認為,道格拉斯在位時,也正是證交會的鼎盛時期,因為“證交會此后再也沒有得到白宮、國會和公眾如此強有力的支持。證交會將以技術能力著名,而沒有什么推動立法的作用”。
道格拉斯本人對自己也充分肯定,成績講透,問題不提。書中引用了道格拉斯本人的一段話:“證交會舉行告別聚會,工作人員都到了。大家都很難過,往日的當局已成過去,新的當局就要開始。我們從此各奔東西,但友情天長地久。”“當局”(regime)一詞在英文中與“行政當局”(administration)和“政府”(regime)是同義詞,也有“規矩”(order)和“制度”(system)的意思。可見道格拉斯的口氣之大。還好,道格拉斯沒有說一個“時代”(age)要結束了。
道格拉斯有什么功績呢?讓我們先看看他是如何贊揚兩位前任主席的。他說:
借助羅斯福總統的立法方案,在保護投資者方面取得了成績。在喬·肯尼迪的領導下,這些進展得到了加強。在杰·蘭德斯的領導下,我們學會了如何奮斗。為了實現我們的目的,讓我們奮斗吧。
道格拉斯很會說話,寥寥數語便勾勒出兩位前任主席的豐功偉績。而且言外之意是,在他領導下證交會要真干了,頗有“當今欲治天下舍我其誰”的口氣。而書中有關道格拉斯的那章就叫“辦成實事的人”。在道格拉斯的大力推動之下,國會修正了《證券法》,設立了證券經紀人和營銷商自己的組織“美國證券營銷商協會”,由其直接監管場外交易。道格拉斯還重新為紐約股票交易所定位,促其建立自我監管機制。加強協會和交易所的作用是道格拉斯的主要功績。推動公司治理是道格拉斯的又一重大貢獻。
2.話語是法官的墓志銘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北島的詩句淚盡啼血,夜半悲歌。而法官的話語就是自己的墓志銘,法官借話語天風海雨,呼喚良知。道格拉斯就是這樣一位法官。斯里格曼教授大段引用道格拉斯的原話。為大師樹碑立傳很難,作者自己相形見絀事小,就怕曲解了大師或先哲的恩怨。所以,大量引用原文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讓我們看道格拉斯的指導思想,因為從來都是指導思想最重要,“先有革命的思想,才會有革命的行動”。在道格拉斯看來,證交會應該是“‘投資者的代言人’。經紀人有自己的代言人;交易所有自己的代言人;投資銀行家有自己的代言人;我們就是投資者的代言人”。這里的“我們”指“證交會”。道格拉斯要保護廣大股民,同時也同情小公司。在他看來,小公司是“這個國家發展的中堅”。
證交會前任主席中,萊維特也一再鼓吹保護中、小股民,經常被人當作一面大旗揮舞。讀了《華爾街變革》,我才知道萊維特并非始終俑者,有道格拉斯在先,而且道格拉斯更加雄辯,更加大聲疾呼,更加高歌猛進,“溫故而知新”這句話千真萬確。
道格拉斯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很下功夫。道格拉斯認為,董事應該是“專家型的……但與公司業務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便他們能夠結合公司競爭對手、貿易發展趨勢等情況來看待公司”。“他們在董事會應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不是仰人鼻息的改革者”。道格拉斯意中的獨立董事多像今天的獨立董事啊!
確實,自道格拉斯以來,公司獨立董事的基本指導思想似乎沒有根本性的躍進。事實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末,道格拉斯便想推出一部《聯邦公司治理法》,但終因各方阻力太大作罷,是“辦成實事的人”的一大缺憾。好在他的未竟事業已由法官通過判例完成。公司治理這面旗幟也在全球高高飄揚。(但不能說永遠飄揚,那樣就不是辯證唯物主義了)
應該承認,道格拉斯并不是好大喜功,為通過法律而通過法律。感謝斯里格曼教授,他又為我們引用了道格拉斯的語錄:
法律本身并不是首要問題,首先應該將金融置于社會控制之下,有一個社會控制的全面方案。凡事要公開,控制資本機構,控制董事,監管投機,監管控股公司,保護小股東,這些才是首要的。
還有:
在聯邦一級管理公司不僅僅是起草一部法律,不僅僅是確定就越權行為、股息、董事責任等問題要制定哪些規則。這些并不是頭等大事。要害問題是確定相關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我們想要什么;我們想要摧毀什么?我們想要什么樣的控股公司?今天的小人物可能是明天的亨利·福特,也可能是街角雜貨鋪的小老板。
事隔50多年的今天,證交會委員亨特(相當于副主席)針對安然事件指出:
沒有任何監管體系可以替代恰當的價值體系。我們尤其需要研究價值體系如何導致我們所看到的種種問題,以及監管者應該如何改進市場和價值體系,確保公司管理層和所有市場參與者作出準確的信息披露。
不知道亨特先生有沒有看過道格拉斯的文章。但兩人的觀點如出一轍,都是誅心之論,簡單說就是“求仁得仁,求智得智”。如果再往前推一步,就要對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制度提出根本的疑問了。所以,兩人也都是點到為止。
3.道格拉斯的傳人
“相逢開口笑,過后無事樣。人一走,茶就涼。”人走政亡在美國很常見,但道格拉斯是個例外,他至少有兩位門生故舊繼任了證交會主席的職能,繼續推行他的方針政策。
繼道格拉斯之后的證交會主席是杰羅姆·弗蘭克(Jerom Frank)。他是位猶太人,公司業務律師,芝加哥法學院畢業,在律師事務所干了15年。但弗蘭克很有人文氣息,自己雖然生活過得不錯,但對窮人和無權無勢的人有深厚的關懷。弗蘭克飽讀詩書,道格拉斯稱其是在“圖書館內遨游世界”。真是很難得,因為律師經常為富不仁,充當權貴的幫兇。
與道格拉斯相比,弗蘭克更是位戰術家,其主要成績是按《公共設施控股公司法》執法,指揮部下打了30多個官司。《公共設施控股公司法》的要害是反壟斷,弗蘭克捍衛了這一目標。弗蘭克干了兩年主席后去當了法官。
威廉·卡爾里(William Cary)主席是斯里格曼教授最佩服的一位。將其視為證交會的中興之臣,寫他的一章就叫“卡爾里領導下的復興”。斯里格曼教授還將卡爾里的話用作卷首語——統領全書。卷首語比較重要,反映出作者的主題思想。例如,《俄國屋》(The Russian House)一書的卷首語是:“思想上我們必須像英雄,行為上我們才能做個起碼的好人。”該書作者雷卡勒的話又被他人用作克林頓傳記的卷首語:
……他什么也不信,所以萬事皆容,這樣的人我們奈何不得。他表面上是位謙謙君子,與人無爭。但實際上是明哲保身,對世上最可惡的罪行也視而不見。他墨守成規,無動于衷,但求無過……當然,這樣的人真是很討人喜歡。
至于《華爾街變革》一書,卷首語是卡爾里的一段話:
政府監管機構經常被稱為“獨立”機構。但只要你在華盛頓多少有點經歷,就知道這句話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沒有國會或行政部門的合作,很難有任何建設性的進展。可以特別強調地說,倘若立法部門或行政部門都漠不關心或是不肯援手,那么政府部門的一個機構是無能為力的。
“獨立機構”(independent ageney)的“獨立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人事獨立、準立法權和準司法權。人事獨立主要指證交會的主席、副主席的座椅相對穩定,他們一經任命,任期內不能被隨意撤換。準立法權(quasilegislative power)指行政機構憑借國會的授權,可以制定規則(rule-making)。準司法權(quasi-judieial power)指行政機構憑借國會的授權,可以審理有關當事人的權利。
斯里格曼教授借卡爾里之口強調,證交會雖有獨立的美名,但仍然不過是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的工具。證交會的成績最終歸功于這兩個部門。證交會的所有錯誤最終也歸因于這兩個部門。
卡爾里重新高舉道格拉斯的公司治理這面大旗,同時支持個人的民事訴訟。但其最主要的成績是將《證券交易法》的適用范圍擴大,即非上市公司的股東在500人以上,而且資產不少于100萬美元,則該公司也受證券法制約。同時,卡爾里繼續與紐約交易所作斗爭,努力消滅場地交易。
卡爾里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耶魯法學院的學生,師從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出任證交會主席,卡爾里又在其手下工作,門生故舊兼于一身。
“遍地英雄下夕煙”
工作之外我不會去看法律,相信絕大多數人也不喜歡看法律,但大家都喜歡聽故事,尤其是喜歡聽些流言蜚語。奇聞逸事是我們的精神食糧,而說三道四則是最大的免費消遣。律師、投資銀行家如此,各行各業的人也都好此道。斯里格曼教授也說了些證交會不足向外人道的故事。
首先是主席的人多。世界上主席最多的地方是聯合國,每屆聯大一位主席,五十多年下來便是五十多位主席,還不算特別聯大主席、各委員會主席和工作小組主席——真是主席多如牛毛。聯合國之后大概就要算證交會的主席多,因為主席們在任時間大多很短,有的不過一兩年。
在斯里格曼教授眼里,眾多主席中,算得上真英雄的不過四位。除上文提到的道格拉斯和卡爾里,還有第一任主席喬·肯尼迪和第二任主席杰姆·蘭德斯。喬·肯尼迪(Joe Kennedy)是約翰遜·肯尼迪總統的父親,靠為羅斯福總統拉選票而得到主席職位。喬·肯尼迪本人在股市中做手腳發了大財,基本可以算一個奸商。當時不少人認為,請這樣的人當證交會的主席,無異于開門揖盜,相當于請狐貍看雞圈。但是出人意料,喬·肯尼迪遏止了內幕交易,而且還保住了新生的證交會的地位。
第二位主席是杰姆·蘭德斯(James Landis),哈佛大學的法學教授。他的功績是為證交會繪制了一幅很好的藍圖。但蘭德斯的心思不在證交會,哈佛大學校長招他回去,此兄便執意要走,羅斯福總統也留不住。
證交會主席中有真英雄,有好人和比較好的人,但也有濫竽充數、尸位素餐者。在斯里格曼教授看來,杜魯門總統最不像話,先是逼走道格拉斯的學生甘遜·伯塞爾(Ganson Purcell),又弄來幾位拆爛污的主席。杜魯門任埃德蒙德·漢拉漢(Edmond Hanrahan)為主席,就是因為此兄為民主黨籌款立下了汗馬功勞。
哈里·麥克唐納(Harry Mcdonald)也是個笑料。此人干過14年的投資銀行工作,但側重的是乳制業,而且還是位共和黨黨員。但他與杜魯門私交甚好,兩人都愛好音樂。杜魯門喜歡彈鋼琴,有空便彈起他喜愛的《大篷車》,而麥克唐納則在總統的伴奏下引吭高歌。
不過,斯里格曼教授非常的實事求是,他專門提到,這些主席雖然無能,但對證交會沒有傷筋動骨。這種主席只是有礙證交會向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爭權、爭錢,但并不影響證交會日常工作的質量。第一任老主席就立下了辦事方針:發行與稽查這兩大塊主要由證交會高級職員決定。
曼紐爾·科恩(Manuel Cohen)在1964年到1969年任主席。此前他在證交會工作,是會內產生的第一位主席。
“證券法之父”
有些人沒有當過主席,但其作用不亞于主席。哈佛法學院的路易斯·勞斯(Louis Loss)教授便是一位。勞斯教授于耶魯法學院畢業,在證交會埋頭干了25個年頭,熬到副主任法律顧問的位置,離職后在哈佛大學任教,83歲仙逝。
肯尼迪哈佛大學畢業,他當選總統后,哈佛的許多學人彈冠相慶,準備應邀去華盛頓做官。基辛格也想去,但給他的職位太低,相當于正局級,終未成行。肯尼迪總統倒是誠邀勞斯教授出任證交會主席一職,但他堅辭不受,很有“桃園一向絕風塵”的意思。勞斯教授更著有一部《證券法實務》,長11卷,彪炳青史。哈佛大學法學院做了統計后很自豪地宣布,勞斯教授的著作被廣為引用,美國法院引用1000次,美國最高法院引用50多次。
勞斯作為教授,其最大成就是門生故舊遍布天下。斯里格曼教授也是他的學生,而且早在1974年便同恩師一起修訂《證券法實務》。換在中國這樣的禮儀之邦,斯里格曼教授必在自己的書中對恩師盡情謳歌。但斯里格曼教授沒有這樣做,對恩師可以說是一筆帶過。不過,按照一般西方人的習慣,斯里格曼教授在書中寫明,把書獻給了他所愛的人——大概是妻兒什么的。
所以說,斯里格曼教授遠沒有錢鐘書來得徹底。錢先生是徹底的唯物主義。他在《圍城》一書的序中寫道:“近來覺得獻書也像‘致身于國’、‘還政于民’等佳話,只是語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說交付出去,其實只仿佛魔術家玩的飛刀,放手而并沒有脫手。”當然,做人也難,感情和禮節上的一些事不說不行,但經常是一說就俗,難免有矯情的痕跡。
斯里格曼教授對恩師一筆帶過,但他確是勞斯教授的嫡傳。美國法學院的山門或是說師門遠沒有中國的那樣壁壘森嚴。只要同出一校,在美國就不可能四世同堂,輩分沒有那么多。美國的法學教授名望再高,也要親臨第一線教授基礎課。所以,只要是出自同一學校的師門,那大家都是平輩。
但誰是嫡傳卻不會有什么爭議,不會出現中國爭當高足的現象。嫡傳、單傳的標志是什么呢?就是他們的衣缽,而這個衣缽就是大師的巨作。大師年邁體弱后,都會與一位中年學者共同修訂自己的扛鼎之作。扛鼎之作可以是用作教科書的判例集,可以是勞斯教授的《證券法實務》,也可以是《華爾街變革》這樣的書。
畫龍點睛之筆
斯里格曼教授在書中也有畫龍點睛之筆,指出了證交會歷史上的各個工作重點。他認為,證交會與華爾街的斗爭的焦點并不是《證券法》,而是《公用設施控股公司法》。該法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此類公司的壟斷。當時在杜勒斯律師的煽動下,許多控股公司硬是不到證交會登記。直到美國最高法院出來說話,通過電子證券和股票公司訴證交會(Electric Bond and Shares v. Sec)的判決,明確表示支持證交會,各家控股公司才向證交會低頭。
公用設施控股公司當年玩弄的一些鬼蜮伎倆至今仍然在作怪。這些鬼蜮伎倆主要是會計方面的,其中包括:少算有形資產的折舊、將子公司未用的收益算作控股的利潤,以及高價向子公司出售控股公司的資產等關聯交易。
證交會與股票交易所的斗爭也是重大斗爭。道格拉斯認為,交易所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監管對交易的操縱,打破內幕知情人的交易優勢,防止經紀人濫用顧客的資金。而且道格拉斯認為,證交會應該起威懾作用,像把放在柜櫥中的滑膛槍,如果交易所越軌,證交會可以操起來便打。換句話說,在道格拉斯心目中,證交會應該很像一支督戰隊,逼迫交易所替天行道,規范其會員的行為。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中國與美國有許多相似之處,至少兩國轟轟烈烈的股市是全世界的兩面旗幟。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人像中、美兩國人民這樣鐘情股票。當然,中國歷史有自己的特色。只要講到歷史,無人離得開帝王史。我們也講農民的歷史,講農民的起義,講農民的戰爭。但農民起義史實際上也是帝王史,農民起義勝利后就是皇帝。小民也喜歡帝王的故事,他們恐懼帝王的天威,但又羨慕帝王的權勢和六宮粉黛。
讀了《華爾街變革》,我有一個小小的心愿,希望在法治的長征中,我們也可以記錄一些故事。可以先易后難,講講中國律師事務所的發家史。美國不僅是證交會這樣的政府機構有正史和野史,各大律師事務所和投資銀行也有自己的正義和野史,而其中不少是法律故事。利用歷史講法律,這也是法治方面的一件好事,法律教授中應該有些人去做這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