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云雷師兄的少年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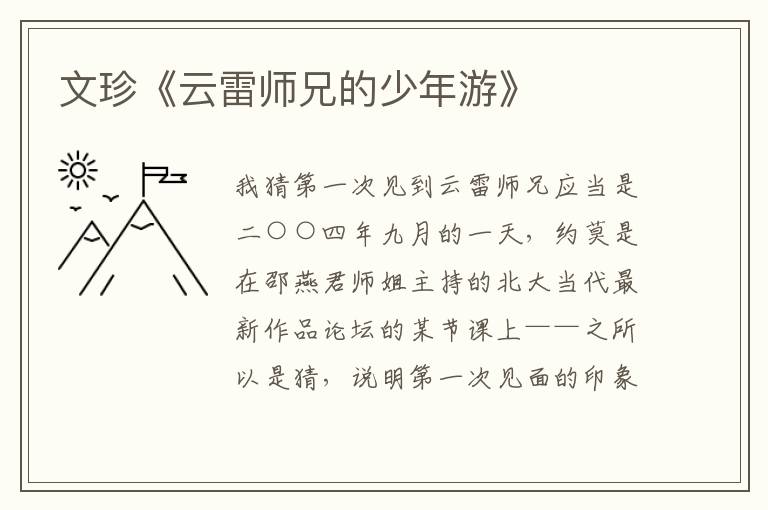
我猜第一次見到云雷師兄應當是二○○四年九月的一天,約莫是在邵燕君師姐主持的北大當代最新作品論壇的某節(jié)課上——之所以是猜,說明第一次見面的印象并不深,需依照其他事實邏輯推演而來。但認識云雷師兄十四年之后的今日再回溯,除了歸罪于我本人的臉盲癥,更重要的,則緣于云雷師兄固有的低調(diào)。一群人初相見,他必定是最后一個給人留下印象的。但印象一旦烙下,卻又極為深刻。倘若把不同的人比作元素,他顯然屬于惰性元素之一:大部分時候總是沉默寡言,對人也總是禮貌性微笑,藏身在眾人背后;大多數(shù)人向他說出的話,都可能遭遇不同程度的滯后反應。一言以蔽之:一個從不寒暄廢話的人。某種時候,甚至可以憤而稱其為“話題終結者”。
但你永遠不知道在某個不確定催化劑的作用下,這神秘的惰性元素會和環(huán)境突然產(chǎn)生怎樣劇烈的化學反應。這就造成了和云雷師兄交往最不可測也最有趣的地方。一個會讓人時時揣度其真正心意的寡言朋友,總是會教人更認真對待一點。他整個人就像金宇澄《繁花》里常使用的那個詞一樣,時時“不響”。但這不響,實際上又包含了一切將說未說或熱情或深沉的話語。他這次“不響”和上次“不響”,究竟有什么不同,究竟是真正地贊同你的話,還是只是心下存疑姑且擱置爭議,答案就好比《邊城》里翠翠所等待的儺送:“也許明天回來,也許永遠不回!”
經(jīng)過深思熟慮之后做出的若干判斷,因為隔了一點認真思索的時間,再出口總是更讓人難以質(zhì)疑。在當今這樣一個容易輕率發(fā)聲的屬于意見領袖和自媒體的時代,這樣的遲疑和慢,或許才更其難得。一句話說出口,擲地可作金石聲,很少收回,幾乎也不解釋:無他,寡言者必更惜字。
寥寥幾筆簡寫,便是云雷師兄最初給我的印象。但是他整個人又仿佛不斷在用全部行動、言語、個人愛好和獨特性情在反對這最初籠統(tǒng)的印象。以至于速寫之后,必須要徹底涂抹掉這輪廓才能重新開始:卷發(fā),皮膚黧黑,抽煙喝酒,總是羞澀地微笑。十多年以前,曾被人美譽為北大的“西班牙王子”。
但很奇怪的,那個青蔥歲月負笈求學的李云雷,在我印象中卻始終面目模糊。他的形象真正在我心目中清晰起來,卻是在自己開始工作之后。
也許了解一個人,只能通過更多“不響”的時間。
云雷師兄雖以當代文學評論名世,最早卻并非只寫作理論文章。在學校時,我就看過他的小說《少年游》。當時就隱隱震驚于文中可以認作個人經(jīng)驗的成分似乎太多,披心瀝膽,竟是坦蕩蕩無遮擋的毫不設防。細想其人,又一時釋然。人總需要傾訴的缺口,或正因為日常生活里的過分謹言慎行,云雷才會選擇文字作為最真實的宣泄口。他早年也寫詩。我猜想——仍是猜想而無有實證——也正因為此,詩歌里的他比日常、比小說中還要更大膽。有一首我記憶尤深,應該寫于在國際關系學院就讀日語本科期間:
她們從女浴室里出來后總顯得更美一點
也許是顯得比原來要胖一些
內(nèi)容大抵如此,原句卻記不真切了。看上去志誠君子的云雷師兄,從此小處落筆亦無猥瑣之感,只教人遙想他當年大概也是一個對美好事物分外敏感的青年。
還有一次,同門約去唱K,大家?guī)追堅评撰I聲,他總害羞推拒,后來實在推不過了,一開口卻是久違的《梅花三弄》,且嗓音驚人地清澈高亢。后來讀曹老師給他寫的印象記,里面也提到《梅花三弄》,看來是他的當家曲目,大概也是文學青年時期的遺跡之一。
后來又看云雷師兄在朋友圈曬中學時期的通信和字條,字跡清秀,且多年來保存完好,讓人驚嘆。師兄的青少年時代果然就是《再見,牛魔王》里那個少年“我”的原型:多思,靦腆,溫和,寡言,卻又無比念舊多情。
師嫂米靜讀書時我就見過多次,據(jù)說是他就讀于國際關系學院時的師妹。米靜本人我也極喜歡,秀麗開朗,本科英語,碩士就讀于北京電影學院,畢業(yè)后留校任教,近年來練成羽毛球業(yè)余高段,可與專業(yè)選手一決高下——與云雷的文靜少言恰可以互補。我讀研期間師兄還在讀博,那幾年師門常在曹師家聚會,眾直男食完作鳥獸散,米靜總和小師妹們?nèi)缥业葼帗屜赐胫邸R话胍驗樵评讕熜质鞘苋俗鹁吹拇髱熜郑话胍惨驗閹熒┍救思蚊目上玻T上下都被她折服,有一次不知誰開玩笑:“米靜這么美,在學校一定很受男生歡迎吧。”至今猶記她當時沉靜大方地笑:“是有些學生自稱‘米粉’的,不過還是要和學生保持一點距離才好。”
如此正大仙容,同時又態(tài)度景然,別人再開無聊玩笑便開不下去。這一點卻隨云雷的端正老派。她社交平臺上稱呼師兄為“雷”,只此一字,鶼鰈蘊藉之意全出。
師嫂給我們帶來的其他福利,還包括時常帶我們?nèi)タ幢本╇娪皩W院的內(nèi)部主題影展。我就跟著沾過許多回光。有一次還集體組團去看黃紀蘇先生執(zhí)導的話劇女版《切·格瓦拉》,大約是在2005年,當時圓臉大眼的湯小姐在一群軍裝麗人中已經(jīng)分外打眼,雖然離拍《色·戒》尚有數(shù)年。也記得某次散場后我們一堆師弟妹們嬉笑著走出劇場,突見一對璧人在不遠處并肩而行,細看正是云雷和米靜。是某個相當教人沉醉的春夜,細數(shù)起來,竟然是十三年前了。
因為曹老師本人并不喝酒,同門亦多不善飲。也是在米靜嘴中,我們才知道云雷師兄平素自己在家中也要獨喝一瓶小二,堪稱曹門飲酒擔當。但云雷之好酒并非酒膩子式的纏人,也從未爛醉如泥。上桌不大敬酒,也絕不苦勸人喝。我甚至懷疑,他只有喝酒,才能略微多說一些話。是為了說更多的話,才會喝更多的酒。尤其是只寫評論不寫小說和詩歌的前些年。有一次一個認識多年的朋友開車送他回家時聽他在后座多臧否了幾句人物,還因過于吃驚接連開錯幾個路口。其人喝酒前后之別,可見一斑。
一次也是在曹老師家里聚會,那天云雷師兄自帶了兩瓶紅酒,自斟自飲了一多半,約莫薄醉,遂默然坐在客廳地板上。米靜悄悄拉我掩嘴笑道:“你看,云雷喝醉了就和一只大熊一樣一樣的!”但我后來也頗見過一兩次她看他喝多后的氣惱擔心。
與此同時,云雷師兄的少年酒壇子之名也隨文名日盛。據(jù)說總有一斤半白酒的量,若遇好酒,更難計其數(shù)。這一年來卻聽說師兄漸漸戒了酒。我想一方面初為人父,責任感不免加重;另一方面,大概也和他重新開始寫小說有關。有地方可以傾吐心聲,就不必一味借助杜康消愁。而這樣,米靜也許也可以少擔一點心吧——小酌怡情,大醉傷身,不飲自是好事。
除掉喝酒、閱讀和寫作,云雷作為沉默寡言者的私人愛好,還包括徒步和攝影。不知道從哪一天起——約莫是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附近的北苑買了房子之后——他的朋友圈里開始主要充斥兩種攝影主題,一類就是奧森的四時寒暑、流云飛雪、草木魚蟲,一種則是“在底層”系列,主角則是附近城中村一位被他命名為“小胖”的陌生男孩。一方面心系自然風物,流連于天光云影間;另一面,也從未停止對真實的人間世的關切和同情,這兩者,都是我所熟悉的云雷師兄。
說到這里,就忍不住回想起一個師兄幾年前和我說起的云雷一樁軼事。說他讀博士后又順利留京,山東老家人滿以為他當了大官,有一次有人遇到解決不了的難事便帶上土特產(chǎn)進京求助。因是轉(zhuǎn)述,那師兄也講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只說肯定超過了云雷的能力范圍,而云雷當時的反應出乎所有人意料,竟是伏案大哭,邊哭邊說我讀這么多書到底有什么用?到底可以為家鄉(xiāng)父老做什么?
聽故事時,我腦海中自然而然浮現(xiàn)師兄酒后大哭的醉態(tài)。一個平素極少流露感情的人,這樣失態(tài)多半只能在酒后;但酒后這番真情流露,已足以令人動容。
還有一次同去皮村的同心果園聽大地民謠演唱會。當時是八月,正是京郊水蜜桃成熟的季節(jié)。那天一起去聽民謠的,還有梁鴻老師和她兒子。幾年前也和云雷師兄還有幾個朋友去過他們舉辦的打工春晚,還在觀眾席見過韓少功和張承志先生,節(jié)目也很新鮮可喜,故當天不惜開車六七十公里去看。這回皮村的朋友告訴我們,正趕上果園桃子豐收,外來朋友可以自摘,出園稱重即可。
我認識云雷師兄那么多年,第一次看到八月耀目的陽光下,碩果累累的桃園里,他笑得完全像個孩子……好像回到了少年時代長大的地方,回到了《少年游》《暗夜行路》《縱橫四海》里寫過的村莊。
也就是在同一天晚上,打道回城后才想起忘了吃飯,路邊小飯館幾杯薄酒后,云雷師兄突然說:“這些年好些朋友都變了……我自己也變了,變了很多。讀越多書,越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能為老百姓做什么……有時候?qū)嵲陔y受,只能拍拍風景,讓人知道我還在努力生活,還沒有被那些人那些事完全擊垮。”
到底會被什么擊垮呢,被曾經(jīng)天真而今早已消磨的理想,被那么多人仍在受苦的“中國故事”,柴米油鹽漸漸失去詩意的現(xiàn)實生活,還是永遠無法對自己滿意的當下?
平時總是說話更多的我就在那一刻啞然,同時又無比清晰地回想起白天在桃樹間見到的他的燦爛笑容。我想告訴他:骨子里一個真正的大寫的人是不會變的。只要還能問出這個問題,那么他便仍舊還是那個初入京城充滿驚異,對現(xiàn)實卻又從未停止思索的赤子。但我忘了當時究竟開口了沒有。也許沒有。那么,就在這里補說。
“初心曾記否?舊江山渾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游。”
2018年3月11日
安翔路1號附:
李云雷主要作品目錄
短篇小說:
花兒與少年,《廣州文藝》2002.6
朝圣之旅,《廣州文藝》2002.6
小城之春,《文學港》2003.4
初戀,《海峽》2004.1
秋去春來,《海峽》2004.1
葬禮, 《山花》2006.6
假面告白,《山花》2006.6
少年行, 《西湖》2006.7
花非花 ——少年行之二, 《西湖》2006.7
一條路越走越遠,《西湖》2006.7
巧玲瓏夜鬼張橫,《紅豆》2007.1,《小說選刊》2007.4
父親與果園, 《十月》2010.5,收入《全球華語小說大系·鄉(xiāng)土與底層卷》
上席,《文學界》2011.5
再見,牛魔王,《青年文學》2016.4,《小說選刊》2016.6
電影放映員,《人民文學》2016.4
縱橫四海,《作品》2016.7,《小說月報》2016.9
界碑,《十月》2016.6
暗夜行路,《當代》2016.6
三畝地,《當代》2016.6
哈雷彗星,《江南》2016.6,《小說選刊》2017.1
林間空地,《芙蓉》2017.1
梨花與月亮,《人民文學》2017.2
織女,《中國作家》2017.2,《中華文學選刊》2017.4
鄉(xiāng)村醫(yī)生,《青年文學》2017.2
富貴不能淫,《南方文學》2017.2
啞巴與公羊,《青年作家》2017.5
草莓的滋味,《人民文學》2017.6
泉水叮咚響,《長江文藝》2017.6
鐵匠的女兒,《江南》2017.6
我們?nèi)タ床屎绨桑渡虾N膶W》2017.9
紅燈籠,《北京文學》2017.11,《長江文藝·好小說》2018.1
小偷與花朵,《青年文學》2017.12,《小說月報》2018.2
并不完美的愛,《紅豆》2017.12
雙曲線,《廣州文藝》2018.3
中篇小說:
無止境的游戲,《大家》2007.6
初雪,《中國作家》2007.9
舅舅的花園,《十月》2010.5,獲“十月文學獎”
無神論者拜菩薩,《大家》2017.5
文學評論:
“不能走那條路”——對當代中國農(nóng)村政策的文學考察,《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2
童真與想像中的詩意——讀泰戈爾《紙船》,《語文建設》2004.3
未完成的“金光大道”——對我國農(nóng)村社會主義道路的再思考,《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4
近期“三農(nóng)題材”小說述評,《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6
對藝術和現(xiàn)實的變革與探索——評打工青年藝術團的音樂及其實踐,《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2
《秦腔》與鄉(xiāng)土中國敘事,《三農(nóng)中國》2005.6
轉(zhuǎn)變中的中國與中國知識界——《那兒》討論評析,臺灣《人間思想與創(chuàng)作叢刊》2006.春季號
底層寫作的誤區(qū)與新“左翼文藝”的可能性,《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6.1
《蒼生》與當代中國農(nóng)村敘事的轉(zhuǎn)折,《文學評論》2006.3
疲勞的“魔幻”,《21世紀經(jīng)濟報道》2006.3.3
歷史的碎片與“地方志”小說,《21世紀經(jīng)濟報道》2006.3.10
我們應該站在何處,《小說選刊》2006.7
從排斥到認同——20年來大陸作家對陳映真的“接受史”,臺灣《批判與再造》2006.7
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上海文學》2006.11
2006:“底層敘事”的新拓展,《文藝理論與批評》2007.1
“底層敘事”前進的方向,《小說選刊》2007.5
如何生產(chǎn)中國的形象,《上海文學》2007.8
底層敘事是一種先鋒,《文藝報》2007.9.4
胡風的另一個悲劇,《中國教育報》2007.10.25
“底層文學”在新世紀的崛起,《天涯》2008.1
先鋒的“底層”轉(zhuǎn)向——劉繼明近期創(chuàng)作論,《小說評論》2008.2
新世紀德國電影中的“柏林墻”,《電影藝術》2008.2
中國電影:“大片時代”的底層敘事,《藝術評論》2008.3
賈平凹與新世紀文學的“底層”轉(zhuǎn)向,《蘭州大學學報》2008.5
肯·洛奇的雙重挑戰(zhàn)與超越,《電影藝術》2008.6
“底層”、魅惑與小說的可能性——讀魯敏的中短篇小說,《當代文壇》2008.6
錢理群的“雙重反思”,《讀書》2008.12
秦兆陽:現(xiàn)實主義的“邊界”,《文學評論》2009.1
我們?nèi)绾螖⑹鲛r(nóng)村——關于“新鄉(xiāng)土小說”的三個問題,《江蘇社會科學》2009.1
如何闡釋中國與中國文學,《南方文壇》2009.1
“神話”,或黃金時代的背后,《天涯》2009.2
我們?yōu)槭裁炊v故事——從《瘋狂的賽車》說起,《電影藝術》2009.2
《問蒼茫》與“新左翼文學”的可能性,《南方文壇》2009.2
日本的“《蟹工船》現(xiàn)象”及其啟示,《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3
看不到的“鐵人”,《電影藝術》2009.4
當今時代,知識分子何為,《天涯》2009.6
小說如何切入現(xiàn)實,《文藝報》2009.7.7
中國電視劇:為什么這么火,《藝術評論》2009.11
隱秘的疼痛及其詩意表達——讀付秀瑩的《愛情到處流傳》,《名作欣賞》2010.1
《建國大業(yè)》:新“模式”及其問題,《電影藝術》2010.1
我們?yōu)楹味x書,《天涯》2010.3
從“純文學”到“底層文學”——李云雷訪談錄,《藝術廣角》2010.3
“打工文學”:新的美學萌芽,《社會科學報》2010.3.18
新世紀文學中的“底層文學”論綱,《文藝爭鳴》2010.6
記憶的詩學及其穿透世界的力量,《南方文壇》2010.6
文學與我們的生命體驗,《文藝報》2010.7.28
我們能否理解“故鄉(xiāng)”——讀梁鴻的《梁莊》,《南方文壇》2011.1
工人生活、歷史轉(zhuǎn)折與新的可能性——簡評《鋼的琴》,《電影藝術》2011.2
我們能否理解這個世界——“非虛構”與文學的可能性,《文藝爭鳴》2011.2
我們能否想象我們的“未來”,《文藝報》2011.3.7
批評是一種創(chuàng)造,《文藝報》2011.4.8
重建“公共性”,文學方能走出窘境,《人民日報》2011.4.13
文學“新人”預示時代走向,《光明日報》2011.6.20
告別的艱難與繾綣,《中華讀書報》2012.5.9
中國人“世界想象”的變遷,《社會科學報》2012.7.6
莫言獲獎的三重意義,《中國文化報》2012.12.13
“新文學的終結”及相關問題,《南方文壇》2013.5
中國鄉(xiāng)村的“新現(xiàn)實”及其藝術化——以陳應松三篇近作為例,《創(chuàng)作與評論》2013.5
美國想象與當代社會思潮,《中國文化報》2013.8.13
歷史視野中的“官場小說”,《文化縱橫》2013.6
如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文學評論》2014.3
賽珍珠: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南方文壇》2014.5
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文化“主體”,《長江文藝》2014.8
“新工人美學”的萌芽與可能性,《天涯》2014.2
虛構的“故鄉(xiāng)”及其精神隱秘——從大陸看《復島》,《當代作家評論》2015.1
重申“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人民日報》2015.2.6
新工人詩歌的“崛起”,《文藝報》2015.3.26
在新的圖景中重建中國視野,《文藝報》2015.4.17
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人民日報》2015.6.5
《白毛女》:風雨七十年,《光明日報》2015.7.31
《三體》:科幻文學之外的意義,《文藝報》2015.8.28
青年批評家面臨的時代問題,《文藝報》2016.3.21
全球化時代的“失敗青年”,《文藝報》2016.3.25
“田園將蕪,胡不歸”——新時期以來中國人與土地關系的變化,《當代作家評論》2016.4
現(xiàn)實主義:越來越廣闊的道路,《人民日報》2016.4.8
中國工人的“史詩”,《文藝報》2016.4.15
歷史的通俗化、美學與意識形態(tài)——嚴歌苓小說批評,《長江文藝評論》2016.5
陳映真是一面精神旗幟,《文藝報》2017.1.25
重返歷史的態(tài)度與方法——洪子誠《材料與注釋》的啟示,《文藝爭鳴》2017.2
“新社會主義文學”的可能性及其探索——讀劉繼明的《人境》,《當代作家評論》2017.3
歷史新視野中的兩個《講話》,《文學評論》2017.5
如何創(chuàng)造中華民族新史詩,《文藝報》2017.10.11
長篇小說與我們的時代生活,《學習時報》2017.10.13
故鄉(xiāng)、初心與我們的時代,《中國藝術報》2017.11.29
文學批評應對“新時期文學”起到建設性作用,《文藝報》2018.2.23
作品集:
父親與果園(小說集),山東文藝出版社,2015.3
再見,牛魔王(小說集),作家出版社,2017.11
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評論集),作家出版社,2011.1
重申“新文學”的理想(評論集),北大出版社,2013.6
新世紀底層文學與中國故事(專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11
新視野下的文化與世界(評論集),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6
70后批評家文叢·李云雷卷(評論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7
當代中國文學的前沿問題(評論集),山東文藝出版社,2017.4
如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評論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