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州窯記》李清明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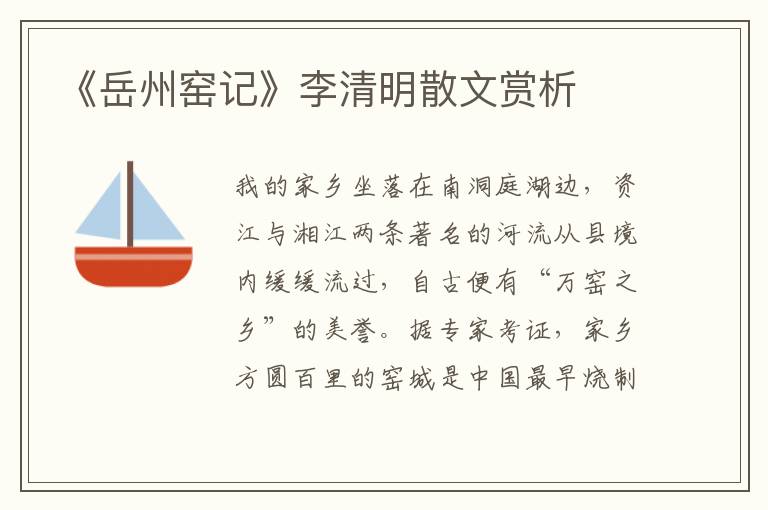
我的家鄉(xiāng)坐落在南洞庭湖邊,資江與湘江兩條著名的河流從縣境內(nèi)緩緩流過,自古便有“萬窯之鄉(xiāng)”的美譽。據(jù)專家考證,家鄉(xiāng)方圓百里的窯城是中國最早燒制青瓷與官窯的地方,曾創(chuàng)造了中國陶瓷業(yè)界的“七個之最”,距今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
少小離家老大回,我穿著鄉(xiāng)愁的草鞋,走遍了洞庭水鄉(xiāng)的山山水水,開始了對湘陰窯(也稱岳州窯)前世今生的追尋與考證。
兒 時 記 憶
小時候生活在洞庭湖水鄉(xiāng),總見有一位或幾位身體敦實、面容黢黑、皺褶蒼茫、頭戴氈帽或草帽、走村串戶販賣各種窯貨的中老年人。他們肩挑一副用竹子或蘆葦,也有的用柳條,編制的平底擔(dān)子,上面壘放著各種各樣的大小窯貨,有碗、有碟、有缽、有壺、有罐,有加蓋或敝口的水缸與壇子,有人俑、牛俑、馬俑,有栩栩如生的神、鬼、道及戲曲人物,甚至還有造型怪異的各種馬桶與尿壺……雖是交易,但他們大都不高聲吆喝與叫賣,只是拿著一根長長的竹片,邊走邊敲擊窯貨,其“叮叮——當(dāng)當(dāng)”或“梆梆——嗡嗡”的聲響,有些與寺廟和尚們擊鐘與敲罄的聲音相近,給空曠、寂寥的水鄉(xiāng)村莊平添了幾許古樸與禪意、清亮與悠遠(yuǎn)。
聽到陶瓷的敲擊聲,鄉(xiāng)親們多會聞聲而動。他們用卷了毛邊的鈔票,或一小捧叮叮當(dāng)當(dāng)?shù)挠矌牛驇咨竺住讉€雞蛋等物品,與早就熟悉的貨郎們進(jìn)行交換。用這些普通甚至有些粗糙的陶瓷產(chǎn)品把貧窮、苦澀、單調(diào)的鄉(xiāng)村生活過得有聲有色、有滋有味。比如,母親們用大肚端罐深埋于燃而未燼的草木灰中煨制的香噴噴、軟綿綿的糯米、粳米、紅薯、綠豆稀飯,回味起來至今仍口齒留香;用素胎或醬釉印紋的雙唇壇子腌制的黃瓜、生姜、紫蘇、藠頭、湖蔥等各種泡菜與腌菜,健脾開胃,長年不壞;用敝口茶罐熬制的大葉茶(也叫粗茶,或“三皮罐”),味道淳厚解渴,即使炎熱的夏季,露天儲存,放上幾天幾夜也不會變質(zhì)變味。至于水鄉(xiāng)的姑娘、媳婦們用素胎或施了醬釉的端罐煎制的“姜鹽豆子芝麻茶”,不但能強身健體、醫(yī)治感冒,還能充饑飽肚,堪稱水鄉(xiāng)一絕。水鄉(xiāng)新娘第一次上夫家待客,還能將整罐裝有80粒花生、80粒黃豆的姜鹽茶,順時鐘與逆時鐘地將罐體轉(zhuǎn)上三圈后,倒出來的10碗茶內(nèi),每碗居然均是數(shù)量相等的8粒花生與8粒黃豆!令鄉(xiāng)親們有些不解的是,此種篩茶方法與效果只能適用于本地窯城,即湘陰岳州窯生產(chǎn)的大肚端罐(又名大化罐),異地窯貨則難以產(chǎn)生如此奇妙的效果。
還有,但凡水鄉(xiāng)姑娘出嫁,其陪嫁品中必有一只或數(shù)只不等的裝有祖?zhèn)鹘呐莶藟印4宋餅橄骊幵乐莞G中的“下窯”(也稱大貨窯,或平窯)的主打產(chǎn)品。形似水桶,兩頭小,中間大,上露雙唇的頂部配以狀如蒸缽一樣的陶蓋;常以素胎為主,也有的略施醬釉或青釉;內(nèi)置的浸水以煮熟的白醋及開水為主,再在雙唇的間隙里倒上一碗清水便可較好地自然密封。被鄉(xiāng)親們視為祖?zhèn)髦锏慕畨又灰褂玫卯?dāng),不讓生水或臟物進(jìn)入壇內(nèi),能百年不壞。更為神奇的是,鄉(xiāng)親們不但可以用浸水壇子預(yù)測天氣,而且還可以通過其好壞的質(zhì)變預(yù)測其家庭運程的好壞。哪日如果發(fā)現(xiàn)浸水壇子雙唇里儲存的清水不斷地冒泡,且頂擊壇蓋發(fā)出“咕咕——咕咕”的響聲,第二天多會刮風(fēng)下雨;如果突然發(fā)現(xiàn)壇內(nèi)的浸水無故變味或變壞,家庭個別成員多會突發(fā)急病,或仕途受阻……不久前,九十高齡的鄰居彭娭毑,一日一壇陪嫁且輾轉(zhuǎn)跟著老人搬了六次家的浸水突然壞了。老人憂心忡忡過了兩天,第三天便傳來了在鄰縣做官的二兒子被“雙規(guī)”的消息。
尤記初中上歷史課時,老師還告訴我們,在離家鄉(xiāng)不遠(yuǎn)處的長沙發(fā)掘的馬王堆漢墓中,也驚現(xiàn)22個標(biāo)注有“魚脂一資(瓷)”、“肉醬一資(瓷)”、“雀醬一資(瓷)”等文字的泡菜與浸水壇子。后據(jù)陶瓷專家考證,出現(xiàn)在長沙侯辛追夫人墓室中的壇罐均為湘陰岳州窯西漢初期的產(chǎn)品。
也許是過去銷往鄉(xiāng)村“歪瓜裂棗”般的陶器制品較為常見的緣故,就連平日里鄉(xiāng)親們調(diào)侃罵人,也是離不開“窯貨”二字。比如,遇有個別頑皮的小孩,大人們常會戲罵成:“這個窯貨喲,好調(diào)皮吶”,“你這個歪嘴夜壺喲,真是該死”;如果是一幫小伙子調(diào)皮搗蛋,則多會調(diào)侃成:“你們這一窯燒的”,或說是“窯貨擔(dān)子摔跟頭—— 一個好的都冇得”;就連偶見一位容貌姣好的女人,也多會咂嘴點頭,稱其“漂亮得像一個窯姐”;甚至,鄉(xiāng)親們概括家里的家財產(chǎn)業(yè),也多會用“壇壇罐罐”四字替代……
那時,水鄉(xiāng)漢子一年的工作均只有三種選擇:一是在家種植水稻,飼養(yǎng)家禽;二是進(jìn)入到洞庭湖里打漁、駕排、砍蘆葦,簡稱“漁樵”;三就是去到相距不遠(yuǎn)、位于縣城邊的窯城打工。也有春夏兩季打漁、秋冬季節(jié)里忙著拉坯燒窯的,則多會被簡稱為“陶漁”。大人們常說,從古至今位于縣城邊的窯場很多、很大、很長,并形容為“縣城有個萬窯窩,要進(jìn)城門過窯坡”。還說,我們?nèi)粘I罾锸褂玫母G貨均出自窯城的大貨窯,簡稱“下窯”,以湘江下游的烏龍窯、蘆林潭窯、白泥湖窯為主;還有專出青瓷、白瓷、黑瓷的“中窯”與“上窯”,以位于湘江中游的馬王墈窯、青竹寺窯、白梅窯、鐵角嘴窯最為著名。
也是從那時開始,我們便知曉,大貨窯(也稱平窯)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只能叫陶器,其燒焙溫度在900度左右;專產(chǎn)瓷器的叫官窯或上窯,其燒焙溫度須在1300度以上。它們均被統(tǒng)稱為岳州窯,又名湘陰窯。
這些窯場明明都集中在家鄉(xiāng)的縣城邊,為何又叫岳州窯呢?大人們的解釋是,在窯場最為鼎盛時期的唐代,家鄉(xiāng)屬岳州轄地,故稱岳州窯。
官 窯 血 淚
縱觀湘陰岳州窯的發(fā)展過程,近兩千年的創(chuàng)燒歷史,其實就是既簡單而又復(fù)雜的三個階段,先是平窯,頂峰期為官窯,然后又回歸漫長的平窯燒制期。湘陰窯的燒制,據(jù)傳殷商之前,舜帝就率先民在湘江一帶開始了制陶之業(yè),進(jìn)行原始的手工制作。后又從西漢、東漢開始,經(jīng)三國、東晉、西晉,南北朝,這一時期主要是以燒制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陶制品為主,也稱大貨窯或平窯。真正開始燒制官窯,即精美的瓷器,則是從隋朝開始的。
1997年6月,家鄉(xiāng)的縣政府在縣城一個叫馬王墈的地方興建宿舍樓,挖地基時,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青瓷片堆積層。只見工作人員在約6米深的文化層中取出了大量的青瓷器物和匣體,較多的有碗、盅、洗、杯及高足盤、四系罐、檐口壇、多足硯、蓮花樽等。釉色以豆青、蝦青為主,色澤晶瑩光潔,紋飾有劃紋、印紋及釉下點彩等等。后經(jīng)專家考證,這是一座隋代青瓷窯址。
誰承想,馬王墈窯址這一挖,竟挖出了湘陰岳州窯在中國陶瓷史上的“七個之最”。即:最早的青瓷、最早的白瓷、最早的官窯、最早的釉下點彩、最早使用匣缽腹燒、最早在瓷器上開始壓紋技術(shù)、最早有準(zhǔn)確年代記載的窯址(公元143年)。也是從這時開始,人們發(fā)現(xiàn)岳州窯當(dāng)時沿湘江兩岸的湖、港、溝邊建窯燒制,各個窯址均以馬王墈窯址為中心沿湘江向上下流域延伸。順江水而下的主要有三峰窯、烏龍嘴窯、蘆林潭窯、營田窯,一直與岳陽的鹿角窯相連;逆水而上的則有八甲窯、白梅窯、青竹寺窯、洋沙湖窯、鐵角嘴窯,并直接與長沙窯的代表銅官窯對接。目前光發(fā)掘與勘探得知的便有三十多處,其間還有許多的窯址尚處“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之境地,其創(chuàng)燒年代可上溯至西漢時期。
馬王墈的發(fā)掘,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莫過于從中發(fā)現(xiàn)了一座長8米、寬2米,里面布滿了每排8個、共計25排匣缽的龍窯。說起時越東晉的匣缽腹燒法,岳州窯的傳人吳軍平先生拉開了話匣,說起了其先祖發(fā)明此種燒窯方法的一段十分優(yōu)美的傳說。
很久以前的湘陰窯,其窯體都是平頂?shù)姆叫闻c菱形,容量很小,難以批量生產(chǎn),且一遇窯內(nèi)高溫及窯外大水,便會常常引發(fā)窯體垮塌,以至窯毀人亡。吳軍平的先祖嘗試著用加高窯體、增厚窯壁、用鐵制品爐橋相隔等許多辦法,仍是屢試屢敗……一日,吳老窯師累得在塌窯邊昏昏欲睡,忽見老人以前經(jīng)常在洞庭廟中祭祀過的洞庭龍王的三女兒飄然而至,手里還提著一個精美的梳妝匣。小龍女目光如炬地緊盯著老人,先是用右手,指指左手提著的梳妝匣;然后又緩緩解開自己的衣襟,也是用右手,指指自己的乳房……在一陣輕煙騰起之際便消失得無影無蹤。老窯師醒后,冥思許久……仿若突然頓悟。老人先是按龍女指點,將過去方形與菱形的窯體改砌成小龍女乳房模樣的圓拱形大窯,再在主窯兩邊分別砌上一個內(nèi)空相連的小奶窯……如此這般,不但使大小相連的窯體能充分利用熱能,降低成本,增加產(chǎn)量;而且使窯體更加牢固可靠,遇高溫與水患少有垮塌。因大小窯體一個個連綿相延,窯體的火口與煙囪極像龍口與龍角,加之又系龍女指點,鄉(xiāng)親們便把這一形狀的窯體稱之為龍窯。
還有,過去先輩們燒窯,大都是將制作好的素坯直接放進(jìn)窯體內(nèi)進(jìn)行燒制,既容易粘連,受熱不均,還易被炭灰直接污染……以至于歪嘴裂口、壓扁壓裂的殘次品窯貨很多。史書有載,當(dāng)時的湘陰岳州窯便有“質(zhì)甚粗,體甚厚,釉色淺而糙”、“只供邇俗粗用之”等描述。這也是鄉(xiāng)親們發(fā)生口角常以“窯貨”二字相罵的直接原因。
幾天后,吳窯師回到家中又想起了小龍女指點隨身攜帶的梳妝匣的奇妙舉動。于是老人又急切找來老伴年輕時從娘家陪嫁過來的梳妝匣子,也是一番左摸右看,仔細(xì)琢磨起來……受此啟發(fā),回到窯場的老窯師將待燒的陶窯制品,裝進(jìn)經(jīng)高溫焙燒過的匣缽中裝窯升火,反復(fù)試驗,使改用的匣缽體腹燒法一舉成功。后人們總結(jié),其發(fā)明的匣缽體燒窯法,不但防止了陶窯制品與窯火的直接接觸,避免了污染、粘連;并且受熱均勻,釉色更加光潔精美匣體成排壘砌,反復(fù)使用,陶瓷的產(chǎn)量也成倍增長……被稱作是陶瓷界的一次革命,也是湘陰窯在中國陶瓷發(fā)展史上最大的貢獻(xiàn)。
后來,窯城的先輩們又采用高硅瓷胎,使用高鈣釉面,湘陰窯所燒器物溫度均衡,釉面光潔,胎質(zhì)堅硬,且瓷化極高。也許是受窯城周邊洞庭湖自然景色的影響,還有窯師們大都曾是漁獵出身的緣故,湘陰窯的釉色均以豆青、蝦青為主,綠中泛青,間或有淡黃、淡白作為點綴,由此也成就了湘陰岳州窯的古樸與大方、自然與精美。
我曾在馬王墈隋代青瓷窯址中,反復(fù)觀看并用戴著手套的手指細(xì)心摩挲過兩件印刻有“官”字的物品。一件是底部印有“官”字的鉀體,另一件為內(nèi)底印有“大官”陽文的南朝時期的圓餅底碗殘片。該碗片釉色綠中泛黃,瑩光閃爍,晶瑩如玉,成器高雅華貴。后又在湖南省博物館見到了該館收藏的一件也是出自湘陰岳州窯、底部印有“大官”字樣的茶杯,其品相與質(zhì)地也同樣是釉薄而質(zhì)細(xì),垂釉如淚,玻璃質(zhì)感強。這一特點,正是湘陰岳州窯自發(fā)明匣缽裝燒法后的重要特色。后經(jīng)專家考證,“大官”即官名,秦漢時期便封有“太官令”,又稱“大官”,為掌管皇帝膳食和宴會的官員。由此也印證了故鄉(xiāng)湘陰的窯城曾有四十八座皇窯的說法。也是從那時開始,湘陰岳州窯開始躋身于中國六大名窯之列。
據(jù)史書記載,從兩晉至清朝的一千多年間,當(dāng)時還設(shè)在洞庭湖邊一個叫琴棋望古鎮(zhèn)的縣衙邊便多了一處“皇家官窯采辦處”,其品質(zhì)與規(guī)格與州府平級。黃馬褂們的到來,除了給當(dāng)?shù)氐奶沾僧a(chǎn)品增添了一些虛有的名氣外,對于廣大的窯民來說卻無丁點實質(zhì)性的好處。采辦處與本地縣衙內(nèi)的官員們多內(nèi)外勾結(jié),沆瀣一氣,以欺上瞞下、魚肉當(dāng)?shù)匕傩諡槟苁隆5材膫€窯莊接到了“皇命”,輕則身遭杖責(zé),重則傾家蕩產(chǎn),甚至家破人亡。民謠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采辦處的黃馬褂。還有:皇榜高懸不敢揭,揭了多是催命符;燒件官窯脫層皮,領(lǐng)份皇差送條命;窯工碗中泡苦水,官差貪斂把命催。
一個窯工由學(xué)徒開始直至成為一名出色的窯師多為不易,他們須10年至12年的磨礪,甚至連何種工藝學(xué)習(xí)多久都有嚴(yán)格的時間與技術(shù)規(guī)定。即淘泥、摞泥、拉坯、捺水、畫坯、修補分別為一年時間,裝窯、燒窯及外出游歷與參師均為兩年。湘陰百里窯城內(nèi)曾有兩位最為著名的窯師,素有“上張中吳”之說。即:上窯的張窯師,大名張義軍;中窯的吳窯師,名叫吳大年。
吳窯師的出場正值南宋年間,當(dāng)時的宋高宗趙構(gòu)為向金主乞和,下令湘陰岳州窯須在一個月之內(nèi)燒制四對青釉龍首壺作為貢品。要求龍壺長高各兩尺,且須外繞龍鱗,下飾海水。其時正值當(dāng)朝左丞相秦檜六十壽辰之際,采辦太監(jiān)又假借圣旨,在原有“皇命”的基礎(chǔ)上增添了六十套底部標(biāo)注有“福祿壽”字樣的官窯暗花碗碟,準(zhǔn)備以此作為壽禮向權(quán)臣獻(xiàn)媚。采辦太監(jiān)把“催命符”交到了當(dāng)時的三峰窯窯主吳大年手中。吳窯師親率一百多名徒弟日夜加班,趕緊選泥、淘泥、制坯、上釉、裝窯、升火……無奈工期太緊,且工程繁復(fù)巨大,眼看皇家規(guī)定的期限馬上就要到了,而任務(wù)卻只完成三分之二……一日,吳窯師在受到官窯監(jiān)工及主事太監(jiān)的一頓鞭笞之后,只得含淚跳進(jìn)正在熊熊燃燒窯火的官窯,化成了一縷青煙……
時間跨至七百多年后的清朝,主持青竹寺窯的窯主張老三精心燒制出了一件官窯神器——紫陶。其色如紫、薄如紙、聲如瓷,據(jù)說用其煲制燕窩,能看到母燕的舞影,能聽到乳燕的呢喃。當(dāng)時的湖南巡撫端方聞訊,準(zhǔn)備上奏朝廷,責(zé)令湘陰岳州窯燒制一批紫陶,作為貢品獻(xiàn)給慈禧太后。張老三得知消息后驚嚇得夜不能寐,因有無數(shù)的前車之鑒,為了保住窯莊、保住自己及全家人的性命,他連夜喝下一小口水鄉(xiāng)毒草“草莽水”,先讓自己變成啞巴,然后再狠狠剁下自己一截小手指……第二天,負(fù)責(zé)皇家官窯采辦的官員見到張老三變成了一個口不能說、手不能動的殘廢,“皇命”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事后,眾窯工為感念張老三的義舉,特意在青竹寺旁專為張老三造了一座生祠。祠堂的名字就叫“斷指祠”。從此,整個湘陰岳州窯的窯工們似乎都有一種默契與盟約:從此再不碰官窯,改燒平窯。這也是為什么湘陰岳州窯自清代后,其官窯的焙燒日漸式微,而平窯制作卻越發(fā)興旺的重要原因。
又后來,斷了小手指的張老三更是再也不碰官窯,改為專制陶塤。
張老三制作的九孔“岳州窯牌”陶塤,音質(zhì)古樸醇厚,空靈優(yōu)美,低沉悲壯。有時,張老三自己也能吹奏幾首,其中《楚歌》、《離騷》及《窯工怨》是其必選的曲目。間或在夜深人靜之時,他還自己作詞譜曲,常常吹奏一首名叫《燕兒飛》的曲子:“燕兒飛,燕兒飛,官府黑暗把命催。燕兒飛,燕兒飛,到處草黃花枯萎,窯工個個心兒碎。”……水鄉(xiāng)黑夜里的塤聲如泣如訴,充滿了無盡的惆悵、哀婉與憂傷。
平 窯 風(fēng) 云
悠悠歲月,漫漫窯路。湘陰岳州窯城的先輩們自唐代以后有些人為地中止了官窯的制作之后,他們把心思又用回到鍋、碗、瓢、盤以及缽、洗、壺、杯等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陶瓷器皿的制作上來了。
他們改革陶瓷的制坯與拉坯工具,發(fā)明了一種“御板工藝”。所謂的御板,即為一塊寬一寸、長約三寸的普通竹板。窯師先將一團(tuán)揉好的陶泥固定在用腳踏使其轉(zhuǎn)動的陶車上,雙手握住御板削刮陶泥,使陶坯不斷變薄變巧、變輕變美。從而大大地提高了陶瓷制作的生產(chǎn)力,是為湘陰岳州窯改進(jìn)拉坯制作方法的一大創(chuàng)舉。
湖湘之地自古人文璀璨,即使從事窯貨挑夫及淘泥、洗泥、摞泥等賣苦力的窯工兄弟也大多讀過兩至三年的私塾,具有基本的文化基礎(chǔ)。加之,每個窯莊幾乎都辦有自己的“陶瓷夜校”(即“瓷庠”)。內(nèi)容包括全套陶瓷工藝的制作技能知識,還附有篆刻、繪畫、雕塑、古詩詞等文學(xué)藝術(shù)課程。這也是讓開始從事挖泥、摞泥、挑貨、裝船等“外八行”苦力活的窯工們,通過學(xué)習(xí)培訓(xùn),逐步上升過渡到從事制坯、裝窯、煅燒、繪畫等“內(nèi)八行”技術(shù)工種的重要途徑。有此作為基礎(chǔ),窯工們開始將從“瓷庠”培訓(xùn)當(dāng)中學(xué)到的技能運用到工作實踐當(dāng)中。比如,開始他們只是在陶瓷的素胎上刻字、刻畫;后來發(fā)展為制作專門的字畫及篆刻印章,直接印蓋在陶坯上;再后來,又發(fā)明將陶瓷胚具經(jīng)過繪畫、雕刻與雕塑后,再進(jìn)行二次煅燒,其觀賞性及藝術(shù)性則更為獨特與精美。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湘陰岳州窯的先輩們還將風(fēng)情詩、感懷詩、閨情詩、飲酒詩、邊塞詩以及格言、諺語、家訓(xùn)等文字刻印在陶瓷器皿上。常見的有:“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要求子順,先孝爹娘。”“天天來客不窮,夜夜做賊不富。”“不種今年竹,哪有來年筍。”還有如戲改的情詩:“君住湘江頭,我住湘江尾。夢里思君不見君,共飲一江水。”等等。從而使古老的湖湘陶瓷文化愈發(fā)炫目多彩。
我曾有幸見到幾個從湘陰岳州窯出土的唐代的碗碟與茶具,即使在這些日常器皿的制作上,先輩們也是耗足了心思、用足了智慧。其一,岳州窯茶碗。其唇口微斂,扁圓腹外罩魚子狀青黃色開片滿釉,太平底,器底平整留有三顆工整的支釘痕。其二,岳州窯茶杯。其深腹圓收,施青黃色滿釉,杯心及內(nèi)壁刻蓮瓣紋飾。后有專家總結(jié),這一時期的湘陰岳州窯產(chǎn)品所施青釉與醬釉瑩潔閃光,呈透明或半透明狀,在當(dāng)時國內(nèi)所有的陶瓷產(chǎn)品中處于領(lǐng)先地位。
岳州窯日常生活制品的美妙絕倫,從湖湘走向全國,乃至世界,則源于唐代一項十分興盛的社會活動——斗茶。唐代茶圣陸羽曾在《茶經(jīng)》中寫道:“岳州瓷皆青,青則益茶”。陸羽細(xì)舉了不同材質(zhì)的瓷碗對泡茶與品茶的影響,尤以對岳州窯茶具如何對茶有著獨特的影響,專門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和述說。
唐代詩人劉言史有詩云:“湘瓷泛輕花”。其“泛輕花”三字便是描繪唐代煮茶法中所出現(xiàn)的一種茶花景色。陸羽在《茶經(jīng)》中進(jìn)一步介紹道,“煮茶法”是直接將茶放進(jìn)岳州窯燒制的瓷甕中烹煮。大意是,先將餅茶研碎待用,然后開始燒水,但不能全沸,待水泡微露時加入茶末。二沸時方出現(xiàn)沫餑,沫為細(xì)小茶花,餑為大花,皆為茶之精華。“輕花”當(dāng)指沫花中的細(xì)小茶花而言。由于岳州窯在唐代以生產(chǎn)青瓷茶具為主,所以湖湘陶瓷研究專家莊小章先生在其所著的《岳州窯·藏珍》一書中認(rèn)為,“湘瓷”當(dāng)專指唐代岳州窯生產(chǎn)的特有茶具瓷器。茶具雖小,見證的則正是湘陰岳州窯的先民們勤勞與智慧的無限榮光。
每次翻開湘陰岳州窯的歷史,我的心情總是特別沉重。窯城的先輩們雖有一技在身,又具勤勞、勇敢、智慧、仁愛等優(yōu)良品質(zhì),但他們一代又一代總是受盡了官府的壓榨,奸商的蒙騙,以及地痞流氓的騷擾……一部湘陰岳州窯窯史,便是一部窯民們的血淚史。
過往歲月里的窯民們幾乎均是靠天吃飯,憑運氣養(yǎng)家。洞庭湖區(qū)春季雨水多,無法生產(chǎn),每年都要等到農(nóng)歷四月初八以后才能正式開工;夏季炎熱,雖是制陶曬坯的好季節(jié),卻是窯貨銷售的淡季,不少窯場因窯貨滯銷發(fā)不出工資,只好關(guān)掉作坊停止生產(chǎn)。這段難熬的日子正是西域雪山上的冰雪大量溶化、引起內(nèi)陸江河漲水的時候,陶窯人便管這段困苦的時間段為“熬西水”。沒有了收入來源,陶工們只好向錢莊的資本家或販賣窯貨的商人借錢賒米,等窯場開工生產(chǎn)后再從工錢中扣還。其中的高利貸,年息高達(dá)30%或50%不等。有些黑心的窯場資本家,預(yù)測第二天會有窯工前來打工賒米,當(dāng)晚便會安排家丁將大米用水泡發(fā),簡稱“化水米”。一斤大米,往往能“化”至一斤半,甚至兩斤的重量。
當(dāng)時,在湘陰岳州窯的窯工中一直流傳著一句形象生動的順口溜:“窯工學(xué)徒,鐵腳、馬腿、神仙肚。”其中的鐵腳,是指窯工須長時間地踩踏在污泥及燒燙的瓦礫與碎石當(dāng)中;馬腿是指多站少睡,窯工們每天工作時間均在15個小時以上;神仙肚則指他們的生活差,什么熱湯冷水、殘羹剩飯都得無條件地下咽。一首《陶工苦》的歌謠這樣唱道:“裝窯燒窯心打鼓,汗水伴泥土。好貨交官府,要錢遭拘捕。茅草當(dāng)被鋪,衣服補又補。餐餐無油水,誰知陶工苦?”還有一首《窯工怨》的民謠,更是如泣如訴:“窯煙子往上沖,年年扯不清;窯煙子往下蓋,年年還舊債;鍋里冒米煮,頓頓熬野菜;天冷無寒衣,半床水絮蓋;五荒六月熬西水,十冬臘月餐搞餐。”
窯工們雖生活艱辛,但每年臨近春節(jié),他們還是會十分認(rèn)真地把各自的窯場打掃得干干凈凈,在窯莊的神龕上面貼上用黃裱紙書寫的“風(fēng)火仙師”四個大字,再在左右兩邊分別粘貼好“風(fēng)助火力”與“火借風(fēng)威”的對聯(lián)。春節(jié)那天,他們還會在窯門前的供桌上擺上供品、燃起香燭,個別富裕點的窯莊還會宰頭水牛……用以祭祀窯神。祈求神仙能保佑行業(yè)興旺,賜福禳災(zāi)。正月里,窯工們還會你一塊、我兩塊地集資籌款,在窯場上放火銃、耍龍燈、舞旱船、踩高蹺、跳蚌殼舞、唱地花鼓戲……其目的還是想借此沖散舊年的陰霾與霉運,讓新年窯場的日子過得熱熱鬧鬧、紅紅火火。湘陰岳州窯的窯莊供奉的窯神,先前是舜帝,中間一段時間是老子,后來是雷公。《湘陰縣志》有云:屬民多陶,悉資神佑。窯工們認(rèn)為,舜帝和老子均是文官形象,難以鎮(zhèn)住窯城日益增多的牛鬼蛇神。后請的“佑陶之神”雷公則是面黑目炯,內(nèi)著皂袍,身披鎧甲,手執(zhí)鋼鞭,腳踏火輪……其形象非常適合降妖除魔,保一方平安。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早在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家鄉(xiāng)人鐘相、楊幺便發(fā)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洞庭湖農(nóng)民起義”。起義軍破州縣、焚官府、殺貪官,等貴賤、均貧富,對“漁樵”與“漁陶”等窮苦之人不收課稅、實施保護(hù)。先后占領(lǐng)了整個洞庭湖區(qū)的十九個州縣,持續(xù)時間長達(dá)二十余年。見此,窯城的窯工們紛紛加入起義軍隊伍,他們戰(zhàn)時參戰(zhàn),平時則抓緊時間加倍燒制窯貨,為起義軍提供強大的后勤支援及軍餉供給。這也為后來代表朝廷前來鎮(zhèn)壓起義軍的岳飛,下令切斷所有窯城銷售窯貨的水陸交通,放火焚燒整個岳州窯城的舉措埋下了伏筆。由此,湘陰岳州窯也遭受到了一次堪稱毀滅性的打擊。
湘陰岳州窯另一次有規(guī)模的“窯工起義”是一位名叫藍(lán)義林的窯工發(fā)動起來的。出生于光緒年間的藍(lán)義林其先祖便是湘陰城里有名的“武秀才”。他自己也是自幼習(xí)武,粗通文墨,且俠肝義膽,專愛替人打抱不平,在百里窯城頗有名氣。一日,藍(lán)義林隨窯莊的貨船來到湖北新堤販賣岳州窯貨。當(dāng)?shù)靥沾衫习宀芎榘l(fā)買下窯貨后,欺負(fù)藍(lán)義林他們是外地人,故意拖欠貨款,甚至還惡語相向……見此,藍(lán)義林揮筆在曹老板的錢筒上留下打油詩一首:“可恨關(guān)羽不斬曹,留下奸商害客陶。借得青龍刀一把,定來新堤走一遭。”后來,曹老板了解到寫詩的藍(lán)義林是湘陰岳州窯城中一個個性強悍、敢做敢當(dāng)、眼里容不得沙子的“狠角色”等情況后,越想越是害怕……不幾日,便親備禮品,攜帶欠款,來到三峰窯窯莊找藍(lán)義林登門謝罪。由此,藍(lán)義林在“江湖”中的影響越來越大,在窯工們中的號召力也越來越強。
此時袁世凱賣國稱帝,改“民國”為“洪憲”,湘人蔡鍔組織護(hù)國軍,通電反袁。岳州窯城又值水旱連年,百業(yè)蕭條,窯城的資本家與窯貨奸商則趁機巧取豪奪,廣大窯民妻啼子哭,生活難以為繼。于是藍(lán)義林振臂一揮,組織了有兩千多名窯工參加的“湘陰岳州窯護(hù)國軍”,號稱“一旅”,自任旅長。霎時,整個湘陰岳州窯城紅旗招展,梭標(biāo)獵槍林立;奸商與惡霸聞風(fēng)喪膽,個個甘愿捐獻(xiàn)財產(chǎn),人人自愿賑濟(jì)貧苦窯民……最后,雖然藍(lán)義林和他所領(lǐng)導(dǎo)的窯工護(hù)國軍還是遭到了反動軍閥的殘酷撲殺,但百里窯城的“紅色火種”從此再也未曾熄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