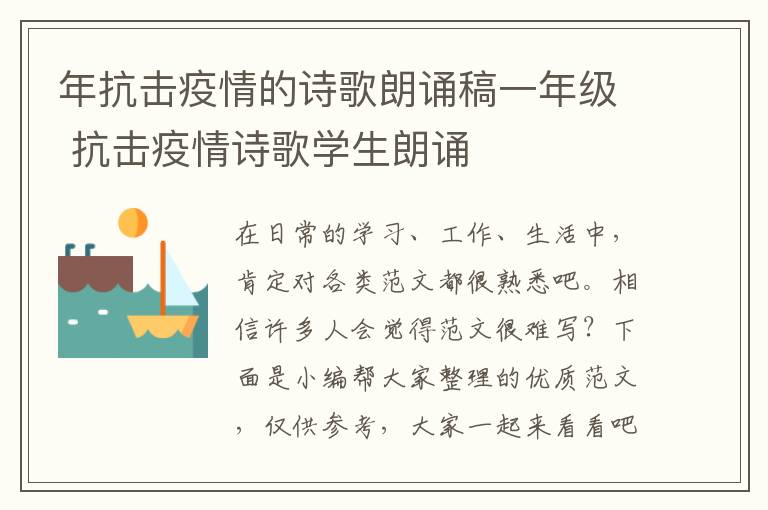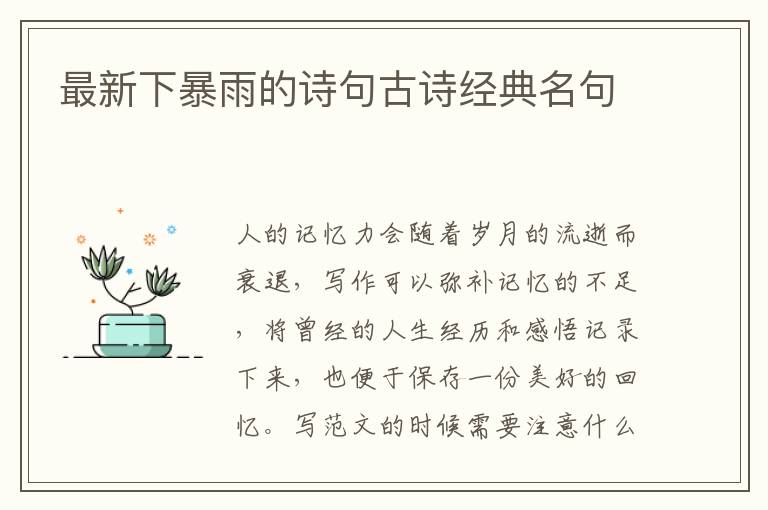傅彩霞《活成一棵樹》

一
《一棵開花的樹》是臺灣詩人席慕蓉的經典之作,如影隨形,令我心動了三十年。光陰如梭,一晃而過。我也步入中年,青絲里隱顯白發。但是,每每吟誦這首詩,依舊扣人心弦,蕩氣回腸;觸景生情時,涕下沾襟,心顫魂飛。懷春少女為追慕神圣的愛情,求佛在她“最美麗的時刻”,卑微地化身為樹,長在心上人“必經的路旁”,并“慎重地開滿了花”,正當她信心滿溢地眺望愛情,示愛擁抱時,那個冷峻的他,卻“無視地走過”。于是,深情少女期許已久的炙熱之心,如凋謝的花瓣,癡纏零落,夢碎一地……人生的況味與惆悵,如一彎瘦月,泛著清冷的光。淡雅剔透,溫婉悲涼,盡在不言中。
寂寥之夜,再次捧讀《一棵開花的樹》,倏然間,卻發現了另一番別有天地的境界。這首看似描寫失戀悲歌的愛情詩,何嘗不是用慈悲情懷,彈奏的一曲熱愛自然的感恩樂章呢?就像純真懵懂的時代,我有幸邂逅詩歌,愛上了樹,讀樹成了親近自然、安頓靈魂的主要方式,仿佛那千姿百態的一棵棵深情的樹里,隱藏著一個前世今生的夢。
喬遷城西后,我喜歡獨自散步,走著走著,不覺拐進了離小區不遠的自怡公園。一棵枝葉葳蕤的大樹,樹冠如傘,默默佇立在荷塘一側,剛正不阿,如龍似鳳。在觸目對視的瞬間,我的心,登時被深深震撼了。這棵不知名的大樹活得實在是步履維艱:前面是死水池塘,后面是亭臺樓閣,上面是青石壓身,下面是黑暗世界。它幾乎沒有了自身發展的縫隙與空間。每天,還有許多行人游客,踩著它裸露的粗根,無視地走過,它卻強忍悲痛,呈現出一副不煩不惱的樣子,在逼仄的生存空間里,在貧瘠狹隘的土壤里,坦然自若,枝繁葉茂,修身養性,活出了自己的姿態和尊嚴。我在它的面前小立靜思,感受著它堅韌的風骨,就像對面站著一位無憂的哲人,常樂的智者。
我用顫抖的手,在那個秋日的黃昏,用相機留下它偉岸的身影,并傳發給幾位文朋詩友求證詢問它的名字。一位好友說:“雖老葉猶翠,年久根愈深。何必問名姓,不語也知音。”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心中釋然。
而另一位詩人則復信說,他很震撼,這棵大樹使他想起在澳洲墨爾本見到的一棵老樹,它們樹干的本根很相似。他把遠道造訪的那棵樹,稱為“樹林中的長者”,并發來詩圖精美的照片,請我對比。古稀之年的他對異國他鄉的老樹肅然起敬,從樹中讀到的是“歷經滄桑活著的尊嚴”和“剛強的人生”。
幾經周折,有一位學識淵博的朋友告訴我,自怡公園的這棵大樹,叫樸樹,是城市的綠化樹,能抵抗很強的毒氣……從無知到有知,從對面相見不相識到從此變成密友知己,人生充滿風雅、真趣與奇跡。我不禁對樹吟詩:“滄桑年年吟秋風,欲覓詩心問蒼穹。老枝新葉通靈脈,相濡同筆寫蔥蘢。”
二
此后,行走紅塵,我會特別留意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老樹。每次驚喜相逢,我都愿意停下腳步,與一棵棵老樹說話。在北京天壇,我被千棵茂密松林古樹的壯觀所震撼,那倔強彎曲又嶙峋的老樹根,讓我心生敬意,樹根上條條天然的紋理,訴說著它們不平凡的風霜歲月;在菏澤單縣牌坊街,我親吻過千年的枸杞神樹,它虬曲粗壯的樹干,從窗戶的縫隙,穿越墻壁,斜逸伸展而出,仿佛一幅活生生的門內暗使勁兒、門外展風華的遒勁畫卷;踏訪青州范公亭公園三賢祠,千年的唐楸和宋槐,閃爍著內斂的光芒,穿透歲月的遮蔽,聳入云霄,矗立大地,任憑風吹雨打,從未低下高貴的頭;也曾專門登上安丘的城頂山,慕名拜訪過公冶長書院門前,已有兩千五百年樹齡的“中華第一雌雄銀杏樹”,雄樹開花,雌樹結果,兩樹根枝相交,宛如夫妻,攜手相依,共沐風雨,貞心德行,譽滿九州,又仿佛“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令觀者醍醐灌頂,耳清目明;我還曾數次造訪過臨朐石門坊,每每相逢一棵棵黃櫨樹,我就會想,黃櫨樹面朝陽光,樸素生長,在發芽、濃綠、醉紅、凋落的四季輪回里,不忘初心,不辱使命。根,深深扎在瘠薄的土地,在巖縫中安身立命,以倔強之姿,剛烈之態,不畏風雨冰霜,不懼寒冬酷暑,冷眼看紅塵,向世人展示頑強。綠樹連成的濃蔭,浸潤著光亮絢爛的晨曦……我把邂逅的每一棵樹,當成等待我熱情的“開花的樹”,而我的造訪與親近,則是“結一段塵緣”的遇見。
至今,我從未見過千歲老人,神仙唯有天上有。在我生活所及之地,百歲老人也十分稀缺,而在大自然里,不經意間,就會相逢到百年千載的老樹,怎不令人向往,心生敬仰?人,活不過一棵樹,更多的時候,人不如樹。樹,從不制造垃圾,那些枯枝落葉“零落成泥碾作塵”,已風化成腳下的沃土;它們吸入二氧化碳,呼出氧氣,凈化空氣,造福人類和世界;它們奉獻鮮美豐碩的果實,用魁偉的身軀,抵擋風沙雪雨,寧肯犧牲自己,也要把綠水青山留住……
我時常凝望著一棵棵頂天立地的大樹,想象著它們那看不見的一層層年輪,感受著那一股股令人迸發向上的力量,它們是經過了多少日久年深的積淀與集聚,多少專注修煉的思索與定力,經歷了多少風霜雨雪,汲取了多少日月精華,才擁有了這樣樂觀向上的良好心態,海納百川的大度包容和堅忍不拔的精神,向著夢想的方向一直向上,向上……最終,活成了一棵參天古樹,既有靜水流深的韻味,又有蕩氣回腸的魅力;既令人仰望敬畏,贊嘆不已,又能俯視紅塵,看人來人往,悲歡離合。
記得三毛在《如果有來生》一文里曾說:“如果有來生,要做一棵樹,站成永恒。沒有悲歡的姿勢,一半在塵土里安詳,一半在風里飛揚;一半灑落陰涼,一半沐浴陽光。非常沉默、非常驕傲。從不依靠、從不尋找。”也許,只有經歷了愛情的痛徹心扉,人生的大起大落的女作家,才會如此渴望“瞻望弗及,佇立以泣”,才會有如此濃厚深邃的浪漫感悟,才會把來生締造成一棵神奇的樹,“站成永恒”。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人和樹,都是受地球邀請而來的貴客嘉賓,宇宙長河的匆匆過客。人,何嘗不是一棵紅塵煉心的樹呢?越是向往高處的陽光,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越是凝神沉潛,默默耕耘,安詳扎根在土里,越能擁有天道酬勤的喜悅;越持之以恒地自律,根越扎得深,活得越優雅高級,枝葉越濃密繁茂。我用心感悟每一棵自信達觀的樹,收視內觀,明德啟智,為自己曾經淺薄虛榮的“飛揚”,羞愧無比。
三
蕭蕭北風,寒冬凜冽。周末,我驅車回家,遠遠地,望見父親佝僂的身影站在樓前法桐樹下。恍惚之間,似覺得88歲的父親儼然也活成了一棵從容淡定的老樹。我攙扶父親回到溫馨的家中,冬日陽光下,他的白發如銀,格外閃亮刺眼。皺紋似波,在臉上蕩漾,莊嚴而凝重。父女倆秉燭夜談,一邊品味著茶里的光陰,一邊漫無目的地閑聊。戎馬生涯三十年的父親,依舊保持著早睡早起的習慣。他告誡我,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一勤天下無難事。我隨意問起他起居作息時間,他淡淡地啜了一口普洱茶,慢條斯理地對我說,自己老了,沒法再英姿颯爽地活著了,每個寂寞的夜晚,從夢中醒來,就無法再入睡。他便會獨自坐在床邊,隔窗看天上的月亮星星,看院子里石榴樹搖曳的影子,靜靜聆聽蕭蕭的風聲,有時,竟把風聲誤認為母親回家的敲門聲,站起身來,去開門相迎,直到把失望的黑天擦亮微明……他說得平平淡淡,我聽得淚珠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