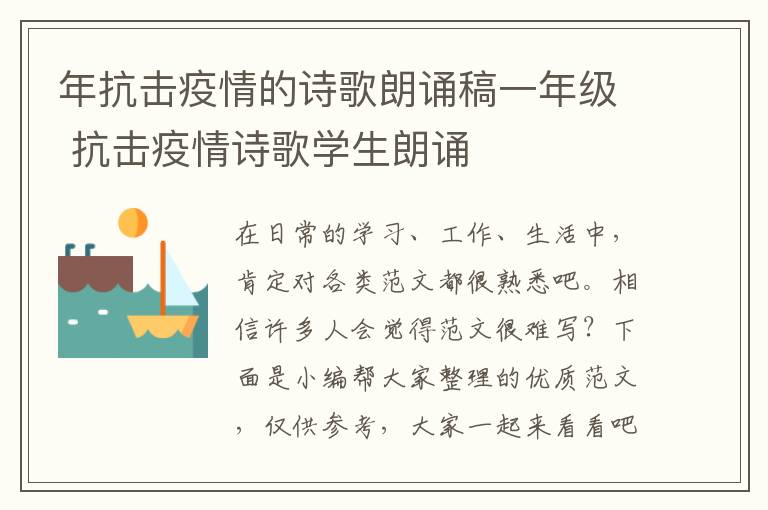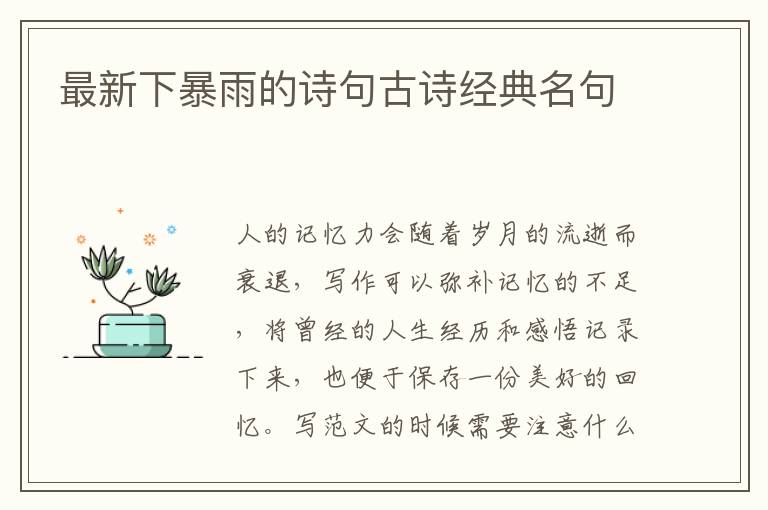唯物辯證法論戰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所謂“唯物辯證法論戰”是中國社會性質與社會史論戰的繼續,也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斗爭的一次重要戰役。新康德主義派的張東蓀與托洛茨基派的葉青之間的爭論。他們都把反動矛頭指向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場論戰中,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是以艾思奇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與《矛盾論》的發表,從根本上駁斥了張東蓀、葉青的唯心主義哲學,這場論戰也就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勝利而宣告結束。“唯物辯證法論戰”是當時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斗爭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必然反映。這場論戰的重要意義就在于批判與抵制了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深入與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運動。
張東蓀認為哲學不包括本體論,哲學只討論認識論問題。張東蓀從右的方面修正康德的學說,取消了康德對物自體的假定,而把康德的主觀唯心主義與不可知論發展到極端。他把感相與物自體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沒有什么關系,把感覺完全歸結為主觀產生的。張東蓀承認外界有其條理,但這種條理并不是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是人們主觀上的自立法度或構造方式。時間與空間也是主觀的。在所謂“名理的先在性”問題上,他割裂了現實與范疇、對象與概念的內在聯系,認為范疇、概念是先驗的,不依靠任何對象的。多元認識論也是絕對不可知主義。在本體論上提出所謂“泛架構主義”,認為“一切都是架構,而不是實質,而架構卻不是能離開我們的認識”(以上引文均見《認識論》)。
張東蓀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與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混為一談,否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是哲學史上的偉大變革。他攻擊否定之否定規律是“歷史定命論”,認為“對待”、“負面”、“矛盾”等都不是矛盾。認為馬克思“一個錯誤”就是“把矛盾又一轉變而成為斗爭的意思”。認為質量互變規律只是“實驗的結果”,不是“法則”,不是“普遍方法”。張東蓀對唯物辯證法的攻擊,實質上是否認矛盾的普遍性與絕對性,反對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
張東蓀極力反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關系的基本原理。他認為政治、法律、道德、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是平等并列的關系。他反對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與階級斗爭的觀點,認為“中國所謂行,即指一種職業,而同時即是一個階級”。因此,他把中國社會分為三大階級:即“種田的農人;做各種工藝的是工人;業貿遷的商人”,他們“都是只求安居樂業的”(《階級問題》)。
張東蓀的哲學思想是中國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他對在中國介紹與傳播康德及其后學的哲學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這對于中國人民了解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不能不說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然而,他的哲學思想體系是唯心主義的,這種哲學的社會作用也是反動的,是為在中國建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提供理論依據的。
在這場論戰中,葉青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卻拋出了所謂哲學消滅論,實際上就是妄圖消滅馬克思主義哲學。他認為:“世界底認識則是由宗教而哲學而科學”,就發展說,“宗教早消滅了,哲學在消滅中,現在是科學獨霸知識的時代”(《哲學到何處去》。葉青還極力鼓吹唯心主義的綜合論,在他看來,“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這個三段式,也就是“辯證法——物質論——辯證法+物質論”,“觀念論——物質論——觀念論+物質論”和“哲學——科學——哲學+科學”等機械的相加。他還認為“事實作用于思維,則生理論;理論作用于實踐,則生事實”,二者是并列的。認為運動是靜止的積累,靜止是運動的停留。認為“外因與內因互相統一”,二者在事物發展中起著同等的作用。認為“思維決定存在”這個命題。“在社會方面則有其正確性”。葉青哲學的實質就是機械論,二元論和折衷主義。
針對張東蓀對唯物辯證法的攻擊,鄧云特指出:客觀事物本來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辯證法從關聯中,從對立統一和發展變化中去把握一切事物。“主觀律只是已認識了的客觀律”,只要主觀與客觀的一致,就是科學的真理。針對張東蓀割裂正反合的聯系,否認事物因果關系的謬論,鄧云特指出:“正與反間是存在了因果關系,同時也就存在了依存關系。”(《形式邏輯還是唯物辯證法》)由正到反或由反到合,都是由量到質的變,都是舊的因素被揚棄而形成更新的形態。
艾思奇指出,唯物辯證法與唯心辯證法不能混為一談,二者有本質的區別,哲學永遠不會消滅,它的對象就是“世界發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法則”。葉青不懂什么是絕對意義,什么是相對意義。辯證法認為“靜止只是運動的特殊形態,靜止的東西,本質上仍是運動的”。外因雖然不可忽視,但它不能決定事物的必然性,決定事物必然性的只是內因,“內因是基礎,是本質,是發展的必然性的原因”(《哲學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