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雜劇的興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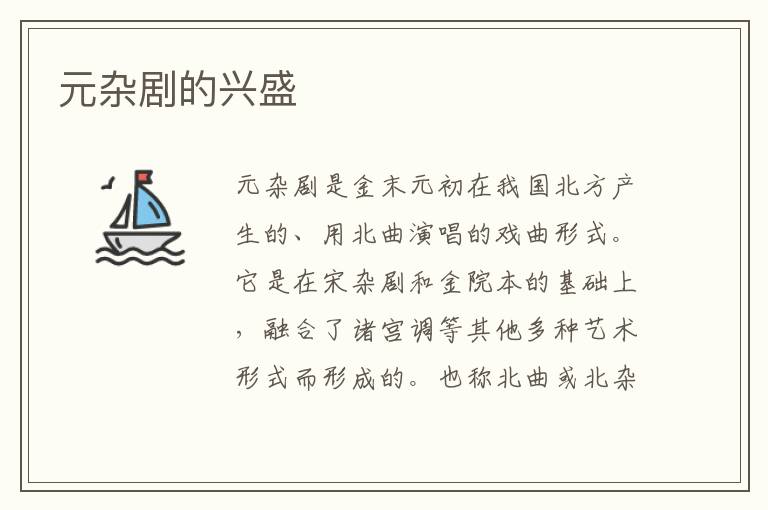
元雜劇是金末元初在我國北方產生的、用北曲演唱的戲曲形式。它是在宋雜劇和金院本的基礎上,融合了諸宮調等其他多種藝術形式而形成的。也稱北曲或北雜劇。文學史上所稱的元曲,並不專指北雜劇,同時還包括散曲。
元雜劇的產生,是我國古典戲曲成熟的標志。雜劇之所以能在元代形成並興盛起來,有它政治、經濟以及藝術本身發展等各種因素。元代社會的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是錯綜復雜的,隨著社會的發展,一方面社會生活呈現出無比豐富和復雜的狀況;一方面人們認識和反映社會生活的能力也有所提高。以傳統的文藝樣式來反映如此紛紜復雜的社會現實,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所以就要求有一種新的文藝樣式出現。于是元雜劇應運而生,由金入元得以長足發展,代替了傳統詩文而占據了文壇的主導地位。因此我們說,元雜劇的形成和發展,首先是社會的要求。同時,元代的民族歧視,階級壓迫,也使漢族知識分子產生了分化。由于元代停止科舉長達七十八年之久,這就阻塞了廣大知識分子仕進的出路。他們的社會地位急遽下降,所謂人分十等,儒者在娼妓之下,乞丐之上。所以許多讀書人便走入民間,走入藝人賣藝的“勾欄”。這不僅使他們熟悉了下層人民的生活,也使他們熟悉了民間藝術,他們就能更好地從事雜劇創作,抒發自己的憤懣,為被壓迫人民鳴不平。在元代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儒家正統思想的統治較為松弛,封建倫理道德的控制力較弱。這不僅使一些知識分子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以新的眼光來看待民間藝人與民間藝術,同時也就有可能產生一些違反儒家思想、充滿反抗精神的作品。一些雜劇作家甚至和藝人合作寫戲,同臺演出。作家、演員相互促進,使他們在藝術上發揮了更多的創造。這樣,就開辟了一條新的創作道路,涌現出一大批雜劇作家,對雜劇的興盛起了重要的作用。蒙古統治者對歌舞、戲曲的愛好,也是對雜劇形成、發展的一個促進。據《元史·百官志》記載,元代統治者把管理樂人的教坊司置于正三品的高位,可見其重視的程度。從經濟上說,由于元代版圖遼闊,地跨歐亞,交通暢開,海運、漕運溝通,就使得工商業空前發展。大都、真定、平陽等北方都市,商賈輻輳,十分繁榮。市民階層也得以進一步壯大。這就給雜劇的演出提供了雄厚的物質條件和群眾基礎。當時的大都就是元雜劇形成與發展的一個基地。元雜劇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我國歷史上各種表演藝術長期發展、互相融合的結果。我國古典戲曲的原始形式在先秦時代就已經出現了,經過長期的流傳、發展,至宋代初具規模,到元代才日臻成熟。宋代的雜劇已有四或五個腳色,演出人物故事。同時,傀儡、影戲、說唱、說話、舞隊等各種民間文藝也十分興盛,這就給雜劇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金代的院本融合了各種伎藝,表演藝術有了新的發展。當時流行的諸宮調,按宮調聲律類別來組織曲子,演唱長篇故事,也給元雜劇的演唱、結構以直接的影響。同時從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傳來的歌曲,也豐富了演唱的曲調。它們和北方的民間曲調相結合,形成了新的樂曲體系。這樣就使得元雜劇從內容到形式都達到了成熟階段。
元雜劇集歌舞、音樂、表演等各種藝術形式之大成,是一種綜合藝術。在結構上,一般以四折為限。每折由同一宮調的一套曲子組成。四折相連,按事物的發生、發展、高潮、結束來安排情節,演唱故事。由于演唱的人物故事一般來說都較為復雜,所以還另加一個短小的場子,唱一、二支曲子作為補救,稱為“楔子”。內容更為豐富的則分為多本多折來演唱,如《趙氏孤兒》五折,《西廂記》五本二十一折。雜劇的每一折都由唱、白、科組成。唱是歌曲,白是賓白,即道白,科是動作、表情或舞臺效果的標志(如“做驚科”、“內做風起科”)。每折歌曲限一韻一調,組成一套曲子。四折的四套曲子由一個演員主唱。男主腳稱為正末,女主腳稱為正旦。次要腳色則稱為外末、沖末、外旦、貼旦等。反面腳色稱為凈,副凈和搽旦。也有的原為當時的市語,后來也成為腳色名目了。如孤、孛老、卜兒、細酸等等,就是當時對官員、老翁、老婦,窮書生的通稱。
元代是我國戲劇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短短的數十年間就有有名可考的雜劇作家近二百人,有劇目可考的作品達七百三十七種(見傅惜華《元人雜劇全目》)。保存下來較為完整的劇本也有一百五十余種,其中就有傳世的優秀作品數十種。如《竇娥冤》、《救風塵》、《西廂記》、《漢宮秋》、《梧桐雨》、《趙氏孤兒》、《李逵負荊》等。七百余年來被改編為各種新的戲曲形式,不斷地在舞臺上演出,有的還流傳至國外,影響十分深遠。元雜劇的優秀作品,突破了傳統文學的禁區,直接從市井的現實生活中汲取創作營養,把被封建文人所鄙視的下層人物作為主人公,描寫他們的生活和命運,就我國的文學發展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進展。它擴大了文學反映生活的領域,使人們感受到濃郁的生活氣息和一種新的思想因素。這些作品,有的深刻地揭示了黑暗的封建統治對人民的迫害,反映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如關漢卿的《竇娥冤》、《魯齋郎》、《蝴蝶夢》,無名氏的《陳州糶米》等等;有的抨擊了封建禮教、封建婚姻的罪惡,歌頌了青年男女的正當愛情,如王實甫的《西廂記》、白樸的《墻頭馬上》、關漢卿的《拜月亭》、鄭光祖的《倩女離魂》等;有的揭露了統治集團的投降賣國,歌頌了人民和愛國將領反民族壓迫的斗爭,如關漢卿的《單刀會》、馬致遠的《漢宮秋》等。同時,也應該看到,在現存的雜劇中,也存在不少封建糟粕。如有的宣揚了封建倫理道德和鬼神迷信思想;有的表現了消極頹廢的沒落階級思想情緒;也有的表現了色情、靈怪等低級趣味。即使那些具有進步思想的作品,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揭露封建黑暗統治的,往往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涉及到民族關系的,也往往流露出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那些表現男女愛情,反對封建禮教的,其反抗性也往往不夠徹底,要以男方奪取功名做為向封建家長妥協的條件。就藝術成就而言,元雜劇有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本色”、“當行”,適合舞臺演出,而不是“案頭之曲”。因為作者不僅熟悉生活,而且精通舞臺藝術。元雜劇具有極大的通俗性,不僅一些以“本色”見長的作家,如關漢卿、楊顯之等所寫的劇作通俗流暢,生動自然,即使一些以“文采”見長的作家,如王實甫、馬致遠等所寫的作品也是“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正因如此,它還具有更廣泛的群眾性,不僅劇中的人物故事在群眾中廣為流傳,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而且有許多劇作,就是書會才人和藝人合作的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