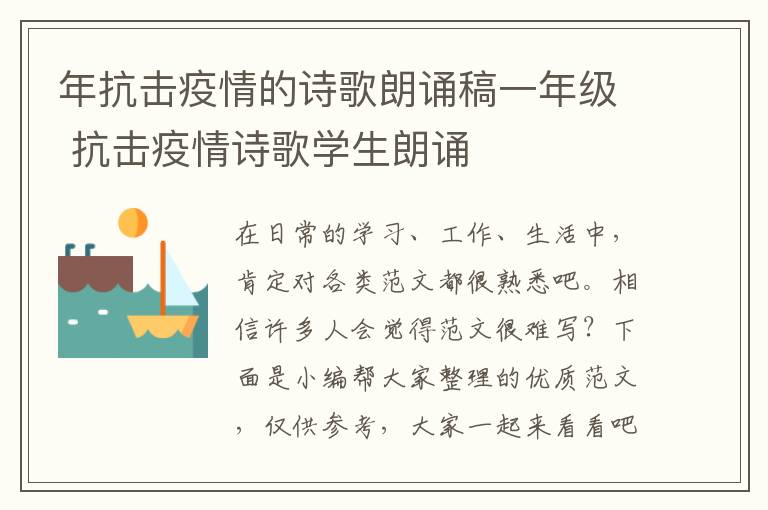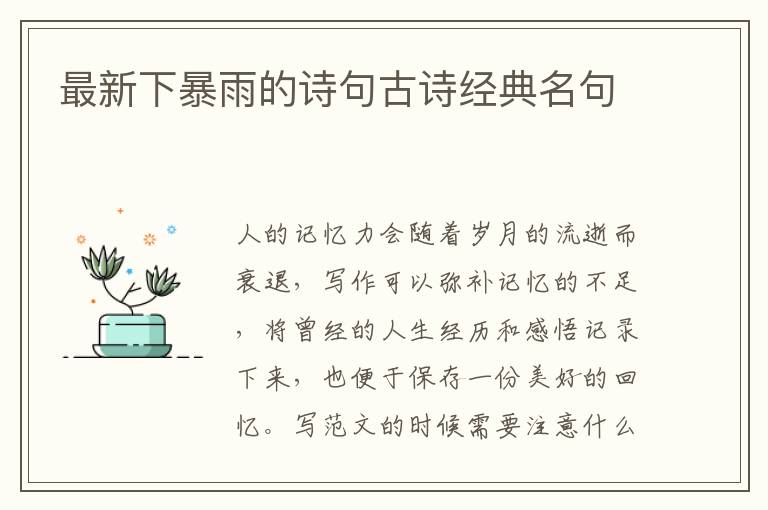丐婦殉節

作者: 李恩江 【本書體例】
沈起鳳
沈起鳳(1741——?),字桐威,號漁、紅心詞客。江蘇吳縣人。乾隆舉人,后屢試不第,歷任祁門(今安徽祁門縣)、全椒(今安徽全椒縣)訓導,晚年在京城候補選官,客死異鄉。善詞,尤精于曲,著有《吹雪詞》和雜劇《報恩緣》、《才人福》等。又有筆記小說《諧鐸》共十二卷。諧,取意于《莊子·逍遙游》“齊諧者,志怪者也”,明其為志怪之書;鐸,取意于《尚書·胤征》“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指文末宣明題旨的結語,著意勸懲。
青州丐婦小苗兒,面微黑,眉目有姿致,隨夫王五丐于淮。王懶而暴,日臥黃公祠,命妻出丐。歸而乞者少,則杖之,曰:“爾從何處嬉,所獲乃止此耶?”歸而乞者多,則又杖之,曰:“爾與誰有私,賺來阿堵物?茍敗露,而翁不爾宥也。”小有迕犯,王坐階級上,曳令下跪,自批其頰。婦不與較,飲泣順受之。
一日,土豪某,使仆招其婦。婦慮見疑,偕夫同往。某命唱《打棗兒》曲。唱畢,某與仆耳語久之,引王出外廂,賞以酒。私謂婦曰:“以爾具此姿色,何患無良匹?乃至為乞人婦,且聞其朝凌暮辱,夫婦之情絕矣!汝盍早自計?”婦艴(fǔ福)然曰:“丐婦知有夫耳!豈知其朝凌暮辱哉?且婦人從一而終,又何計之有?”某笑曰:“汝不自計,吾已為若計之。”引婦出外廂,夫已短帶結喉而死。
婦知石卵不敵,佯曰:“薄幸奴,我隨汝十數年,有何享受,動輒加赤棒。今若此,是天報也!”某大喜。婦曰:“殺之固善,然犬馬斃,亦當埋帷蓋。茍假尺土而掩之,實君之盛德。”某信之,命仆監守其婦,出詣曠野,相度隙地。
婦乘間謂仆曰:“爾知我心愿否?”仆曰:“不知。”婦曰:“我乞人妻耳,驟作富家婦,飲食起居,都不慣。但得如爾者事之,則我愿足矣!”仆喜,繼而曰:“奈主人何?”婦曰:“是不難。急首于官,則主人必系縲紲(léi xiè雷泄)中。爾與我席卷而遁,向他鄉作一小貿易,差勝低頭檐下也!”仆大稱善,急啟后戶去。
某歸,失其仆,詰之婦。婦曰:“不見汝來,想渠蹤跡去矣。”某擁婦求歡。婦曰:“是亦大可笑。幾見未寒肉在側,即欲強眠人婦者?”某固逼之。婦正色曰:“以彼遇我虐,故強顏事君子。若相逼,是以暴易暴,相去幾何?”正撐拒間,忽見仆引持索者數輩,洶洶而入,系某竟去。婦亦隨至衙暑。稟驗之,一鞫而服。某論死;仆以同謀首告,減一等,并系諸獄;命以尺地掩王五尸。
掩畢,丐婦持刀而前。環視者爭勸之,且曰:“渠當日荼毒若此,今以德報怨,亦已過矣!何必爾?”婦嘆曰:“君臣夫婦,其義一也。丐婦之死,俾天下知盡婦道者,不得以夫為借口;亦以愧夫視臣草芥,而敢視君如寇仇者。”言訖,自刎死。
鐸曰:“烈士捐軀,盡其在我。此柱厲叔之所以死報莒敖公也。眾人國士之論,彼豫讓直不曉事漢耳!”
(選自《諧鐸》)
青州有個討飯的婦女叫小苗兒,臉色稍微有點黑,眉眼卻很有姿色韻致,跟隨丈夫王五在淮河流域某地求乞。王五懶惰而且暴虐,每天躺在黃公祠里,命令妻子出去乞討。回來要是乞討的東西少,就用棍子打她,說:“你在哪兒玩,討得的東西竟然只這么一點?”回來如果乞討的東西多,就又用棍子打她,說:“你跟誰通奸,賺回來這么些東西?假使事情敗露,你老子是不會原諒你的。”只要稍微有點不順其意,王五就坐在黃公祠的臺階上,拖過來命令她跪在下面,親手打她的耳光。婦人不跟他計較,忍泣吞聲逆來順受。
有一天,地方上有錢有勢的惡霸某某,派仆人來叫那個婦人去。婦人恐怕被丈夫懷疑,偕同丈夫一起前往。某某叫唱了個名為《打棗兒》的小曲。唱完之后,某某和他的仆人附耳低語了好久,就領著王五出去到了外面廂房,賞給他酒喝。某某在無人時對婦人說:“憑著你長得如此美貌,哪愁沒個好的配偶?竟然至于做了乞丐的老婆,況且聽說他對你一天到晚地欺凌侮辱,夫妻間的恩情已經斷了!你為什么不趁早替自己打算打算?”婦人惱怒地說:“討飯婦人只知道有個丈夫就夠了!哪能記著他一天到晚地欺凌侮辱呢?況且女人應當從一而終,又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某某笑著說:“你不為自己打算,我已經替你打算好了。”于是領著婦人出來到了外面廂房,看到她丈夫已經被用短短一條帶子系在脖子上勒死了。
婦人知道雞蛋碰石頭是不行的,假裝著說:“負心奴才,我跟隨你十多年,享過什么福?動不動就用棒子打,施行家法。現今落個如此下場,這是老天爺對你的報應!”某某大為高興。婦人道:“殺他固然不錯,可是,就是狗啊馬的畜牲死了,也應當用破車帷裹了或用爛蓬蓋蓋著埋掉。如果借用數尺之地將他掩埋了,實在是您積了大德。”某某相信了她的話,命令仆人看守著那婦人,自己出門到曠野中去,找塊空隙的土地。
婦人趁機對仆人說:“你知不知道我的心愿?”仆人說:“不知道。”婦人說:“我只不過是個乞丐的妻子,突然作富貴人家的媳婦,飲食起居,都會很不習慣。但是要能嫁給象你這樣的入,那么我的心愿就算滿足了!”仆人很高興,接著說:“對主人怎么應付呢?”婦人說:“這不難。趕快到官府去出首,那么一來主人肯定得繩捆索綁地關到監牢里去。你和我將他的細軟之物席卷一空、暗中逃走,到其他的地方作個小生意,也比在人家家里低聲下氣地伺候人強!”仆人連稱不錯,趕忙開后門出去照辦。
某某回來,不見了他的仆人,向婦人詢問此事。婦人說:“老是不見你回來,想必是他找你去了。”某某抱住婦人要求成其好事。婦人說:“這也太可笑了。哪見過人家丈夫的尸體還在身邊,就要強迫同人家的妻子睡覺的人呢?”某某堅持要逼迫她。婦人臉色鄭重地說:“因為他對待我暴虐無恩,所以才厚著臉皮來侍奉您。如果逼迫我干此事,這是以暴易暴,相差能有多少呢?”正在撐持推拒的時候,忽然看見仆人領著幾個拿著繩索的差人,氣勢洶洶地自外而入,綁上某某徑直帶走了。婦人也隨著到了衙門官署,稟告官長勘驗這件兇殺案。只經一次審訊罪犯就服了罪。某某被判處死刑;仆人以同謀犯的身分首先告發,罪減一等,將他們一并關到監獄里去了;命令用數尺之地掩埋王五的尸體。
埋葬完畢之后,討飯婦人拿著一把刀走到墳前欲自殺。周圍觀看的人爭相勸阻,并且說:“他當初如此地殘害你,現在你為他申怨報仇、埋葬他入土,以德報怨,也已經超出常格,對得起他了!何必這樣尋短見呢?”婦人嘆息說:“君臣夫婦之間相處,應該遵從的原則是一樣的。我從夫而死,是要使天下人知道,應該恪遵婦道,為人婦者,不能用丈夫的不良作為不守婦道的借口;也是用來使那些借口君主視臣如同草芥而膽敢視君如同寇仇的臣子感到羞恥。”說完,自刎而死。
鐸詞:“烈士為國捐軀,是在盡他們自己的本分。這就是柱厲叔盡管不被重用但仍要去為莒敖公以身相殉的原因。至于豫讓主張主人以對待普通人的態度對待我,我就以普通人的規格報答他,主人以對待國士的態度對待我,我就以國士的規格報答他;那么此人只不過是個不懂事的莽漢罷了。”
此篇小說寥寥千來字,卻寫得波浪起伏,錯落有致。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位善良端莊、智勇雙全的乞丐婦女小苗兒的形象。先寫其“隨夫王五丐于淮”,王五懶且暴,對她百般凌辱,而她“飲泣順受之”,以見其本性之善良。王五貧賤而得美妻,不會也無力護持,心理變態而產生猜忌之心是自然的。對此,小苗兒或許是理解的,委屈求全,獨力乞討以維持二人的生計。貧賤夫妻百事哀,其中最大的悲哀在于心靈不能溝通,王五和小苗兒都在以自己所特有的方式“相愛”著也實在太苦了。再寫土豪某的殺夫奪婦,開始,小苗兒嚴辭拒絕勸誘;既見夫死,就佯許而陰圖之,以許嫁為誘餌唆使土豪的仆人“急首于官”;結果,既保全了自己的名節,也報了殺夫之仇。這時候,小苗兒一改素常的柔順軟弱,儼然巾幗而丈夫者,智勇具備,敢于斗爭,也善于斗爭。對丈夫與對土豪的不同態度形成巨大反差,讀來引人入勝,不禁為主人公的果敢機智叫絕,為古來受侮辱的弱女子吐氣。但是,在黑暗的封建社會里,象小苗兒這種身世的女子是沒有出路的,等待她們的是受凌辱被玩弄的命運,要想保持自己的清白人格,只有死路一條。所以,最后寫了墳前自刎一節,小苗兒在葬夫之后,了無生趣,夫在時至少還有個精神上的寄托,還有個抗拒壞人奸污玩弄的堂皇借口,而今流落異鄉,孤苦無告,頓覺人海茫茫,已無自己的立身之地。小苗兒是同惡勢力抗爭的斗士,但終其一生,所扮演的只是一場悲劇,“自刎死”是這場悲劇的高潮;然而,象夜空中的閃電一樣,小苗兒的死照見了封建惡勢力的卑鄙無恥無情,昭示人們不砸爛封建的落后制度,婦女永無翻身之日。
但是,作者的世界觀同作品的文學形象的現實、歷史意義相矛盾是文學史上的普遍現象。沈起鳳敘述丐婦殉節的故事本意在于宣傳綱常名教,我們卻從中發現了小苗兒形象的反封建意義,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作者表面地看到了小苗兒的從夫、殉夫,以為是從一而終的烈婦的典型,因而贊譽有加,甚而借小苗兒之口,叫她在自刎前講上一通夫婦君臣之義的陳辭爛調。最后,作者振鐸以呼“烈士捐軀,盡其在我”,表揚柱厲叔死報莒敖公的愚忠,批判豫讓的眾人國士之論,純屬借題發揮,迂腐得可笑。其實,眾人國士之論還有點民主思想的閃光,在歷史上不無進步意義;柱厲叔的愚忠卻死得莫名其妙,無足取。仿佛按照作者的意思,小苗兒若是真實人物,可以上烈女傳,至少可以同烈女傳上的人物媲美。豈不知烈女傳上的三貞九烈也各自有其不得不“貞”不得不“烈”的原因,絕不會同封建衛道士所標榜的那么堂而皇之。從沈起鳳的作小說,人們完全可以推定沈起鳳們如何寫正史。然而,文學形象的自身發展有其不以作者意志為轉移的固有規律,設身處地,小苗兒或許受有一些封建思想的影響,但她的生活處境決定她不可能對三綱五常之類有什么深切的了解,君君臣臣的大道理她是講不來也不屑講的。小苗兒的自刎死,是由于絕望,作者強加給她死前宣言,實屬敗筆。人常說作者落后的世界觀會影響作品中文學形象的創造,于此可見一斑。